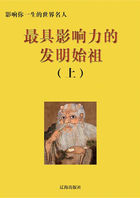班彪知道窦融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但更多地是不服气,上前扶着他的手说:
“尉佗之举实在不足取,鼎足之势也不可能久远。”
窦融考虑再三,最后有所顾虑地问道:
“我拥兵割据河西已经多年,虽然没有正式提出称王的封号,但也从来没有同刘秀有过任何交往,更没有向他称臣的表示。如今刘秀与隗嚣已经开战,我突然向他称臣刘秀会相信吗?他或许认为我与隗嚣串通好向他使诈呢?假如这样,隗嚣认为我归顺刘秀了一定与我反目成仇,而刘秀又不信任我,那才是骑虎难下呢。”
班彪点点头,认为窦融担心得有道理,便建议说:
“周公要想让刘秀释疑也不难,只要窦兄做出一两件让刘秀感激的事,公开表明你的立场,我想刘秀一定会对周公坦诚相待的。我虽然没有见过刘秀其人,但从他人的口中了解刘秀是一个宽厚仁慈之人,善解人意,因此,手下将领都悉心为他驱使。在平定中原的叛乱中,刘秀除了武力平叛外,也始终于安抚怀柔为上策,像周公这样的贤才能够主动归附,对于刘秀是求之不得,怎会将周公拒之千里呢?”
班彪缓了缓又补充道:“当然,对于你的突然归附,刘秀心生疑虑也是难免的,你在同隗嚣决裂的同时也可暗中派使臣携书到洛阳拜见刘秀,讨一讨刘秀的口风。”
窦融明白了班彪的意思,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窦融忽然想起了什么,他瞟一眼班彪,开玩笑地说:
“叔皮兄,愚弟怎么觉得你不像是隗嚣派来的说客,倒有点像刘秀所派来的人啦,莫非叔皮兄早已暗中归顺了刘秀,今来是奉诏行事。”
班彪哈哈一笑:“我倒真希望能像你说的这样,只可惜我班彪手中无兵将无地盘,孤身一个,像我这样的穷酸书生投奔刘秀,只怕被当作讨饭的拒之门外呢!我可不像周公这样成为人人都想争取的对象。”
窦融收住了笑容,压低声音说:
“如果叔皮兄也有东归之心,不妨先去洛阳探一探虚实,顺便也为我探探口风,如果刘秀真心待我,我再臣服于他。”
班彪连连摇头:“不合适,不合适。周公若有诚意应该亲自附书一封,并派亲密之人到洛阳献书表明心迹。人人都知我是隗嚣的幕僚,我入洛阳,在他人眼中我是为隗嚣还是为周公呢?”
窦融固执道:“你是西州大儒,名满天下,又是你劝我归顺刘秀,我可以派亲信前往洛阳,但你也必须一同前往,凭你的声望,有你去面见刘秀就可以减少他对我的疑虑。”
班彪一再推脱,窦融都坚持让他~同前往,最后只好笑道:
“那好吧,只怕我没有周公所说的那样的声望,周公要失望呀!”
窦融一见班彪答应为他奔走,立即说道:
“我回去后立即写一封亲笔信,派我的弟弟窦友随叔皮兄东去洛阳。”
班彪努努嘴,窦融会意,耸耸肩说:
“你担心张玄坏事?放心吧,你们一出发我就派人送他上西天,这也算我对刘秀的一个小小表示吧,当然,还有更大的表示,当你到洛阳后自能听到。”
第二天,张玄再次向窦融提及与隗嚣合作的事,窦融推辞说:
“合作一事关系到河西五郡存亡大事,非融一人能够作主,必须召来五郡太守共同协商后才能决定。”
张玄估计西州兵现在一定正和刘秀派遣的征西大军交锋,双方胜负如何不得而知,为了尽快得到窦融的援军,张玄催促窦融尽快召集五郡太守共商大计。窦融考虑到臣服刘秀一事也应当同五郡太守协商一下,便答应了张玄的要求,派人召集五郡太守来金城。
张玄和武威太守马期曾经相识,他在马期刚刚来到金城后便到马期住处登门拜访,询问马期对于同隗嚣合作持何意见。
马期一听张玄这么说,嘿嘿一笑,说道:
“窦融自立为王也好,保持现状也好,拟或归顺刘秀也好,我马期不喜也不忧,无论情况如何,我仍是我的武威太守,升不了,谁也把我赶不走。”
张玄一见马期持这种态度,有点急了,略一皱眉说:
“马大人,此言差矣!现在是关系你个人前途命运的关键之际,怎能说与你无关呢?如果窦融自立为王与隗将军合兵打败刘秀大军,天下将为刘秀、公孙述、隗嚣、窦融几人共有,窦融拥兵河西称王,马大人身为一郡之长理当封侯。相反,假如窦融归附刘秀,情况将大不相同。当然,窦融也许能够封侯,而马大人你就惨了。”
张玄故意卖个关子,惹得马期十分不解地问道:
“张学士,请你说个明白,我怎么会惨了呢?升官不敢保证,但武威太守的位子还是没有问题吧?”
张玄摇摇头:“不见得,刘秀是怎样的人,他对中原各路归顺之人又怎样,前车之鉴后车之辙,他怎么会相信后来归降的人。刘秀一定对窦融心存疑虑,但碍于情面又不能不用他,这样,刘秀惟一的做法就是断其左右臂膀,他一定会拿你们河西五郡的太守开刀,或撤职,或调离,换上他的亲信,从而监视窦融,架空窦融,让他空有其位却无其实。无论如何,窦融还有个空位,而你们几位太守恐怕连空位也没有,这不叫惨吗?”
马期沉思不语,张玄趁机说道:
“马大人,你联合其他几位郡守力主窦将军拥兵自立,并和隗嚣将军一同抗击刘秀入侵为上策。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你的太守之位,也才能保证你武威郡子民免遭兵戈涂炭。”
马期略微点点头:“明日聚在一起时先听一听其他几人的意见再说吧。”
正在这时,张掖太守任仲来访,任仲一见张玄在此,带着几分嘲讽的口吻说:
“张学士自诩西州第一辩士,伶牙利齿,巧舌如簧,来河西游说多日不仅没有说动窦将军的心,反而使他有心归汉,实在是可笑之至啊!”
张玄被说得满脸绯红,一时竟不知如何反驳。
马期并没在意张玄的反应,一听任仲说窦融要归附刘秀,急忙追问道:
“任兄,你从何处得知周公要归附汉室,只怕是你想归顺刘秀才四处散布谣言违惑众人?”
任仲并不恼,哈哈笑道:
“马兄弟,你我做郡守的,归顺刘秀有什么益处?到头来还不是做他人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我才不要归汉呢!”
任仲说到这里,幽幽叹息一声:
“不过,这自立与归顺的事是周公一人说了算,不是你我能当家的,他决定的事谁也更改不了,让我等到此不过是走走形势,行也行,不行也行。”
马期立即显出不满的表情:“姓窦的也太过专横跋扈了,这河西之事也不能处处听他一人的,他是什么东西,没有我们弟兄们几个,哪来的河西今天?任兄,凭良心讲,这河西本是咱哥们的,自从窦融来到后却反客为主,我们反而处处受他挟制。说真的,我早就对他不满了!”
任仲知道马期的性子,劝慰道:
“别说气话了,我等不是看在他祖父有恩于我们的情份上,怎会容他在这河西指手划脚。事到如今,他要归顺刘秀也许有他的道理,我等先与其他几位太守通通气再说,如果大伙一致反对归顺,这事也由不得他一人说了算。”
“倘若他们三位都同意臣服呢?”
“那我们也只好顺从大势啦。”
“哼,无论谁去归降刘秀,我坚持不去,我佩服隗嚣的胆量和志气!”马期嚷道。
张玄趁机怂恿说:“马大人,不是小弟说句奉承话,凭你的才华,不用说做一郡太守,整个河西五郡交给你也治理得井然有序,保证不会比窦融逊色。”
任仲白了张玄一眼,张玄只作没看见继续说道:
“如果窦融执意归降刘秀,马大人可以率武威一郡与隗将军合作,小弟可担保马大人得到好处一定优于刘秀所给的。隗将军知人善征,对马大人一直十分敬重,时常在众人面前称赞马大人的品行与才学,让众人向马大人学习——”
不等张玄说下去,任仲冷冷地嘲弄道:
“想不到张学士之所以深得隗嚣重用,原来凭借的就是给人带高帽,拍马溜须。”
张玄嘿嘿一笑,回敬道:
“我说的可句句都是实话,任大人若不信,不妨随我走一遭,亲口问问隗将军。”
“我可没有那份闲心!”
张玄现在还不愿得罪任仲,他还想通过马期争取任仲,对任仲的冷淡与讽刺并不介意,反而进一步讨好说:
“任大人整日操劳张掖郡的大小事务,可谓日理万机,如果不是为着河西归属这等大事只怕也无暇到此,只可惜河西的前途堪忧,像任大人这样的河西元老也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着让河西五群拱手让给他人。”
这话确实点中了任仲的心事,他叹息一声,独自默默不乐地走了出去。
第二天,窦融正式把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库钧、敦煌太守辛肜五人召集到军机厅商讨面临的局势,并亮出自己的态度。梁统、库钧、辛肜都表示一切听从窦融的决策,任仲沉默不语,马期向来性子急,胸中也藏不住话,站起来反对说:
“主公为何不拥兵自立为王,偏要归顺刘秀那鸟人,他虽是刘姓,又非王室王宗,何德何能让我等归顺于他。我反对主公这样做!”
窦融似乎早就知道马期会反对,也不吃惊,淡淡一笑说:
“马大人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从心里说我也不想臣服刘秀,但这是大势所趋呀。隗嚣与刘秀已经打得难舍难分,凭隗嚣的实力目前还可勉强撑上一阵子,但从长远看,隗嚣最终一定要被刘秀所灭。隗嚣一灭,下一步就轮到我河西之地了,与其等到那时归附,不如趁早做出决定,也给刘秀等人一个深明大义知道进退的好印象。从我对刘秀的了解,我等现在臣服,不仅能保住河西的地盘,而且还能够加官进爵呢!”
马期不待窦融说下去,就打断了他的话。
“哼,什么加官进爵,你仅为你个人考虑,根本不顾及我等的利益,归顺刘秀你当然可以加官进爵,而我们五人呢?只怕连郡守一职都保不住,我不管其他几人怎么想,我是坚决不投降,要降你们降好了。”
马期一把臣服说成投降,弄得窦融也很尴尬,他瞟一眼马期。颇为不悦地说:
“你不愿臣服,莫非你想随隗嚣一起与刘秀争战?”
马期嗡声说道:“我马期不愿投降刘秀又怎会投降隗嚣,我只想保住武威一郡谁也不投降,自己保住一郡百姓不受兵灾——”
马期一口一个投降,惹火了窦融。
“投降,投降,谁投降谁?你能不能不说得那么难听!”窦融厉声斥道。
马期被训得垂首不语,但脸上却是气鼓鼓的,没有一点服气的样子。整个大厅里谁也不说一句话,大家都这么沉默着,各自想着心事,打着个人的算盘,气氛显得极不自在,可谁也不先开口,惟恐出言不当遭到他人反对。
任仲看看梁统、库钧、辛肜,见他们都面色平静,似乎刚才的争论与己无关,他又瞟一瞟窦融,见窦融铁青着脸,他张了几次嘴,都没有说话,最后忍不住问道:
“主公,刘秀与隗嚣刚开战不久,一时还不知谁胜谁负,臣服一事能不能暂且不提,等上一段时间,等他们分出胜负时再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