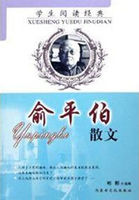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我的娘,城里那馒头,啧啧,要不是我亲眼看到,我真不敢相信那个大啊……父亲说着,一双粗大的手叉开,像捧着一个很大很大的球。父亲一边比划着,布满胡渣子的阔嘴巴不自觉地大张着,拳头大的喉结上下滑动。那一刻,我清楚地听到咕咚一声吞咽的声响。
我仰着头,看着父亲比划,尽我30多年前所拥有的最大想象力。
有咱家过年蒸得饽饽那么大?父亲不屑地摇摇头。
有喝糊糊的陶瓷白碗那么大?父亲还是摇头。
有盛玉米糊糊的瓦盆那么大?父亲依旧摇摇头。
有洗脸的塑料盆那么大?父亲仍然摇摇头。
我想得头皮发疼也想像不出到底有多大。我很不争气地听到我的嗓子眼里也发出父亲那样咕咚咕咚的声响。
你小子,想不想亲眼去看看?
想啊,不光亲眼看看,还要吃个饱吃个够。我知道,我的这个想法无异于做梦。那时只有逢年过节,或者碰着娶亲的时候,才能偶尔吃一回馒头。
那你小子就好好念书,念到你北京的二叔那样,就能看到那么大的馒头了。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亮光闪闪。
真的念到二叔那样,就能见到您说的那么大的馒头了?我歪着头,看着父亲,问道。
那还要说,你爷老子啥时候骗过你?父亲脸一沉,一副神圣不容置疑的样子。
于是我开始拼命读书,发誓一定都要读到城里去,去亲眼验证一下有没有父亲说的那么大的馒头。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我的娘,城里的馒头那个白啊,啧啧,要不是我亲眼看到,我真不敢相信天下还有那么白的馒头……
我仰着头,看着父亲的脸,说,比雪还白?
雪?嘻!父亲说这话时那神情,雪算什么。
比我二姐的脸皮还白?我不服地看着父亲的脸说。我二姐当时十八九岁,脸皮白嫩得全村的姑娘没人能比。
嗯,差不多,不过还不如城里的馒头白。
哪里有那么白的?我有些怀疑,显然我的怀疑的口吻惹怒了父亲。那还要说,你爷老子啥时候骗过你?父亲脸一沉,一副神圣不容置疑的样子。
我赶紧闭紧嘴巴。
你小子,想不想亲眼去看看?
想啊,不光亲眼看看,还要吃个饱吃个够。
那你小子就好好念书,念到你北京城里的二叔那样,就能看到那么大的馒头了。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亮亮的光。
于是我就拼命地读书。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我的娘,城里的馒头那个香啊,啧啧,要不是我亲口尝过,打死我也不会相信,这世上还有这么香甜的馒头……父亲说着,鼻息抽着,闭着眼睛,一副陶醉的样子。好久才睁开眼睛,那样子像吃了三斤猪头肉。那时过年一家人也吃不了二斤肉。
我仰着头,看着父亲的脸,说,那么香?比吃肉还香?
肉?嘻!父亲说这话时那神情,言外之意,肉算什么。
比我二姐脸上搽的粉子还香?我不服地看着父亲的脸说。我二姐当时十八九岁,正是爱美的年龄,脸上总是涂抹雪花膏,从人前走过,小伙子都忍不住抽动鼻子,抽得空气丝丝响。
嗯,差不多,不过还不如城里的馒头香。
哪里有那么香的?我有些怀疑,显然我的怀疑的口吻惹怒了父亲。那还要说,你爷老子啥时候骗过你?父亲脸一沉,一副神圣不容置疑的样子。
我赶紧闭紧嘴巴。
你小子,想不想饱饱地吃一顿?
想啊,最好吃个肚子朝天那才叫过瘾。
那你小子就好好念书,念到你北京城里的二叔那样,就能看到那么大的馒头了。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泛着亮亮的光。
于是我就拼命地读书。
脑子里装满了那么大那么白那么香的馒头,我成了全校学习最勤奋的学生,成绩在全校数一数二。
你小子,有口福,以后一定能吃上又大又白又香的城里的馒头。
父亲果然言中了。后来,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再后来,我又考上了京城的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再后来,我在京城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我们结了婚,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正当我准备接父亲到京城的时候,父亲却病倒了。
弥留之际,父亲突然睁开眼,看着我,艰难地说,娃儿,爹没骗你吧?城里的馒头大不?香不?甜不?……你……你小子有口福,吃到了。
我重重地点点头,强忍住泪水,哽咽着说,爹没骗我,爹哪会骗我呢?城里的馒头真的那个大那个白那个香,比咱家过年、娶媳妇蒸的馒头都大都白都香……
我嘴唇哆嗦着,说着,突然父亲头一歪,去了,一抹笑容凝固在了沟壑纵横的老脸上。
现在,我时常对我女儿讲起她爷爷的故事,讲起他爷爷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我的娘,啧啧,城里的馒头那个大啊白啊香啊……好几次,我十八岁的女儿插话说,我爷爷好福气,能吃到那么大那么白那么香的馒头,我可一次也没吃到耶……
那一刻,我真想对女儿说,孩子,其实你爷爷一辈子没离开过大山,就连最近的县城也没去过,更没见过吃过什么城里的馒头。而我那年到城里读书,第一次见到的城里的馒头只有小孩子的拳头般大小,味道也没有老家手工馒头那么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