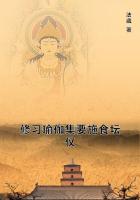德清,是我的一个姐夫,堂姐夫。
端午节前一天,午后五时许,父亲来电话了;心想:什么事呢,不是说好他和母亲不来,我、妻子、孩子也不回么?果然,第一句话就是:出事啦!我心一忐,脑袋“嗡”的响了一下。第二句话却是:德清死啦,拖拉机压死啦。我心虽惊,却也稍稍平复下来,脑袋似乎清醒许多。
问:真死啦?
答:嗯!
问:怎么搞的?
答:我们也刚到现场,具体还不很清楚。
问:哪里?
答:溪水中学上来,离红旗桥百吧两百米的样子。
问:一条平路啊,又不转弯,怎么就?
答:是啊,怎么就?德清是去看翀儿,在溪水镇下的客车,搭的盘拖,出事的地方有一条通往他家的小路,其实到红旗桥下车也有一条小路通他家,并不远多少,他怎么偏生就在……
问:是不是喝酒喝多了?
答:谁晓得!只是,只是翀儿怎么办?后天,就高考了啊。翀儿的书又读得好。
我说,要瞒了翀儿,不能影响他高考。事情已经发生,德清泉下有知,也会同意的。只能这样了,他会同意的。
我和德清没有什么交往,近二十年吧,也就相见过二三十回罢,怎么就有权替他作这样的主呢?并且我后来了解到,还不只我一个,知道消息的亲朋戚友都是如此;甚而至于有的说,德清死的不是时候,自己喝醉酒,被拖拉机压死,一了百了,却带累了孩子。
堂姐,是二伯的女儿,和我同年,夏天生的,大我几个月。同时上的学,小学同班,初中同校;堂姐很普通,无论是学习,还是其他;给人的印象是:朴讷。初中的时候,分田到户了。两个劳动力少的家庭合在一起分到八又三分之二份田,就是七亩来田吧。于是,农忙时节,特别是“双抢”,两家不分彼此,合在一起做。堂姐做事不偷懒,勤快,话少,给人的印像仍就是:朴讷。后来,我初中毕业考入师范学校,转城镇户口了;二伯母落实政策,回一个学校做工友,堂姐、堂弟也都转城镇户口了。两家的田锐减,但仍然不分彼此,依旧合在一起做;堂姐呢,还是朴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堂姐顶了二伯母的班,在家乡的村小学以工代教了。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啦,这就是德清了。媒人说,男方比女方大一岁,要长相有长相,要口白有口白;关键是铁饭碗,虽则是顶父亲的职,在外县,养路工班,但红黑是铁饭碗;还有两个妹,没有其他兄弟,家当总归是他的。果然,次年春节我初次见他,只觉一表人才,不仅高我半头,而且相貌堂堂,满面红光,特别是启眉动眼,神采飞扬,似乎总在笑,且笑得自然。我心想:配堂姐还是配得来的。二伯父却有些不满意:嫌他话多,一餐饭要呷两三个钟头,边喝酒,边海五天六,天上事知一半,地上事他全知,花,飘……二伯父是一个勤劳一辈子,朴讷一辈子的人,不满意是自然、当然的。——但是,堂姐和德清的事并没有拖很久,九十年代初就结婚了。
那年暑假,回老家去。虽则两家的田更少了,仍然合在一起“双抢”。印象中,我和堂姐都下了田,而德清似乎不在;问堂姐,说是工作忙,回不来。二伯父在一房搭言:“他是呷不惯这个苦,懒。”那时,祖母还在。正月初一,一大家子都聚拢来,给老人家拜年。德清和堂姐也不例外。德清依旧是一餐饭要呷两三个钟头,别人都下桌了,他还在喝酒,谈笑,海五天六;脸上红光更甚,神采更是飞扬。每当这时,二伯父总是鼓着眼睛望着他;要么就骂堂姐:老公都管不住。而我呢,对德清的评价也渐渐地与二伯父靠拢了:花,飘。
像普遍的夫妇一样,德清和堂姐也有孩子了,一个男孩。父亲打电话给我,说是德清说啦,托他强舅舅给孩子取个名,他强舅舅是个文化人。我说,叫“翀”吧,“羽”字旁,加个“中”;父亲说,德清是“德”字班,孩子是“富”字班,还要取个辈名;我说:叫“富弼”吧,与范仲淹、韩琦、欧阳修齐名的“富弼”。当时,似乎还特别招待过父亲,要孩子的父母查查字典,搞清楚“翀”字、“弼”字的音义,莫读错啦,出洋相。后来,德清是感谢过我的,说:“到底是文化人,有学问。”我说:“我真是担心你们把‘翀’念作了‘羽中’,把‘弼’念作‘百’呃。”德清笑,笑得爽朗、自然,说:“我和你姐还真是查了字典;翀,鸟向上直飞;弼,辅助……”
几年后,二伯父去世了;又几年,祖母也去世了。我和德清相见的次数就更少了。要见,也多在正月里。没有了伯父在旁鼓眼睛,德清一餐饭似乎呷得更久了,仍是边喝酒,边谈笑,海阔天空,神采飞扬;有时大家躲他,有时敷衍他,有时乘机开他的玩笑,依旧言笑自若。堂姐是个朴讷之人,二伯父在时都管不住他,此时自然听他。但是他的酒量确实了得,上桌时脸是红的,话是清的,下桌时脸仍是那样红,话仍是那样清,我是没见过他醉过。
除了正月,我平时一年难得回一趟老家。正月里见到了他,一年就见一面;正月里没见到他,一年就见不上一面。关于德清的消息,也就道听途说的多。或曰,仍旧喝酒吹牛,几个小时不下桌;或曰,三天两头不去上班,打牌赌博;或曰,翀儿不像爷那么花,话少,懂事,书读得好,不要爷娘管,还管爷娘不呷酒、不打牌……这些“或曰”,让我更认同二伯父当年的“不满意”,“鼓眼睛”了;往往听后,一笑置之:“这个德清!”
我们的相见,有较例外的一次。那时,我还在县里工作。一个夏天吧,两三点钟的时候吧,红火大的太阳——不知什么原因,我会在那样的时候在县城的街上溜——突然,听到喊声:“强舅舅,强舅舅!”哦,原来是德清——高我半头,面如关公,满脸的笑。我问:“你怎么……”德清解释道,他想调回县里,中午请对口部门的领导呷饭、喝酒。他说:“有眉目啦,领导夸我搞接待是把好手!强舅舅,你在领导机关工作,到时候请你帮忙哪。”我含糊地应着,说:“要不,到我家去歇一晚?”德清说:“歇就不麻烦啦,我回嘞,翀儿和你姐等我嘞。”我说:“这个时候,没得到溪水镇的车啦。”德清说:“那不要你管,你只管到时帮、帮忙。”
这次例外的相见,以德清的离去而告终。看着他以不稳的步态渐渐远去,我摇了摇头。不知为什么,他的调动并无下文;或曰,是因为三天两头不上班,喝酒,吹牛,打牌,在单位名声不大好。我懒得深究,这样倒好,免得自己给人以“不帮忙”的口实。
以后仍然极少相见,极偶尔听到关于他的“或曰”,直到这个端午节的前一天,父亲打来电话,说他出事了,被拖拉机压死了!这才想起,许久不见我的这位堂姐夫呷酒、谈笑、海五海六了;是的,今年正月,我们似乎确实未曾谋面。
灵堂设在禾坪上,上面悬着德清的遗像:年轻,眉目爽朗,笑容如生……这已经是端午节后一天了,他的孩子——翀儿正在高考;我呢,前来吊梓。
礼毕,将堂姐撑起来,她就哭倒在我的怀中了:“老弟呀——”我不知说什么,于是不说什么,撑着她,任她哭;大家在一旁相劝:“都这样了,都这样了,再哭,他也回不来了!”
终于,堂姐能够边哭边说了:“讲起翀儿,他脸上就有光。他想望翀儿考到他毅舅舅那个大学去。他说自己就这样发身了,翀儿会出息。这次去看翀儿,也是不放心。哪料——”
我赶紧问:“翀儿知道吗?”
“我们瞒着他。昨日翀儿打他爸爸手机,姐没敢接,他满舅舅接的,说他爸不知哪里打牌去了,手机掉在家中了,呜——”堂姐又哭了,说,“老弟,老弟,翀儿会不会感觉什么,会不会影响他考试,万一,怎么对得起你姐夫,呜——”
“不会的,不会的,姐夫会在天上保佑他。”
“会吧?会吧?”
“会的!会的!”我的话气分外肯定,大家也一旁附和,而堂姐呢,用她的双手不住地拍我的肩膀,机械地问:“会吗?会吗?万一!万一!呜——”
七嘴八舌,连哄带劝,堂姐慢慢平静下来;而我,也该告辞了。堂姐送我,又哭了,说:“你姐夫舍不得办呷,舍不得办穿,打牌也是几块钱的量,喝酒……他省,把钱省来明日供翀儿上大学……还说,那时就带我出去旅游,呜——”
“翀儿会带你去旅游的,翀儿会的。”
“那天,那天你还会来吧?”
我明白,“那天”指的德清出殡的日子。我能来吗?为着一个过从不密、不甚了解、不甚满意的姐夫,还是堂的,我已请假一天,驱车七十公里,前来吊梓,还能再请假一天,前来送葬吗?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必要吗?于是,我打起官腔,漫应道:“看情况吧。有空,我一定抽空来。”
“我晓得你忙。你老弟,他毅舅舅,都是他给翀儿树的榜样。毅弟远;老弟,你要来啊。”
“我今日就是请假来的。没得什么特殊情况,我一定——想方设法——请假来。你——你要保重啊。”
对我话中那些曲里拐弯之意,朴讷的堂姐显然没听懂,悲戚的面容焕出几分满意的微光。怕对着这面容,更惭愧于德清那眉目爽朗、笑容如生的脸,于是,赶紧上车,赶紧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