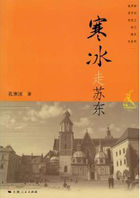文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状元、宰相、文学家和思想家。生于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就义于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吉州庐陵县人(今江西吉安市青原区富田乡文家村)。宋宝祐四年(1256)天祥举进士,在集英殿的廷对中,他以“法天不息”为核心观念写成的《御试策》被理宗“亲拔为第一”,成了该科状元。考官王应麟云:“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宋史·文天祥传》卷四一八,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818页。文天祥刚介正洁,“天性澹如”,“自拔于流俗”。其立于朝,以正直敢言著称,故常被免职而返乡;其官于地方,则关心民生疾苦,深得百姓拥戴;当元军铁骑踏遍江南大地时,一介书生状元宰相文天祥起兵勤王,九死一生,其意坚不可摧。在兵败被俘百般劝降皆不奏效的情况下,元世祖亲自许以中书宰相之职,仍为天祥所拒:“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愿赐一死足矣!’……天祥临死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拜而死。”同上,9823页。文天祥以一腔热血实现了其“慷慨为烈士,从容为圣贤”的人生理想。近八个世纪以来,文天祥的人格气节,他的诗文、他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面对外侮内患,英勇不屈,逆境奋起,从而使中华民族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外来侵略、天灾人祸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始终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因此,分析文山先生的人生态度、生死追求、人格意志等,能帮助我们获得卓越的生死智慧,帮助我们更好地做人做事,得到幸福与成功的人生。人生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从文天祥一生事迹来看,其人生态度可一言以蔽之:知其不可而为之。一般来说,人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时,常常要考虑:这件事能不能做?做得了否?以及后果是什么?通俗一点说,即做这件事值不值?若做这件事毫无成功的希望,人们便不会去做;若做这件事的后果是得不偿失,人们也不会去做,这就叫“知其不可而不为”,人之常情也。观文天祥的一生,他恰恰相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做这些事必定做不成,明知做这些事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他却偏偏要去做,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就是天祥异于常人之处,亦是其感人至深的地方。在文天祥中状元的宝祐四年(1256),其父文仪病逝在京城。送父葬并守孝原要三年,但在实际的制度上规定25个月即可,这样,到了宝祐六年(1258),天祥服孝期满,可以赴朝廷为官了。以文天祥状元的身份,以理宗皇帝对其试卷的高度评价,跻身朝廷既为必然亦是当然。其时在朝丞相是丁大全,有人劝天祥去信求一职,他却说:“仕如是其汲汲耶!”意为自己决不愿钻营官场。庐陵郡侯自然以天祥中状元事为地方骄傲,知县刘汝励就曾在县学建“进士第一堂”,他们也在为文天祥还不能官于朝而焦急,准备代他申报以“除初官”,天祥“力辞谢,得止。”《纪年录》,《文天祥全集》卷十七,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86页,下引该书均只注篇名页码。
古代士子皓首穷经,奔竞于科考,不就是盼早入朝廷为官宦吗?人人知其“可”而极力做之;天祥虽知“可”而独不为。其不阿权贵,敝屣尊荣的人格精神于此可略见一斑。直到宋开庆元年(1259),文天祥陪弟文璧赴临安参加进士考试,由朝廷补授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未及上任,蒙古兵已分三路,直指川、湘、鄂,京师为之震动,被宠幸的宦官董宋臣极力主张朝廷迁往四明(今宁波),以避元军锋芒。满朝文武多觉不可,但慑于董的权势而少有非议。文天祥以微末之地位,毅然写下了《己未上皇帝书》,认为:大敌当前,朝廷必须从四个方面痛下决心:“一曰简文法以立事”;“二曰仿方镇以建守”;“三曰就团练以抽兵”;“四曰破格以用人”。文天祥尤为尖锐地指出:宋理宗贪图享乐,纵容奸佞,以致酿成社稷生死存亡之祸。他还说:“臣愚以为今日之事急矣,不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灵,以解中外怨,以明陛下悔悟之实,则中书之政必有所挠而不得行,贤者之车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异议,何从而消?敌人之心胆,何从而破?将士忠义之气,何自激昂?军民感泣之泪,何自奋发?”《己未上皇帝书》,第95页。真乃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但是,天祥根本没有想到,或者根本不在意,以他一个二十四岁的“后生”,列散官二十八阶的品级,又怎能撼动董宋臣这棵“大树”?上书自然如泥牛入海,渺无声息。次年,文天祥被改派去签书镇南军(今江西南昌)节度判官厅公事,这带有贬黜意味的任职,使他愤然自请任闲散祠禄官(建昌军仙都观主管)。天祥还未正式入仕途,便打道回府隐于老家文山了。这些超出常人的行为举止,实匪夷所思,充分显示出文天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
宋景定三年(1262),文天祥被召为秘书省正字,后迁景献太子府教授,升为著作佐郎。就在天祥“官运”稍有起色时,被贬官外地的董宋臣被理宗召回,任为内侍省押班,兼主管太庙,并主管景献太子府事,成了文天祥的上司。在天祥眼中,“君子”与“小人”形如水火,势不两立,于是,他又写了《癸亥上皇帝书》,全书提及他曾议“以宋臣尸诸市曹”事,并乞宋理宗屏退董宋臣:“宋臣之为人,臣实疏远,亦安能以尽知之。惟是天下之恶名,萃诸其身,京国闾巷,无小无大,辄以董阎罗呼之……伏望陛下稍抑圣情,俯从公议,纵未忍论其平生之恶,以置其罪;亦宜收回成命,别选纯谨者而改畀之。”《癸亥上皇帝书》,第99页。书上后,仍毫无消息。实际上,董这次被招回后就从未失宠于理宗,死时还被追封为节度使。于是,文天祥只好再辞官退归田园,后经斡旋,才被改知瑞州。一已甚,何能再?文天祥真的是犯了主之“婴鳞”(逆鳞)。董宋臣者,何许人也?他在宋理宗的生活圈子里,绝对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他不但能为理宗皇帝敛财,而且能起楼台亭阁,进“倡优傀儡,以奉帝为游燕”。这就是天祥在上书中“稍抑圣情”一句的由来。文天祥可谓是明知其不“可”却一定要“为之”,其铮铮铁骨令人赞叹。天祥曾在给友人书中自明其志云:“某不量其愚,辄上书论其事,区区以为宗社有故,死亡亦在旦夕。不若犯危一言,有及于今日之难。其得祸与否,不计也。”《贺吴提举西林》,第152页。会不会导致“灾祸”?正是人们“为”还是“不为”的前提和基础,天祥独能“不计也”,实为高于和异于众人之处,此不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吗?后来,天祥一受御史黄万石以“不职”弹劾,二被人指为违反礼制不守孝道,被迫再辞官职,复返故里,悠游山水之间。二年后,才再授尚书左郎官。咸淳四年,天祥兼学士院权直,还兼国史院检讨官,但旋即又被台臣黄镛奏免官职。咸淳六年(1270),权臣贾似道以退为进,玩弄辞官致仕以求更大权力的把戏。恰此时,当文天祥受命起草挽留贾似道的诏书,他“裁之以正义”,按惯例,当先呈稿于宰相,而天祥独不遵循,贾似道极为不满,指别官改作,而度宗也采用了改作之辞,于是,天祥只得第四次辞官退职。贾似道不等其退,指使台臣张志立奏免其职。十年宦海生涯,让文天祥尝尽了世态炎凉、官场龌龊的苦头。他在回到文山故里之后,写给友人太博朱埴的信中说:“仆十年受用顺境过当,天道反覆,咻者旁午。七八月以来,此血肉躯,如立于砧几之上,齑粉毒手,直立而俟之耳。仆何所得罪于人?乃知刚介正洁,固取危之道;而仆不能变者,天也。”《与朱太博埴》,第163页。面对权臣奸相,邪恶小人,无端祸水,天祥都决计不退缩,不彷徨,“直立而俟之耳”,他曾自嘲说:“某碌碌不如人,独有愚憨,不能改其素。”《贺翁丹山兼宪》,第179页。“愚憨”之性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表现,真是可叹可感,可圈可点。德祐元年(1275),元帝忽必烈命伯颜担任最高统帅,率大军20万,水陆并进,打响了灭宋的最后一战。文天祥时任江西提刑,接到由谢太后下的《哀痛诏》及另一道圣旨,命文天祥起兵勤王。天祥奉诏泣涕皆下,仅三天,他传檄各地,招兵买马,甚至毁家以充军资,很快聚军一二万人,共赴国难。他的朋友对其行为表示疑惑,说:“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回答说:“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几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可保也。”《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第9819—9820页。天下官宦多矣,而官品高于天祥者亦比比皆是,为何在南宋朝廷面临灭顶之灾时无人起兵呢?当然都是考虑到如此做的结果必为“驱群羊而搏猛虎”,所以,他们都是“知其不可而不为”者。天祥则不然,明知此“为”必败无疑,却义无反顾,以一介书生率军勤王,这仍然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所至。从宋德祐元年到元至元十九年,是文天祥几乎每时每刻面临死亡胁迫的七年。天祥曾在《指南录·后序》中记之甚详:“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发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傍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
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指南录·后序》,第479页。三次“当死”不死,又继之以自刭死、傍徨死、“无不死”、“送死”、“落贼手死”、“迫死”、“陷死”、“无所逃死”、“捕系死”、“邂逅死”、“无辜死”等等,身临死境其自称达十八次之多,真是“痛何如哉”。可天祥却得以不死,这是其生命旅程中的奇迹。但是,应该看到,若天祥在派往蒙军大营议和时便接受劝降,早已享荣华富贵了,怎会经此九死一生?也许在生活中,人们可以为某种动机放弃一些可能带来利益的行为,但是,“生”还是“死”则是人生中最为根本、最为严峻的问题。文天祥人生态度最为感动人心的恐怕并不是其中状元,名耀神州,亦非其在朝与地方为官吏时的骄人政绩,甚至也不在其奋起抗元,转战万里,而是他视死如归、知“死”之可避而不避,知“生”之可求而不求的精神。观文天祥的一生,除在科考上的辉煌之外,就陷入了政坛上与奸佞小人、权臣宦官的苦苦抗争,在三十七岁前,先后罢官贬职达六次之多;其后天祥奋起抗元,除在江西战场上小有胜利外,可以说是屡战屡败,最后被执,被迫亲见南宋小朝廷的覆灭,这对忠臣义士的天祥来说,何啻万箭穿心,痛不欲生?真可谓是求生不能,求死又不得。最后他身首异处,惨遭杀害。人生坎坷艰难困顿凶险,莫如天祥一生之为甚。那么,为何他在如此局促穷途短暂的人生过程中,还能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为底气,昂扬向上,奋发有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明大儒亦是状元的罗洪先在仔细研读文天祥事迹之后感叹道:“人之遭蹉跌者,往往回顾而改步,三已不愠,古人难之。今罢而仕,仕而复罢,经历摧创,至于六七,志愈坚气愈烈,曾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为之所者矣。”《重刻文山先生文集序》,第807页。天祥与常人完全不同的是,他遭百般蹉跌却从不改悔易辙,此究竟源于何?而支撑文天祥如此行为的“为之所者”又是什么?简言之,是儒家先圣先贤“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资源,是文天祥关于“命”、关于“道”(“理”)的思想和学说。生死追求:“命”与“理”(“道”)的合一“知其不可而为之”本就是儒家创始者孔夫子的主要精神。《论语》中记载:“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朱熹集注:《四书集注·论语·宪问第十四》,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92页,下引该书均只注篇名。盖春秋末期,各诸侯逐鹿中原,攻伐无度,斯文扫地,诚所谓“礼崩乐坏”,而孔子却汲汲于复周礼倡仁义道德的事业。朱熹在注释中认为,“晨门”是“贤人隐于抱关者也”《四书集注·论语·宪问第十四》,第192页。,他以“天下”无可救药,是“不可为”的。他抓住了孔夫子“知其不可为”而偏要为的特点,但他并不理解:
其何以能如此?其何以一定要这样?其实这与孔子的道德天命观有紧密的关系。孔子一生皆系于恢复周礼、提倡仁义。“周礼”主要为政治和社会的准则,“仁义”主要为人伦道德的准则。既然是“准则”,必对政治、社会和个人行为形成某种约束。这在纵横捭阖于天下者和沉溺于声色犬马者看来,皆为无形的桎梏,必欲破之而后快;但在孔子及儒生们看来,这些皆是“天”之“命”人所遵之“道”,必欲树之而后快。可是,孔夫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天下大乱之际,其所推行的东西显得迂远而疏阔,不近事理也不近人情,因此,“贤者”会叹为“不可为”。但是,虽然孔子栖栖遑遑,“席不暇暖”,“干七十二君无所遇”,其意其行却反而更加坚定,个中关键就在孔子沟通了外在的“命”与内在的“道”。“命”者,一般皆理解为“命运”,一种冥冥中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所以,孟子云:“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四书集注·孟子·万章上》,第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