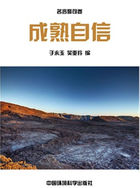教化宗族,本来就是宋明理学家一大努力方针。理学家论经世,主要思路即在于此。例如:
△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者,使之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族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正蒙·经学理窟》)
△ 凡人家法,须令每有族人远来,则为一会以合族,虽无事亦当每月一为之。古人有花树韦家宗会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类,更须相与为礼,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为不相见,情不相接尔。(《二程先生书》 卷一)
△ 宗子法坏,则人不知来处,以至流转四方,往往亲未绝,不相识。今且试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术要得拘守,得须是且如唐时之庙院,仍不得分割了祖业,使一人主之。(《二程先生书》 卷十五)
本来,宗族内部只是一种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要被赋予道德意涵,并要求作为实践之规范时,才能成为伦理关系。譬如近代名种狼犬,亦多附有血统谱系证明书,但这种证明书,就丝毫不带有伦理之意义。而在宋代以前,宗族即未被赋予这样的关系。因此宗族也没有应去实践道德的伦理义务。
在上古,姓氏宗支的亲疏及祭祀关系,实与继承和分配统治的权力有关,故宗法制度之建立,基本上来自“世卿”之事实。魏晋以来,中古之世族姓望,用以别士庶,所谓“立品设状以求人才,第士族以为方司格,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张即之,《蓝溪李氏族谱序》)。二者均不以族内伦理关系为主要内容与功能。宋代以后,才讲族内孝悌义务,并企图由敦睦亲族而达到整个社会都能风俗淳化的目标。张载和程伊川之说,可为代表。
南宋时,吕东莱与朱熹推广此意,更是不遗余力。如吕东莱的 《宗法条目》,就是推衍发挥程子这一类想法的重要著作。《宗法条目》 名为宗法,易令人以为是古代的封建宗法制度,其实不然。因社会变迁,古宗法制早废了,宋人托古改制,讲的乃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宗族组织法。此法之基本原理,是把宗族血缘关系转为契约规定,而这种契约规定又实现了伦理价值,不会显得只是一套法制规约。其目共列有祭祀、忌日、省坟、婚嫁、生子、租赋、家塾、合族、宾客、庆吊、送终、会计、规矩、学规等项,分别说明其行事规范仪节。揆其内容,殆与宋代自温公以下迄朱子之“家礼”一脉相通,亦与朱子制定的 《白鹿洞书院学规》 相通。
朱子撰 《家礼》,自谓是“愿得与同志之子,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朱文公文集》 卷十一),显然也与程颐、张载的用心无异。朱子在 《跋三家礼范》 中,更自任司马光之后,把厚彝伦、新陋俗的工作,视为他与他朋友同志们共同的事业,说:
呜呼!礼废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长沙博士邵君渊,得吾亡友敬友所次三家 《礼范》 之书,而刻之学宫。盖欲吾党之士,相与深孝而力行之,以厚彝伦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张之言犹颇未具,独司马氏为成书。……熹尝欲因司马氏之书,参考诸家之说,裁行增损,举纲张目,以附其后。
其欲参考增损,即是“采集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广传之,庶几见闻有所兴起,相与损益折中,共成礼俗”(《跋古今家祭礼》)之意。移风易俗,而一再强调家礼祭祀,正是希望透过这些制度,让人能体现亲亲孝弟之心。乾道四年(一一六八)九月,吕氏又推广宗族宗会法之义于社会,云:
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同志者规之;规之不可,责之;责之不可,告于众而共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朱文公文集》 卷十)
这个乡约,事实上就是再将宗族亲睦合会之法推拓到社会上去,是族谱族规的扩大,故后世往往也将它并收到族谱族规里,因为内涵是一样的。宗法条约转化着血缘宗族,乡约则转化着地缘团体。朱熹对此乡约也极为重视,特“取其他书及附己意,稍增损之,以通于今,而又为月旦集会续约之礼”(见 《朱文公文集》 卷七四 《增损吕氏乡约》)。
换言之,宋代理学家努力地以重定族谱功能、建立宗法条目、编修家礼、组织宗族宗会等办法,来改造宗族,把一个血缘团体变化成为有道德义务且须努力实践其伦理规定的团体。再由一个个宗族,拓展到一个个乡,以乡约化民。
因此,书院讲学、家族宗会、乡里会约,内在是一致的,只是对象施用范围略异而已,以此化民成俗,亦以此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