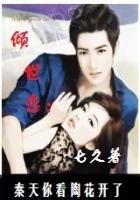水仙花沿岸盛开,我不由得联想到汲水而来的姐妹。
一样的倒影,一样纤巧的手指,高傲地拘留住泡沫的裙据。她们的掌心把玩着大大小小的月亮,一举手一投足都有雨点般的露珠摇落。她们的梦在水上,变形成一盏灼灼的渔灯或一朵花;她们的梦在我的梦里。
也就是说我梦见了另一个梦。另一个做梦的人黑发飘散,仰泳于湖面,像半柄被雷电打断了的木桨。水仙花沿岸盛开,我踏上她未竟的旅程,心儿被潜在的叶掌温柔地划动,直至浪花溅湿了我的脸。
我在自己手掌的蒙蔽下闭上眼睛,不敢回望尾随而来的火红鱼群,它们吐露出成串成串的心事,使我的想象变得轻松而又易于幻灭。有时候我想以背影铺设一张虚空的网,或许能拦截住往事的游离;上岸之后欲要炫耀自己的不无收获,却发现增添的不过是那么几个狭隘的心眼……
水仙花惆怅地盛开,我的眼神在空想之间一明一灭。
更多的日子独坐花丛,凌空抛弃莲子的暗语,以猜测你迟到的归期和失落后的水温。于是一群手提裙据的水妖应召而来,又踏浪而去,使我在短促的间隙失去平静,误以为超脱的身世花团锦簇……
很久以后我才察觉自己已置身对岸,横渡的草鞋沾带有前世的浮尘。不堪清算它载歌载舞之中涉及多少条假设的河流,横陈于水上的花园,使我误入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