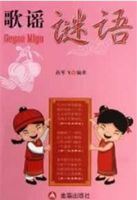爱情是痛苦的。只有当你出现在我身边,爱情才可能带来短暂的欢乐。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距离,相当于城市的这头到那头,骑自行车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仅仅是个比喻,更确切地说,我们属于两个世界。我有我的大漠孤烟,你有你的小桥流水。在别人眼中,我作为雾都孤儿式的落魄无产者,是无缘结识你这位小布尔乔亚的贵族女儿的。如果真的在街上擦肩而过,我也很难有勇气抬起低垂的眼皮,打量你这样的很明显生长于温室里的花朵。我是旷野上一棵土里土气的树,除了风,从不寄希望于谁来做我的朋友。然而你,还是透过褴褛的衣裳、憔悴的神情认识真正的我——那是一颗未曾经历过月蚀与污染的心的形状,像粘带着两片绿叶的毛茸茸的山桃子,我可以信手用剪刀在纸上剪出来给你看。
你恐怕是以欣赏野生植物的心情来接近我的,你信赖地走进我不见阳光的小屋,背靠墙壁坐着,倾听我谈起萧条时期的诗歌、理想以及就一位流浪汉而言不可能贫乏的人生阅历。你惊讶地扑闪着睫毛:“你居然去过那么多地方,而且有那么多故事?”这帮助我醒悟到自己富有的一面,我在你湿漉漉的目光笼罩下恢复了滋润。西北风在窗户外面响着,我和你面对面坐着——中间是茶杯、书、烟灰缸以及假设中的葡萄藤蔓,全世界宁静得仿佛只有两颗心在跳动。风越来越小,我觉得茅草的屋顶很结实。这一刻啊,你在我身旁,即使给我一座珠光宝气的宫殿,我也不愿搬家。我对世界保持沉默,然而面对你时永远是演讲者的姿态。我的往事,我的未来,我的海洋般折叠的心灵书卷,只可能在城市里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对你打开……然而爱情又是痛苦的。送你回家,从这个车站转乘到那个车站,曲曲弯弯,漫长的告别仪式,只听见车轮磷磷作响,街灯的光芒像一层神秘的面纱撒在你的脸上。我从熟悉里看出了陌生,从温柔里看出了忧伤——一个人仰躺在草地上凝视夜空时常常会这样,星星的语言无法破译。在颠簸的无轨电车最后一排座位,在黑暗中,我的心像盛水的瓷罐哗哗作响,又尽量克制着不让你听见。你对我笑了一下,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明亮。
真不敢相信啊,我居然还会爱别人——在物质挤压的时代,千疮百孔的个人主义帐篷里,我首先失去的是这种信心。然后就是生命中温柔的全部丧失。我像块石头般在楼群与楼群之间走动,经历了烈日当空的持久的蒸发,性格变得干涩、硬朗。我不敢接触爱情,生怕给姑娘们带去嚼刨花般枯燥的感觉。在无人知晓的黑夜里,我很坚强,也很安全。如果不曾遇见你,恐怕我的一生都会这样度过。
当我为刀枪不入的年龄而自诩之时,你出现了,微仰着满月般无可挑剔的少女的面庞,走过了北京沙滩北街103路车站,时间是1994年3月某日下午两点钟。我高筑的防线,我流浪岁月里的自尊与冷漠,溃不成军。我冻伤过的心如果确像一枚半青半红的桃子的话,那么正被我的两只手掌捧着——像接受了两片绿叶的委托,呈现在你系着北方风格的花格纱巾的胸前。我居然还会天真地爱一个人——这种感觉比具体的爱情事件更令我喜悦。
为了抵达你所代表的世界,我顶风践踏沉重的命运齿轮,像铁鸟横渡茫茫人海,穿过千差万别的面孔寻觅你温馨的窗户。我呼啸着冲撞树枝、镜框、旗帜或者歌谣,栖落在你附近的草坪上——小块阳光投射在上面,明察秋毫般梳理我蒙满灰尘的羽毛。你用木桶拎来了古典意义的井水,你用花朵般的小手蘸着,擦拭我易碎的玻璃心——那大大小小的伤痕,顿时奇迹一样愈合。
正如疼痛消失得突然一样,爱情到来得突然,不容我做任何准备。我沿着一向忽略的万家灯火,回到城市边缘的小屋——揿亮灯海中最后的一盏,晕眩的瞬间,我仿佛看见你了,看见你背靠墙壁坐在一幅世界名画下面,等待着倾听我谈论诗歌、理想什么的。你扑闪着睫毛,惊讶地凝视我用钥匙开门的动作。我不敢伸出怀疑的手,我几乎就要触摸到你温存的衣饰。这就是你的幻影,它已在我心里扎根。室内郁闷了一整天的空气,似乎都遗留有你披肩长发的香味。
我真的不敢伸出期待的手,那样我会像盲人一样,在正午的黑暗中触摸你在我记忆里呈现的轮廓,永远地寻找,永远地胆怯——直至事实与自身的梦想完全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