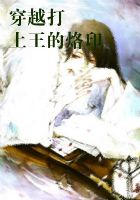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化社会,对一个缺乏权威的中央政府持怀疑态度。这一点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中也可看到。从一开始,美国的大学就背离了其源于英国的基本原则,同时在许多方面也背离了欧洲大陆的模式(尽管后来受到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影响)。正如基奥恩(K eo-hane,2000)所说,最初在17世纪由来自英国的移民所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和英国的大学是类似的。由于各地发展的需要,殖民地也需要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才来为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服务。第一批学院,诸如哈佛(Harvard)以及威廉和玛丽(William and M ary)等学院,它们被授予颁发学位证书的权力,同时具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那样的居住与建筑方面的环境。最早的课程重点关注本科生的自由教育(liberal un-derg raduate education),这种课程教育受到各有关图书馆的必要的支持(在那个时代,很难从其他来源获得信息)。
这种殖民地的遗产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结果。首先,每一块殖民地和后来每一个州对于它们自己的学院都有一种权威和自豪感,这种权威和自豪感一直被保持着,并以此抵制联邦政府过多的干预。其次,任何想要成立一所国立大学的计划从未被付诸实施。相反,就像社会上普遍流行的那样,采用的方法是多元的,即机构的多样化,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和以移民为基础的社会,艺满足这种社会各种各样的需求。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只能由各种不同类型的机构来满足。但是,高等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民主的和经济上的必需品(不管其形式怎样)。
考虑到美国的大学起源单一,产生以下这种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即来自别处的结构模式———例如讲座教授职位制度(欧洲大陆),或者研究员(fellow s)的民主(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开始就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可是,由于缺少现有的学术声望,以上这些设想遭到了拒绝,于是准备采用一种新颖的方法,该方法基于强大的校长权威,而这种权威受到有许多地方和外界代表参与的理事会(trustee)和董事会(boards)的支持。这种模式最终在20世纪由于一种力量的作用而突出起来,这种力量就是私有企业的行政管理和领导风格对大学的影响。由于大学对团体捐赠和学费的依赖以及大学和各种公司之间逐渐形成的紧密联系,其结果是,私有企业对大学的影响加强了。和欧洲大陆许多国家不同,例如,美国的大学校长和教师是自主的和“独立于政府”的从业人员,他们不是政府雇员。这也许促进了大学的事业和创新,而创新逐渐成为美国“多元化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的特征,也形成了大学为广泛的社会利益服务的职能,使大学和各方面建立起多种联系。这包括大学早期设置一些新的和具有实用倾向的学科,诸如工程和食品生产等。它有助于强调:大学对全社会有广泛的义务,而不仅仅是对自己或只是对知识的探究负有责任。
“二战”后,帮助许多退伍军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有助于改变大家对谁应该上大学和什么年龄上大学这些问题的看法。就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对受过教育的人员的需求、对持续不断的科学发现及其应用的需求,所有这些导致了联邦政府对大学的干预,例如通过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对研究和发展的资助(这方面经常出于军事目的,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时冷战激化了)。但是具有教育意义的是,就本科生的教学而言,政府的干预是通过对学生的资助,而不是直接资助学校,这就强化了高等教育中美国式的“学生是消费者”的观点。
可是联邦资助的增长最终也许已经抑制了美国制度多样化的程度,刺激了公立和私立大学两大部分的会合。今天,私立学校比以往更依赖于公共资金,而公立学校却被鼓励扩展其慈善和承包商的活动,以便补充其经费。然而,尽管美国大学的传统一直是招收社会各阶层的子弟入学,但是名牌大学(诸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举世闻名。一流大学继续努力地采用各种基本的方法来教育学生,使学生适应社会的需要。这些方法能增强学生的信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品格———这些性格和精英的身份与“有进取心的”领导人的身份是相称的。
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从一开始就面向各种市场,同时要求高等学校适当地回应那些市场(如果这些学校想要生存的话)。和英国以及欧洲大陆不同,在美国没有中央政府的慷慨赠与可以依靠,也没有像英国国教会那样历来对大学的捐赠(国教会希望通过这种捐赠来保持它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同时也保持其神职人员供给的来源)。自由也许是对多数大学和学院的一种准确的描述(如果在某些地方有点不可靠的话)。但是,随着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尤其是在那些积极向上和有抱负的移民中,而他们对进入大学的准备却常常是不充分的),回应市场意味着以下观点在现实上是难以接受的,即所有学位应具有一个可比的标准(例如,这个要求在英国是被强烈地坚持着的)。由于缺少公共资助的“安全保障”,在美国要维持像英国大学那样一种普通的和高的标准,这就意味着许多学院和大学要漫天收费以致使自己失去市场。就标准而言,学校的生存需要多样性而不是共性。较低的收费和标准是一种市场化的观点,这种观点被大量增长的入学人数所证明是正确的,这也使得某些学校要寻找其特有的专门市场并在经济上得以生存。
因此,为什么美国高校的体制具有多样性(例如其特征包括不同的标准与课程、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与地区的学生的广泛入学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种制度本身的要求,即要求在一种市场的环境中保持学校的运转,而在这种环境中,资助一般是由直接“花现钱”的消费者提供的,而非由国家安排的第三方代理人提供(“模拟市场”)。然而这是一种由“有多少愿望就有多少需要”的情况所造成的多样性。较穷的学校热切地希望获得那些具有较高地位的大学的声望和市场力量(有一位优雅的教父来施舍大量的资金,它们必定会模仿市场的领导人,而不管其担负着什么样的任务);而富裕的学校总是感到有来自邻近的或国外的竞争者想要吸引更多的资金并在地位上超过自己。精英学校因此就表现出好像它们也很贫穷。
马丁·特罗(Martin Trow,1979)曾提出一个有趣的论点,即美国在一个世纪前就已有了一种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尽管当时还未达到那个今天被用来判定一种高等教育制度是否是大众化的数字标准。也就是说,美国的高等学校在制度上是开放的和多样化的,它们欢迎各种各样的追求者,而无需在保持一种选择性的或精英式的凝聚力时维持一种一般的“金本位”的标准。技能而非文化造就了驾驶员。因此学生人数的增长并未导致整体转换或过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出现在诸如英国或澳大利亚等国的体制中,精英式的目的已不得不被嫁接在那里,而同时高等教育也日趋大众化。在美国,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结构最初在体制上就已被设计进去了。
此外,由于缺乏一个能够或愿意来管理学院和大学的中央政府,美国的竞争性市场已不断地被巩固了。就绝大部分而言,州政府(而非联邦政府)已控制了高等教育,各种决定和资源一般是面向消费者和那些最关心消费者的学校。只是在近些年中,英国对全日制的本国学生收取学费,而取消维持性的拨款是根据美国的方式所采取的“顾客至上”的态度,但是中央政府的资助仍然保留着,尽管这种资助近来有所减少,但对多数学校来说,它还是一种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美国,资助教学的公共资金多半通过各州的政府流入大学和学院(而非直接由联邦政府提供),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干预也不是很多。
在美国(现在英国越来越也是这样),高校在招生时进行竞争的一个方面是,学生逐渐被认为是已按照他们的志愿“选择”进入大学。因此,大学逐渐对它们的学生有一种所有权的感觉,这也许就少了一些傲慢的作风,大学的感受反而如同一家私立或商业性的公司在寻求扩大消费群和加强消费者对品牌的信心时的感受。与此相对照,就绝大部分而言,欧洲大陆实际上一直把学生上大学几乎看成是一种享受公共福利的权利。在别的地方(诸如澳大利亚),“使用者付钱”也已更具有了“消费者至上”的特征,那里的做法是学生在本州上大学,这就抑制了学生在地区间的流动,也阻碍了大学想从国内更广的地区吸引最好的本科生的竞争性努力。欧洲大陆的大学也已倾向于经常资助大量被分配给它们的学生,在近来公共支付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出台以前,这些大学普遍对于本科生花多长时间获得学位一事漠不关心。
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具有自治和独立的悠久传统。它们看来重视其自己本地的根基和特性。相比较而言,英国新成立的地方院校考虑到自己缺少保障、考虑到其是地方创办的院校因而具有狭隘的地方观念,所以它们的态度一直是寻求国家和中央政府的庇护(从20世纪初在诸如曼彻斯特、利兹和诺丁汉等城市创立的“城市大学”,到20世纪60年代高级技术学院获得大学的称号,再到20世纪90年代多科技术学院改称大学,都是如此)。牛津和剑桥大学显赫的学术名人,国内和国际的声望,处于最高的地位(在伦敦),中央的保证基金等,所有这些东西的诱惑结合起来,对于多数院校的领导人而言就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对于这些主要是地方建立的大学来说,来自中央的支持(包括政府的资助和管理)已被大学副校长们认为是一种解放(而非压迫)的行动(至少在过渡时期是这样)。其结果是:就一所“好的”(proper)大学看起来应该怎样这一点而言,英国比美国具有更大和更长期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