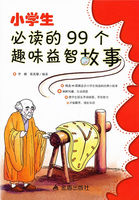此行就要结束,我们有点慌了。可看可做的事情太多,语言差异教人气恼,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已达到此行的目的。我们跟很多俄国人接触,但我们希望得到解答的问题,是否真的已得到解答呢?我虽把各种交谈、琐事,甚至天气预报都做下笔记,以备日后整理,但还差得远。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掌握到的是什么。美国报纸大声疾呼的问题,如俄国军备、原子弹研发、劳工奴隶、克里姆林宫政治欺骗伎俩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完全没有这些事情的相关消息。没错,我们是看到很多德军俘虏在清理自己所造成的破坏,但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太不公道的事。当然,我们并没有确切资料。的确有很多军人,但纵使有大规模军事备战,我们也并没有看到。换个角度说,我们并不是来当间谍的。
最后,我们尽量多看看莫斯科。我们跑去参观学校、去跟女商人、女演员和学生聊天。我们也到买什么东西都得大排长龙的商店。留声机唱盘发卖的消息一宣布,马上就大排长龙,不出几个小时便销售一空。新书上市的情况也相同。我们到莫斯科不过两个月,俄国人的成衣供应似乎已大有改善,同时,莫斯科各大报也纷纷宣布面包、蔬果、马铃薯和纺织产品降价的消息。各大商店总是人满为患,只要是店里有得买的东西几乎全都抢购一空。几乎完全移作战时生产的俄罗斯经济,已慢慢恢复平时生产,被剥夺必要和奢侈消费产品的民众,涌到店头购买。冰淇淋一到店头,队伍立刻排得好几条街长;批到一箱冰淋淇的人,抢购者蜂涌而至,生意好得来不及收钱。俄罗斯人特爱冰淇淋,再多也不够分配。
卡帕每天打听。现在他已有将近四千张负片,每天担心得要死,但每天所得到的回答都是没问题,裁定很快就会下来。
莫斯科作家的晚宴在一家维多利亚式餐厅内举行,作家协会三十位作家和干部到场,其中包括西蒙诺夫和伊利亚·爱伦堡。这时,我已到了一闻到伏特加就反胃的地步,根本不能再喝。格鲁吉亚的无甜味葡萄酒倒是还满可口的。这种酒有数字标志,看到六十就知道是浓红酒,三十则是淡白酒。这些数字虽不一定准确,但我们觉得四十五号不含糖分、清淡,口感甚佳,很适合我们,因此我们常点这种红酒。还有一种类似的无糖分香槟也很不错。这家餐厅有个格鲁吉亚乐团和几名舞者,食物也和格鲁吉亚当地相同——依我们的口味而言,算是全苏俄最好的。
人人都穿起最好的行头,但我们的衣服还是相当邋遢。事实上,我们是出了洋相,可人儿拉娜有点代我们感到不好意思。没有人穿晚礼服。其实,我们在此行社交场合中没见过有人穿晚礼服。外交官可能有晚礼服,但我们不太清楚。
晚宴上的谈话既冗长又复杂。在场的人大部分都在俄语之外还会某种外语,如英语、法语或德语。他们希望我们此行愉快,且已获得想要的资料,并一再举杯祝愿我们身体健康。我们回答说,我们此来并不是探查政治制度,而是要看看一般俄罗斯民众;我们已跟很多人见过面,希望把所见所闻的客观事实告诉美国民众。爱伦堡起身说道,我们若能这么做,他们会铭感五内。坐在桌尾的男士接着起身道,事实有很多种,我们应该拣可以促进俄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事实说。
这话立时引起争论。爱伦堡跳起来,发表不留情面的谈话。他说,告诉作家该写什么等于是一大侮辱,一个作家既以说真话著称,就不该对他提出任何建议。西蒙诺夫立即声援爱伦堡,谴责适才发言那位男子,而后者只能心虚气弱地自我辩白。奇玛斯基先生想说话,可惜辩论不休,淹没了他的话。我们常听说俄国作家之间界线严明,绝不容许争辩,依晚宴上的情况来看,这话似是完全不实。在卡拉加诺夫先生一番调解之后,晚宴这才平静下来。不喝伏特加,改以葡萄酒相敬,也许会被人看做是孬种,但我的胃舒服多了,当个健康的孬种又何妨。伏特加跟我就是不合。11点钟左右,晚宴在宾主尽欢中结束。没有人再胡乱告诉我们要怎么写。
我们已经订了机票,三天后就要离境,但照片通行证还没下来。卡帕郁郁寡欢。美国大使馆人员和各特派员待我们十分亲切,我们觉得应该举行个鸡尾酒会辞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蒂芬斯是极少数在莫斯科有房子的特派员,别人都以旅馆为家。可怜的史蒂芬斯因此膺选,纵然不愿也没有办法。我们拟了宾客名单之后,赫然发现该邀请的人起码上百位,史蒂芬斯家客厅可以充裕容纳的人数却只有二十人左右。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们原以为有些人不会来,怎知竟是料错了。一下来了一百五十人。在莫斯科,酒会是赏心乐事。的确是场欢乐酒会,只可惜饮酒不多;屋里挤了太多人,几乎不可能举杯就口,而且一举杯就无法放下。史蒂芬斯很快就困在角落上脱不了身,当然也就无法顾全大局。
我们深深感谢大使馆人员和特派员的协助和鼓励,此外,我们更觉得他们在艰困的环境下表现极为出色。且不说别的,这里可能是全世界最严酷的政治舞台,绝对说不上是最愉快的地方,但他们并不像当今许多人一样糊里糊涂。我们称许从大使到为大使馆重新架线的T/5小组整个团队。
我们即将在星期天早上离境。星期五晚上,我们到波尔肖剧场欣赏芭蕾舞,一出来就接到一通急电。文化协会的卡拉加诺夫来电告知,说外交部终于有消息了:我们的底片每一张都得经显像和检查通过才能出境。至于这三千张底片的显像工作,他自会安排人手。若是在这最后关头才动手,我们真不知要从何着手。他们并不知道,其实所有照片都已显像。卡帕把负片全打包好,一大早信差过来取走之后,仿佛是母鸡走失了小鸡一般,整天来回踱着步,懊恼得无以复加。他打定主意,没有底片绝不离境;他宁可取消订票,绝不同意底片随后再寄给他。他在房里嘟嘟哝哝踱着步,洗了两三次头,却忘了要洗澡。若要说起他的苦恼和痛苦,生孩子只怕不及其半。没人要看我的笔记。其实,就算他们要看也不打紧,反正没人看得懂。连我自己也有难以卒读之感。
我们花一天时间分别向众人话别,并答应会把一些难得一见的好文章寄给他们。我们暗忖,可人儿小约有点舍不得我们走。我们虽偷了他的书和雪茄,用了他的衣服、肥皂和卫生纸,又怪他威士忌存量不足,辜负他殷殷待客之道,仍觉得他舍不得我们走。
卡帕一会儿在琢磨若是底片有差错,就来个“反革命”行动,一会儿又考虑索性自裁了事。他思忖,不知能否在红场行刑台砍下自己的脑袋。当晚我们在豪华大饭店办个伤别酒会。音乐比平日更嘈杂,我们取名为“茜查丝小姐”(匆忙小姐)的吧女,动作比平日缓慢。
我们摸黑起床,最后一次赶到机场,最后一次坐在斯大林肖像下,恍觉一身勋章的他正揶揄地冲着我们微笑。我们喝一样的茶,这时卡帕已吃起牛肉干。信差一到便把一只箱子塞到他手中。是个硬纸箱,盖子以细绳缝妥,绳头上有小铅印。他得等到抵达布拉格前的最后一站基辅机场通过后才可以碰铅章。
卡拉加诺夫、奇玛斯基、可人儿拉娜、可人儿小约前来送行。我们已把可以舍弃的东西,如衣服和夹克、相机和多余的镁光灯泡、未曝光的底片都送人,行李轻便了许多。我们上机坐定。到基辅得花四个小时。卡帕抱着纸箱,但不准打开,否则,一旦铅印坏了就无法通关。他掂了掂箱子。“很轻,”他可怜兮兮地说道,“只有一半的重量。”
我说:“搞不好他们放了石头,里面根本没有底片。”
他摇了下箱子,“听起来像是底片。”他说。
“说不定是旧报纸。”我说。
“去你的!”他说罢便自顾自地心口相商。“他们会拿掉什么呢?”他自问道,“全都是无害的东西嘛。”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喜欢卡帕的照片。”我说道。
飞机飞过森林与原野处处、河流如银带般蜿蜒的大平原。秋高气爽,蓝色轻岚悬浮地面。女服务生送粉红苏打给机员回来,自己也开了一瓶。
晌午时分,飞机滑行进入基辅机场。海关人员草草地检查一下我们的行李,但立刻拿起那箱底片。他们已接到通知。有位关员将细绳切断,卡帕有如受伤的小羊般在一旁观看。关员全面露笑容,挥挥手走了出去,关上机门,发动机发动。卡帕颤着手打开箱子,一见底片差不多全在,不由得微微一笑,头朝后一仰,飞机还没升空便沉沉睡去。他们取走一些负片,但数量不多。他们拿走的是暴露太多地形的底片、那张斯大林格勒疯女的远距照片、囚犯照片。不过,从我们的观点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农庄和人像、俄国人民的照片纹丝未动,而这些正是我们此来的主要目的。
飞机飞过边境,在午后降落布拉格,我不得不摇醒卡帕。
终于到了。我们大致不虚此行。正如我们所料的,我们发现俄国人也是人,也跟别的民族一样亲切。我们所遇到的人都憎恨战争,他们跟所有的人一样,所要的只是美好生活,增加舒适度、安全感与和平。
我们很清楚,这篇纪行会让如日中天的左派和落魄失意的右派同感不满。前者会说它反俄,后者说它亲俄。它的确是失之肤浅,不然又能如何呢?我们不做结论,只不过,俄国人跟世上所有的人一样之外,坏人当然有,但更大多数都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