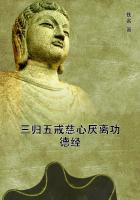当作红色教材来读的。那时的阅读,不仅投入,甚至如饥似渴。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能供我阅读的选择范围非常有限,古今中外的许多优秀作品,都因种种缘由,而被挡在我的文学视野之外。我不知道,也没有人指导我去寻找“红色经典”以外的好书来读。这样说,并不是简单否定“红色经典”,实际上,其中的优秀作品,即使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感动。当然,关健仍取决于你如何解读。作品还是那些作品,但时代与读者,却是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的。一个读者走到人生的秋季,他对作品的领悟,与少年、青年时比,肯定会有不同。试想,一个青少年会在20世纪60年代初思考有些作品何以成了“经典”,且被冠以“红色”吗?不会。当今年轻人喜欢时尚,动辄就成了某颗“流星”的崇拜者。我们年轻时何尝不也是这样?
我初次阅读“红色经典”,离新政权从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不久。所以被称为红色政权,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崇尚红色。红色是血的颜色、火的颜色、红旗的颜色,这种颜色昭示着以往的斗争的光荣,也象征着胜利者的自豪。就连我小时候加入少先队,也被告知:胸前佩戴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由无数先烈的鲜血染成。在那个年代,红色是一种象征,象征革命,象征正义,象征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人的精神修养所能达到的境界。于是,那些描写革命历史题材、塑造英雄形象的文学作品自然就被赋予红色。这,体现了国家意志,也代表了当时社会思潮的方向。何谓“经典”?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典也者,典章、法则也。不难理解,当人们将上述作品信奉为“红色经典”时,是相信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和不可更改的权威性,应该对千秋万代的读者起到规范思想、端正行为的作用。当下,颇有人在重新挖掘红色资源,走红色之旅,翻拍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除了经济因素外,也不排斥有人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强调红色资源的教科书价值。重读“红色经典”的意义,在我眼中,恐怕更在于通过不同时期阅读同一部作品之比较,加深对自己所走过的和正在经历的时代的体察,并由此反观自己的心灵历程。
然而,文学毕竟是“人学”。无论文学的创造者,还是作品表现的我初读“红色经典”的时代,是一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且要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时代。“斗争”“革命”是那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于是,“红色经典”表现的对象,似乎除了斗争,还是斗争;所抒发的情感,似乎除了革命,还是革命。课堂上,老师告诉我们,《青春之歌》是写小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成长的历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出版前言更是介绍作品“犹如一幅政治历史画卷,描绘了乌克兰地区一代革命青年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下,为保卫红色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而英勇奋斗的革命历程”,而主人公保尔“就是无产阶级战士的典型形象”;《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的妻子在为中国青年读者写的文章中也说:“最重要的,是要在生活和日常工作中把他(即作者伏契克——笔者)作为模范,要不倦地学习工人阶级为争取新的、美好的世界而进行的伟大历史性斗争,积极地参加这一斗争,并在促使它走向胜利的过程中,无论遭遇到怎样巨大的牺牲和考验,也绝不逃避。”……在这样一个阅读政治化的氛围中,我也就糊里糊涂地被那种潮流裹挟着,懵懵懂懂地接受了流行观念,认定这些作品确实如此,只能如此。其实优秀作品如果确实优秀,绝不止一种颜色,而会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彩。与其说,伴随着我成长的那些流行读物(它们当年可真流行啊,其流行程度大概超过现在的任何一种畅销书),本身就是“红色经典”,毋宁说,它们是在传播过程中被框定成单一的红色,并被指令性地“经典”化了。原因在于红色政权需要文学在熏陶接班人方面发挥作用。
对象,抑或文学的接受者,虽然都会因为特定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氛围,而不免带有特定印记,但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其精神世界并不能彻底被格式化成单一的模型。“红色经典”本身及其在不同时期被接受的境况差异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这一代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人,大约很少。小说的封面上,主人公保尔跨战马、手举钢刀,呼啸着向敌人冲过去的形象,鲜明地体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与读者对此书的基本理解:这是一部表现战士在革命熔炉中百炼成钢的作品,但对小说所写的保尔哥哥和铁路工人杀死监视他们的德国兵时闪现的内心怜悯,对谢廖沙第一次在战场上挥刀砍向敌人时的心理波纹,以及对作品一再写到的谢廖沙那双温柔的蓝眼睛,却并不在意。这些在当年被读者所忽略的情节和细节,倒恰恰表现出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虽然无愧为暴风雨中成长的战士,但其心中依然淌着人道潜流,无论战争多么残酷,斗争多么尖锐,都不能使其干涸。当年许多评论津津乐道于保尔与冬妮亚的决裂,从而论证爱有阶级性。可我在少女时读保尔与冬妮亚初次邂逅,及其以后的纯真相恋时,总是免不了情为之牵引,心为之颤动,甚至暗暗为他们的分手惋惜。这说明了什么呢?即便是红色作家,在描写不具政治色彩的人类情感时,也难掩内心喟叹。这或许还表明,即使有意识形态的强势诱导,但读者心中仍保留着一块柔情的领地不受浸染,故随时都会为纯美的情感战栗、悸动。或者说,那些被钦定,继而被公认的“红色经典”,本身并不像坊间所想象的“红”得那么纯粹乃至单色。
我还清楚地记得四十年前初读《青春之歌》时的感受。林道静一身雪白的装束,曾让我钦羡;卢嘉川的英俊、潇洒、英勇、顽强及其内敛的情感方式,使我神往;林红的高贵、坚贞,让我崇敬;对余永泽,我曾那样顺从地随着作家的笔触,从颇有好感一步步走向讨厌、鄙视、憎恶。四十年后重读,我对卢嘉川、林红、林道静的看法基本没变,对余永泽却多了一份理解和同情。他,一介书生,爱妻子,爱到将她视为私有财产,对臆想中的情敌满怀嫉妒;热衷于经营安乐窝,对时局缺少兴趣,对学潮不像职业革命者那般投入,其实不难理解,虽然理解不等于认同。谁有权苛求所有的人都务必投入洪流,成为战士呢?当一味谴责余永泽自私、猥琐、落后,进而将他列入被鄙夷、憎恶的行列,其实也就是在想象中剥夺了他选择自己的人生的权利。是那个将“红色”指定为唯一有“存在正当性”的颜色的年代,才让缺少阅历的青少年,自以为是地将自己也未搞明白的流行观念再强加到别人身上。
初读《牛虻》,不免赞赏牛虻的忠贞、英勇与坚韧,而对蒙泰尼里,当时总有声音在提醒我,这是一个阴险、狡猾、虚伪、残酷又极具欺骗性的主教。甚至有评论说,作品写的亲子之爱和男女之情,全是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观念,不足为训。如今,当我走出盲从的时代和年龄,重读《牛虻》,就意识到当初我不敢流露的对蒙泰尼里的同情,倒是符合人性、人情的。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社会理想和思想倾向,是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比如,当伏尼契借女主人公琼玛的口说,用暴力胁迫政府只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目标是为了改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提高民众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为了提高他们对人性的神圣的认识——便极深刻。想想《牛虻》中父不认子的情景吧,难道不是因为蒙泰尼里受宗教戒律的束缚不能自拔,无视人性的神圣造成的吗?改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人类长远的奋斗目标。历史上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都是假革命的名义,谋求以一个政权替代另一个政权,使专政的对象掉了个个而已,哪里有改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目标来得彻底呢?我进而想,假如真能敬畏人的生命价值,认同人性、人道的神圣,历史上将会避免多少惨绝人寰的悲剧啊!还有一些东西,是我过去读作品时,因为不理解而故意回避的。比方说,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写到他从牢房押送到另一个地方受审的路上,常常在囚车上数女人的秀美的腿,如果超过了九双,心中就认定今天可以活着回到牢房。当时,我真纳闷一个视死如归的英雄何以会对女人的腿感兴趣,而且还以所见数目的多少来推测自己的命运。我读不出其中的幽默,也不明白这正表现了英雄坦然地面对死亡,却误以为这有损于英雄形象。又比如,伏契克在“遗书”中嘱咐妻子或朋友,在他牺牲后应结集出版其作品,稿费用来维持他父母晚年的生活。当时读到这里,在为他对父母的拳拳孝心感动的同时,又惊诧他为什么不像我在中国作品中看到的英雄那样,心里装的只有党和人民呢?又不敢说,只好避而不谈。
重读就是反思。朋友说,反思是一种负责任的清理:剔除该剔除的,拾起曾被我们忽略的,重新认识该保存的。非常深刻。反思替某些读物插上红色标签的那些岁月,反思我们曾经信奉的思想理念,反思我们对那些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其实也就是反思我们曾走过的那段历史以及我们曾奉为圭臬的价值谱系。其意义将远远溢出对“红色经典”的怀旧式猎奇。
重读“红色经典”,确实使我体味到了“温故而知新”的深意。
2006年11月
何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