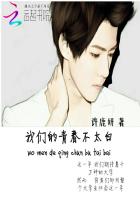我的短篇小说《鞋》,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确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但不管什么奖,一得到就算过去了,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在考虑今后的创作,并在心里对自己提出要求:不要因为得了奖就萝卜快了不洗泥,也不要因得了奖就不敢写了,该怎样还怎样。
可有朋友热情相约,让我谈谈关于《鞋》的创作动机和创作过程,我勉强答应下来。一篇小说,发表时快乐一回,收到稿费快乐一回,得了奖又大大地快乐一回。这些都是快乐。而谈小说背后的事情,唤起的就不一定是快乐,有时可能是一种渺茫的思念,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回忆。说实在话,《鞋》这篇看似很美的小说,写的却是留在我心中的一段隐痛。
我1967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当了农民。那时大队时常召开大批判会,因为我识字,难免被指定在大会上作大批判发言。之后大队成立文艺宣传队,我也是其中一员。这样一来,全大队五个自然村的不少姑娘都知道我了。我有两个姐姐,她们为我挑中了一个姑娘,意思是可以作为我的恋爱对象。我那时十六七岁,对姑娘们的看法没有什么标准,也没什么主见,很容易受别人影响。既然两个姐姐都认为那个姑娘好,肯定有她们的道理。再说姐姐是用姑娘家的眼光看取一个姑娘,能被她们看上,说明那个姑娘是经得起挑剔的。还有一点我后来才知道,两个姐姐为我挑对象时目光放得很远,她们不仅为我着想,连我的后代都想到了。比如说我的个子比较低,她们就要给我物色一位高个子的姑娘。也就是说,姐姐为她们的弟弟挑选对象是很理性很慎重的,也是很负责的。我留意把那个姑娘观察了一下,姑娘个子高高的,胖胖大大的,很有劲的样子。姑娘一笑眼睛弯弯的,牙又白又齐,看上去还算顺眼。于是姐姐托了媒人,我和那个姑娘在媒人的撮合下会了一次面,谈了几句话,亲事就算订下来了。
接着姑娘就该给我做鞋了。当年我们那里很少有人买得起鞋,一般都是手工做布鞋穿。人们常年在田里劳作,对鞋的消耗量很大,纳鞋底子是妇女们手中最常见的针线活。我母亲、姐姐,稍有空闲就纳鞋底子。生产队或大队开会,妇女们舍不得闲着,差不多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只鞋底子,一边听会一边纳,把会场里纳得一片哧哧响。由于见得多了,我对做鞋的整个工艺过程非常熟悉,写起来心到手到,一点都不费劲。定过亲的姑娘给对象做第一双鞋,跟平常做鞋又不一样,一是它有着很强的规定性;二是有着仪式般的性质。这双鞋的重要性我在小说里已经写得相当充分,这里就不重复了。反正这双鞋不仅是物质性的,更是精神性的,它的象征性和隐喻性,都包含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鞋文化。
不断有人向我报告消息,说那个姑娘在为我做鞋。那个姑娘下地干活,还把没纳完的鞋底子带到地里去了,趁工间休息时纳几针。那个姑娘怕把鞋底子弄脏,把鞋底子包上了手绢,每次开始纳鞋底子之前,都是用清水把手洗了又洗。鞋底子纳好了,那个姑娘犹嫌不够洁白,用漂白粉擦了一遍,又用硫黄熏了一遍。每听到一个消息,我都美气得不行,心头鼓荡着一种不可言传的情愫。给我的感觉,鞋本身的使用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姑娘通过给我做鞋的过程,传达给我的是一种无限美好的情感。这种情感深深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时间越久越醇厚绵长,让人难忘。
姑娘把鞋做好了,在我到煤矿参加工作之前把鞋送给了我。我把鞋带到矿上,一开始对鞋十分爱惜,看了又看,就是舍不得穿,想留作美好的纪念。后来买了运动鞋、网球鞋和皮鞋之后,回头再看那双方口的布鞋,觉得它过时了,已经穿不着它了。关键还不在这儿,关键在于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想自己谈恋爱,自己找对象。这时,我给那位姑娘写了一封信。说是一封信,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希望能看到姑娘的一封亲笔信。我听说那个姑娘上学很少,想试试她会不会写信。姑娘给我回了信,她的信也很简单,只有几句话,至今我还记得。她说她永远都不会变心,松树落叶都不变。尽管如此,第一次回家探亲,我还是把那双鞋捎回去,退给了那个姑娘。我自以为做得很高明,不说退亲,退鞋就意味着退亲。那个姑娘接过鞋,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就这样,我们的亲事就算吹了。
如果我不写小说,这件事也许过去就过去了。因为我是个业余时间写小说的作者,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我只要一回忆起过去的事,那个姑娘,那双鞋,就不声不响地浮现在我的脑子里。特别是我后来听到的一些事情,使我对那位我家乡的姑娘产生了愧疚感,心里渐渐地有了隐痛。听我母亲说,我外出参加工作不久,那位姑娘去我家看望过我母亲,并对我母亲说,她担心我会退亲。由于担心得整夜睡不好觉,她的头发掉了好多。听我姐姐说,那个姑娘嫁人后,日子过得很不如意。她回娘家必须经过我们村的村头,而她每次从我们村路过都不敢抬头,生怕别人认出是她。我想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辜负了那个姑娘,并伤了人家的心,我一辈子都对不起她。我还想到,我要是不把鞋退给她就好了。鞋是专门给我做的,退给她,她毫无用处,看见鞋,只会让她更加难过。
懊悔是没有用处的。我怎么办?我所能做的,只能是把这件事情写成小说,通过小说写出我心中的隐痛,并表达我的愧疚之情和忏悔之意。
其实这个意思我已经在小说的“后记”里简单表达过了,那个“后记”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绝非可有可无。林斤澜老师看破了我的用心,他在点评我这篇小说时特别指出:“这篇《鞋》的‘后记’,我认为当属‘翻屋’,是比较成功的一例。短篇更要锻炼技巧,这个结尾可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