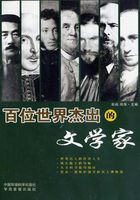莫言说:《四十一炮》中的一部分曾经作为一个中篇在《收获》发表过,这是1998年的事了。在《收获》发表时,小说题名《野骡子》。这部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小说的叙事主人公罗小通在跟随母亲收购废品时,曾经收到过一对从山里来的老夫妇用骡子驮来的一门红锈斑斑的迫击炮。他如获至宝,用砂纸把炮打磨得锃明瓦亮,像宝贝一样收藏着。好像是契诃夫说过,如果小说的开篇描写了墙上悬挂的猎枪,在小说结尾之前,一定要把它打响,否则这样的描写就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当你在小说中写到了猎枪的时候,读者已经产生了期待,期待着你找个理由把它打响。《野骡子》只有三万多字,没有机会让罗小通把炮打响,但我知道,他应该把炮打响,这就决定了《野骡子》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中篇,而是一个长篇的部分。
事实上,罗小通的炮打响了,却又带来两个谜团,为何是四十一炮?为何打不死老兰?
至于“四十一”,莫言解释过:
这个小说有41个章节,小说里的主人公曾经得到了一门迫击炮,最后一章里面对他的仇人发射了41枚炮弹……在我故乡里炮有特殊的含义,说话喜欢编造的人叫“炮人”,这个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孩子,他们叫他“炮孩子”,所以我确定这个小说叫做《四十一炮》。
那为何不是二十一、三十一,而是四十一呢?没有人给出答案。我感觉和对莫言影响较深的一部苏联电影有关,就是《第四十一》。这部电影莫言在谈论战争叙事的时候提到过,故事是说一个红军女战士亲手杀死了四十个白匪军,在押送战俘的过程中与一个白匪军官意外流落荒岛,日久生情,忘记了各自的阶级立场,而当白匪的大船来荒岛营救的时候,白匪扑向大船,女战士的阶级观念被唤起,她开枪打死了第四十一个白匪。可见,第四十一个就是神来之笔,变化之处,也是女战士在面对真实的自我和阶级的自我的时候所产生的矛盾纠结,让人唏嘘,也是荒诞的、不讲人情的。这跟《四十一炮》在探讨荒诞和人性上有一致的地方,就是实在很难界定“我”在谎言和真实之间的取舍,实在很难相信“我”是个可以抛弃一切只要有肉吃就幸福的人,自尊、父母、良知、是非,都可以不管不顾,最为诡异的就是集中攻击老兰的那“第四十一炮”竟然没有打死他。四十一又很适合一部长篇的章节长度,所以用“四十一”仿佛顺理成章。
为何打不死老兰?老兰实在是个很传奇的人物,在“我”和大和尚的叙述中,还有个有着漫长性史的兰大官当亲戚。在罗小通的儿童视角中,老兰是个亦正亦邪的人物,他理应趾高气昂,因为身份和财富在村子里首屈一指,他理应和一切对他不屑一顾的人为敌,或者对他不服气而又受人敬重的人比高低。父亲罗通先是在肉市上因为自己的眼力,仅仅靠眼睛就能分辨肉牛的毛重与出肉率,受到屠户们的尊重;还有一点就是在对野骡子的追求当中,父亲赢了老兰。这两点引起了老兰的挑衅,但却因为一头发狂的牛反倒让父亲救了他。老兰与父亲的恩怨并没有到此结束,后来父亲和野骡子私奔,老兰反倒照顾罗小通母子俩,在父亲回来之后,不计前嫌一起开起了肉类加工厂。
后来因为言语相讥,让罗小通成为孤儿,罗小通与妹妹的屡次复仇却始终没有把老兰杀死,老兰反倒活的越发滋润。老兰没有死,并不意味着他品德高尚,反倒他就是新式注水猪肉的研发者。罗小通也对老兰有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恨这个人,另一方面却崇拜他。老兰的不死其实是一种普遍的状态,这个社会不缺少这种人,这种人可以还过得更好,罗小通杀不死他,意味着社会上人们就是这样半谴责半羡慕,多半内心还想成为这种人,以至于老兰生生不息。
2
罗小通就是莫言关于饥饿的另一个变体,这种变体多次出现在莫言的小说中,在《四十一炮》里是嗜肉的,在《丰乳肥臀》中是恋乳的,在《铁孩》中是爱铁的。可见,莫言在用对吃的极端夸张去营造一个反饥饿的世界,一个餍足的世界,也是一个非理性、没原则的世界。这其中往往含有讽刺,比如“五通神庙、肉神庙、肉食节、吃肉大赛、谢肉大游行”等无所不用其极的“肉崇拜”,代替了原始的对于神灵的崇拜,正好预示着现代人信仰的缺失,人人都为“肉”这种外物所迷,自然对精神匮乏满不在乎。莫言说: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罗小通就是我。但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了”。
为何是?因为感同身受;为何不是?因为毕竟是个叙述者。
罗小通嗜肉,可农民偏偏往肉里注水,这跟以往莫言在叙述农民生存时的朴实与苦难书写大相径庭,其实这不过是一种直面市场化真实的写作,莫言说:
“农民的疾苦我也写到了,我写罗小通的饥饿感,我认为这个小说里面是通过罗小通的嘴巴来讲述故事,罗小通的观点不能跟我的观点划等号,我应该跟书中的人物有一个距离感,他们的观点是他们的观点,我不愿意用我的观点来批判他们的观点。农民往肉里注水,在这个小说里看起来注水很有道理,我们不注别人也注,大家都注,我不注,我就无法生存,有人买了我的注水肉,我们吃的药很可能买了一包假药,我们买的化肥很可能是假化肥,我们抽的烟很可能是假烟,在这种虚假的社会里,这是令人担忧的一种现象。”
其实,以往莫言的小说是习惯性与社会脱节的,我们看《红高粱》、《食草家族》等很少会引起共鸣,仿佛在看别人的故事,但在《四十一炮》中虽然依然荒诞,但有一点是共情的,满嘴放炮的“谎话精”罗小通和满目谎言的市场一样都充斥着虚假,一旦到了吃什么都不安全的时代,到了村长老兰带领大家往肉里注水,甚至添加福尔马林防止猪肉变坏的地步,《四十一炮》让农民以往的朴实瞬间崩塌,碎了一地。
或者,在“食、色”的世界里,一定要有一些“食、色”之外的东西存在,比如“虚假”,这样才会让小说丰满的羽毛扯动本就一片灰蒙蒙的现实天空。
《生死疲劳》之“疲劳”的轮回
2006年,《长篇小说选刊》上登载了删节版的《生死疲劳》,最大的删减是把前面的“四世轮回”留下,删去了后面的“两世”。同时,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未删节版的《生死疲劳》。在我看来,《生死疲劳》是莫言最特别的作品,他一直试图做的改变尝试,这是最为成功的一次。《生死疲劳》有让人读第二遍或者是第三遍的魅力,这部作品在2008年获得的奖项也颇为诡异——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的第二届“红楼梦奖”。
第一届的获奖作品是贾平凹的《秦腔》,可见充满民间传统味道的作品更容易受到青睐。古典小说《红楼梦》偏偏是莫言没怎么看过的作品,但《生死疲劳》中轮回反复和奇幻色彩却颇似《红楼梦》里的佛道。
莫言近期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讲时,称《生死疲劳》的书名来自佛教经典,这本书也是他老早想为邻村单干户写的一部作品,但一直到了2005年,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正确方法。他认为佛教的很多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间的纷争在佛家眼里毫无意义,在佛家的这种精神高度下,人世间的众生就显得十分可悲。这故事,其实还是学习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席方平》,是莫言在中学课本上看来的,估计还是得益于哥哥的教材。主人公为他的父亲鸣冤叫屈,和阎王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斗争,阎王给他种种酷刑和好处,比如锯成两半,叫他投生富贵人家,都被他忍受下来。最后,终于要到了一个说法,二郎神给他父亲沉冤昭雪。莫言赋打油诗一首,专门向蒲松龄致敬:
装神胜过装洋葱,弄鬼胜似玩深沉。
问我师从哪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
遥想那古老的《红楼梦》,也处处充满轮回的影子,那株草来还眼泪,那块宝玉来体会尘世之苦。莫言在作品中加入了宗教色彩,就让《生死疲劳》带有神圣的意味,然而他还没满足,而是用跟自己亲密的动物勾勒这幅长卷,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在瑞典给读者推荐就是《生死疲劳》。
1
在王德威看来《生死疲劳》涉及“如何解放历史”。莫言在轮回叙述中的确涉及对60年的共产革命史该如何解放,他笔下的主角是交错轮回的动物,仔细想来不过是把大历史还诸民间的一种方式,在“土改”、人民公社、包产到户、改革开放的历史叙述中,他的视角是用动物和孩童切开的一个小口,在这个小口中可以把原本沉默的东西用胡言乱语表述出来,看似不着痕迹,看似不知所云,看似地域与现实不是一个世界,却偏偏达到了奥威尔《动物庄园》般的效果,即便“莫言、狂言”却也“千言万语”,入情入理。
在《生死疲劳》里,最不解的地方就是地狱。地狱里的最高统治者是阎王,而阎王在中国的古老传说中,被认为是对一个人一生最后的功过认定的公正判官。现世的痛苦要人们把受苦的理由归结为上世的罪孽,转而去寄托来世,这样的“三生三世”仿佛是佛家给与人们最美的希望。无论中方还是西方,都在用死后的公正判定来厘清这一世的是非,无奈的是,莫言笔下这个本应该主持公道的判官,却也是贪官污吏,是非不分。小说一开头,就是地主西门闹喊冤叫屈,然而阎王不但不理还对其施以酷刑,来保证地狱里的安静太平。经过下油锅的酷刑,浑身焦酥的西门闹还是不依不饶,连阎王也承认西门闹却有冤屈,但就是不想主持公道,在以后的几世轮回里还常常不守信用,让西门闹投胎做了猪、狗。
莫言这样书写,多半也是为他重构历史的举动服务,只不过,他想采取更为夸张疯狂的方式。西门闹所经历的世界,无论是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文革”还是新时代,在文本中充满了混乱,官不是官,民不是民,这和地狱的混乱对照看来,就显得微妙了,世界如此慌乱,干脆就乱到底。天上地下无处说理。
想要贯穿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六世轮回中不让西门闹失去记忆,西门闹保留着记忆,其实就是在保留人性。可偏偏他不是人,他幻化成了各种动物,从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再到狗精神,最后才勉强成为大头婴儿蓝千岁。西门闹的英雄气息和他所表现出来的人性,跟各个时代具体的个人相比,要公正客观很多。也许就是因为时代的是非颠倒,莫言才把各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价值、道德判断一一呈现,再让自己笔下的角色进行反攻。在小说中,“土改”时期人人得而诛之的地主西门闹,却是个好人,他没有过多压榨,他本身也是勤劳的。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单干户也是各个村镇消灭的对象,而蓝脸却是忠实的捍卫者,他宁可死去,宁可孤独终老也绝不入社,就是单干。至于,西门闹转世的动物们,无一不忠心耿耿,个个都成为传奇。小说所诉说的单干缘由,仿佛给那个时代一种生命本身的活法:
“我曾听人说,正是因为我们的蓝脸,我们才单干,而且还有人说我们爷儿俩,白天躲着不见人,到了晚上,才出来耕作。我们确实有过几次借着明月光下地劳动的经历,但那与我们脸上的蓝痣无关。这些人把我们单干,归结为因为我们的生理缺陷导致的精神变态,这是放屁。我们单干,完全是出自一种信念,一种保持独立性的信念。”
而蓝脸最后坚持一个人不入社,原因是:
“我就是想图个清静,想自己做自己的主,不愿意被别人管着!”
可见,蓝脸想要固守的是在那个时代保持个人的自由,而不是非要在群体里没有自我地生存。
当那个稍微让人感到公正的阎王出现时,是西门闹的狗轮回,已经是九十年代,阎王换了人,他问西门闹心中可还有仇恨否?并说西门闹马上就可以进入人的轮回,西门闹也说自己没有了。阎王是守信的,西门闹成了进入轮回修炼的,这种改变发生在一个相对安静的九十年代,可是,却有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酷,或者因为在现实的轮回中是没有安静可言的,无论过多少世纪,人世间的恩怨情仇是完不了的,西门闹的这些轮回更像是一个逐渐劳累不愿再堕入轮回的过程,而不是他没有仇恨了。我们多半不想看到《西游记》取了经就天下太平了,我们想看到取了经还有经院的主人索要贿赂,大概因为没有哪一部经卷可以真的拯救苍生,就像没有哪一世轮回可以真的化解仇恨。我想莫言把蓝千岁写成一个患有绝症的儿童,并且依靠黄互助带有血脉的头发续命,照顾他的人还有蓝解放,这两个人一个是三太太的女儿,一个是二太太的儿子。冥冥中,莫言开启了另一种偿还的轮回,我以为,这还是在轮回中安排化解,只不过这次不是用“仇恨”而是“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