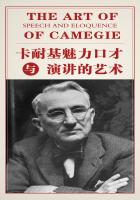《一》
很早以前,羊角村有一个小女娃儿,大伙都管她叫筐女。她母亲大概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生下她的。
可问题是,筐女的母亲那时估计还没有嫁人呢。就是说,筐女的母亲那时很有可能还是大姑娘家,至少没有正式过门吧。当时的情形谁也没有亲眼见到,所以对发生的一切都只是胡乱猜测而已。筐女刚一生下来,就被母亲丢在密麻麻的玉米沟里,而且是个傍晚,天色已擦黑了,估计只有那些星子,在高处模糊地看见了地上呱呱叫着的筐女。星子在人头顶不停闪耀着,一颗颗想要跳下来看个究竟似的。
那会儿地里干活的人都散了。在玉米沟里薅了一整天草的女人,都提起手里的筐子,筐子满当当沉甸甸的,把女人的胳膊吊得又长又细。筐里都是她们从玉米沟里拔下来的青草。这些草当然得顺路带回家去,兔子啦羊啦牲口啦都喜欢吃这种新鲜的青草。当时大伙儿拎着筐子,走出老远了,人都上了田,稀稀拉拉地走在回家的小土路上,所以,根本没有人注意到,筐女的声音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她就像一只拳头大小的狗崽或猫娃子,猛不丁扯出一串嘤嘤的泣音,在雾蔼蔼的暮色中,透出一股鲜活而幽忧的意味来。
若是碰上一帮大大咧咧的老爷们,这种赢弱的声音,通常是不会引起足够重视的,可女人就不同。她们的耳朵天生就有特殊的功用,这种婴娃的哭声,尤其能打动女人那根纤细的神经,也最能感染女人内心最脆弱的那一部分。她们听见了,就不能装作若无其事。女人的胸怀有时候也是很宽阔的,就像眼前这一望没边的青纱帐子,什么也能盛得下。女人们稍稍怔了一会儿,就顺着断断续续的哭声又摸索了回去。那些又长又宽的玉米叶子,一时间被女人嫩白的手臂撩拨得唰啦唰啦叫唤个不停。最终,几乎快走到玉米地的尽头了,女人身边的玉米叶子都不再乱叫的时候,才寻到了那哭声传来的准确位置。
这一大群女人顿时不言语了。
她们仿佛变成一棵棵结了丰硕的谷棒的玉米,都惊惶地围成一个圆圈儿,木呆呆地低着头,嘴角嗫嚅着,腿脚戳在玉米沟里一动不动。
要说也没有什么可稀奇的。这些女人多半都生过一男半女,娃娃都是她们身上的一块肉,生的时候就跟拿刀子割自己一样疼,等生完就没事了,伤口和疼痛像是永远消失了。但眼下的情形,还是让她们惊叹了一阵,又唏嘘了一阵。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猜疑着,半晌也没拿出一个好主意来。
这是哪个坏女人干下的?
咋能尻子一撅,就把娃娃养在玉米沟里!
女人们鸟雀似的七嘴八舌,彼此开始重新打量对方,似乎都在竭力怀疑:肯定是站在自己身旁的某个女人做下的“好事”。
婊子养的心肠比刀子还硬唼!
没良心的贱货,这是伤天害理哟!把娃娃狠心地撂在这里喂蚊子吃。
真格不要脸么!
谁说又不是呢……可怜见的……
就这样,她们围绕着扔在玉米沟里的那只筐子、和正在筐子里手脚朝天像只小青蛙样乱哭乱动的婴娃说起个没完。起先,每个人都愤愤然的样子,都恨不得立刻将那个坏女人从人堆里揪出来扇她一顿耳光、撕烂她的衣裳,或者带她去游街。
不过,这种打抱不平的想法,很快就被一颗颗怜悯和疼惜的心肠替代了。有个女人已经默默地蹲了下来,她把草筐子里的婴娃轻轻地抱在怀里了,并且,好像她就是这个小东西的母亲,嘴里羔羔蛋蛋地哄逗着,一副失而复得的惊喜样。
后来,女人们再次离开了玉米地,当然也带走了筐子里的婴娃。
她们轮流抱着那个女婴,不抱的也都很兴奋地提着盛满草的筐子前簇后拥。一路上有说有笑,仿佛再有多少个空筐子也装不下她们洒了一路的声音。
快到村子时,大伙终于从兴奋和愤慨当中理出了头绪。
首先,她们决定把情况向村里的男人们如实汇报,因为谁也不想不明不白地领养这个可怜兮兮的小东西;其次就是,她们对于这个婴娃的情况真的一无所知,她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村里面哪个女人的肚子悄悄地鼓了起来。为了方便起见,她们不约而同地管她叫筐女,就是盛在筐子里的女娃娃。这样非常好记,也不用动什么脑筋。旁人若问起时也好说呀,她是跟草筐子一起被大伙捡回来的,所以取了这么个名字。
有人说,应该先把筐女抱到村长家去,让村长拿个主意才对。
有人说,筐女肚子正饿着呢,还是赶紧回家,给她拌点面糊糊喂上再说吧!
有人说,怎么也得给筐女找身小衣裳穿上吧,最好在换衣裳之前,先用温水好好给她洗一洗。
有人说,真是可惜了的,筐女要是个长牛牛的就好了,那样的话准保大伙都会心甘情愿地抢着来领养她。
也有人说,你们几个看着弄吧,反正我是上有老来下有小,家里的事我还顾不过来呢,哪有闲工夫操心这个筐女?
大伙一边胡乱说着各自的想法,一边把筐女在每个人的手里传了一遍。她们都忍不住亲了亲筐女的小手和脸蛋儿。小人儿的皮肤嫩得简直无法形容,就连已经生过好几胎的女人,也都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之前她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观察或亲吻过自己的那些儿娃,可娃娃们已经不知不觉长大了,并且永远不再需要做母亲的这种亲吻。
于是,女人们都像占便宜似的筐女筐女叫着,亲起来就没完没了,弄得小家伙认生似的又呱呱地叫了起来。
到最后,筐女的名字就这样被她们叫开了。
村里突然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这倒不是什么坏事,可也算不得多好的事。
那些天村长带着两、三个曾在玉米地里捡婴娃回来的女人(其余的人一开始就打退堂鼓了,她们怕生事端,更重要的是屋里的男人不允许她们抛头露面),女人怀里轮流抱着那个婴娃,他们几乎跑遍了村里的每一户人家,他们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又摆事实又讲道理,希望筐女的母亲能站出来,勇敢地面对现实。毕竟,筐女也是一条命儿,就算是一条小狗,也不应该随便撂在野外不管不问。但这种劝说没有任何收效,相反,却惹怒了好几家的老辈人,他们气横横地把上门来的人连推带搡给轰了出去,并警告他们,不准再来门前胡说八道。
筐女的初来乍来,着实让村里那些欲嫁未嫁的黄花闺女紧张了好一阵子。
这些大姑娘平时去地里干活也好,还是随便出门转街也罢,总觉得有人在背后嘀嘀咕咕、指指戳戳的,总觉得旁人的目光正不怀好意地盯着自己的肚子、和走路时一扭一扭的屁股,好像非要从她们身上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以打消这种无止境的猜疑。
有两个姑娘已经订好婚的,双方都谈妥等冬闲了就办喜事。可不知什么缘故,好端端地事情就黄了,连媒人都一个劲直叹气摇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就连那个最初将筐女从玉米沟里抱起来的好心肠女人,这时也泄气了。村里的闲言碎语铺天盖地,有些人甚至恶毒地怀疑,筐女跟她或她家的男人有点关联,要不她怎么那么热心肠呢?看来,这件事弄不好她自己也会被唾沫星子淹没了。
这个女人终于在一天夜里,将睡熟的筐女悄悄抱到了村长家。她对一脸茫然的村长说,这活我实在是干不了了,你再另挑一个人吧。
村长本来是要发一通火的,可回头看看仍在睡梦中的筐女,和那两只红扑扑的小脸蛋,村长就把胸口的火气强压住了。他大概不想把这个小东西从梦里惊醒。
女人离开时,又从自己的脖项上摘下一条粉红色的棉围巾,轻轻地盖在筐女的身上,然后一咬牙,红着一双眼圈转过身,默默地出去了。
对于这个女人来说,一切仿佛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二》
羊角村有个专门看守场院的外乡人,一直住在库房旁边的一间小窝棚里。窝棚当然不是什么正经的房子,有点像牲口圈,不过四周是封闭起来的,虽不很严实,却也能挡风遮雨。村里专门用破草席、细木棍和从别处拆来的一堆旧土坯,在场院垒起一间又矮又小的土屋,让这个从外地逃荒来的外乡人住在里面。
这个来自外乡的老光棍汉多少有点奇异。这样评价他也是有些原因的。他好像不会说话,反正他到羊角村以来,还没有谁真正听到他说过一句完整的话。大伙都坚信不疑,他是个哑巴。因为他从不说话,大伙就无从知道他的名姓,私下里都管他就白脸、白鬼或白无常。这只是一方面。另外吧,这个远远看去悄无声息的人,却生着令所有人都发怵的皮肤,他身上的肉皮已经白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就像一只刚刚被揭去毛皮的老羯羊那样,膘皮雪白,却又布满了鲜红的血丝和红斑。外乡人的面皮、脖颈、手背、胳膊,甚至连头皮和耳廓子都是那种白里透红的古怪颜色,怵人得很。只要稍微看上一眼,就会心惊肉跳半天。以至于,他都在窝棚里住了好些年了,村里多半人都没有跟他有过任何的交往。
村长真是个精明人,将这样一个外乡人留下来看管库房和场院,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那年为了筐女的事儿,村长也着实犯了难。不过,村长眼珠子一转,立刻就有了主张。村长连夜把筐女抱到窝棚跟前,他指着筐女对外乡人比画了好一阵,意思是她跟外乡人一样,都没有地方可去。然后,就把筐女一股脑地塞到外乡人手里,好像塞一只没人要的包袱团。临走前,村长又把嘴靠在外乡人耳边(好像这样对方就能听清楚),喊着说,我看你一个人怪凄荒的,这个娃给你作伴正合适。外乡人一直不安地看着村长,又偷眼诧异地看看被强行塞给他的婴娃,两只白惨惨的手瑟瑟抖颤,仿佛捧着一团滚烫而又危险的物件。
不管怎么说,筐女总算在村里落住了脚。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出去。其实根本不用谁来传话,场院离着住户并不很远,一整夜恼人的婴娃的哭声,从那间低矮的窝棚里不时地传出去,传到每一家住户和他们的耳朵里,女人们一听就知道是她们从玉米地捡来的婴娃在哭号。不过,当她们确定下来哭声竟是从场院那边传出的,就有些坐立不安了。天亮以后,她们急忙差派自己家的娃娃跑到场院去察看,结果被告知,她们整夜跳动不停的眼皮所带来的焦虑,完全是事出有因。
天神哪,谁把好好的一个娃娃送到无常那里啦!
真是作孽哟……作孽!
女人们的眼珠子简直快要被这个不争的事实惊得飞出眼眶去了。她们无不觉得与其这样,倒不如当初根本别把筐女从玉米地里捡回来,就是让野狗叼走、让蚊子活活吃掉,也比交给窝棚里的那个流浪汉强。
一旦她们得知,这一切都是村长老人家的精心安排之后,谩骂的声音立刻减小了许多。不过,等她们被自己的男人从街上拉劝回屋里,她们还是会一个劲地埋怨,认为村长这纯粹是把筐女往火坑里推。
尽管如此,也没有一个女人再肯站出来,将筐女从窝棚里抱回自己家去收养。
也有极个别的人觉得,这样也好,那个白脸无常这回可是捡了个大便宜。因为像他那样的人,恐怕下辈子也不会讨到婆姨,而现在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个活脱脱的女娃儿,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福气呢!
《三》
那间又矮又黑的窝棚里有了些生气。
起初几日,筐女的哭声惹得一村女人还是提心吊胆的。
渐渐地,哭声没了,几乎再也听不到。女人们又开始怀疑,是不是白脸无常对筐女下了狠手?但是,娃娃们很快就向大人报告了白天玩耍时所看到的情形:说他们亲眼看见白鬼抱着筐女在外面晒太阳;说白鬼在窝棚跟前生火做饭的样子真可笑;说白鬼让烟火熏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一个劲在那揉眼睛;娃娃们还说白鬼好像在窝棚旁边的树上拴了几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块一块的抹布片……这些好奇的母亲听着听着,突然就打断了娃娃的话,并纠正说,你们懂个屁,哪里是抹布,是婴娃的尿布才对。
有一次,女人们正在地里干活,突然看见那个白脸男人忙忙慌慌地顺着小路朝村外去了。他走得太快了,简直跟跑一样,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眼睛尖一点的女人注意到,他怀里抱着一团东西,抱得很紧,跟他的胸口紧紧地贴在一起。
这一去就是多半天,天黑前才匆匆赶回来。女人们又在村口碰到他,他果然怀抱着筐女,神色惶惶。女人们仗着人多,壮着胆子上前摸了摸筐女,才发现婴娃的脑门烫手呢。不用问,筐女生病了,在发高烧。她们也由此得出结论,他八成是抱着筐女去外面的医疗站了。看来,这个白脸男人并不像大伙想象中那么坏,他还是有点良心的,至少知道给娃娃治病。
村里的鸡白天一般不在窝里蹲,都放开四处乱跑,找路上散落的谷米吃,也钻到庄稼地里啄虫子解馋。有的母鸡吃里扒外,偏把蛋随便丢在外面,有时也趴在场院里的草垛上下蛋。养成习惯,就会经常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下。主家经过观察,摸清了地点,到傍晚就爬到草垛上收蛋,几乎每天都不会空手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