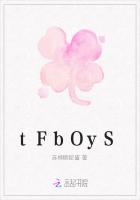我搭早班船去厦门。
江面上那些停泊着的货轮,还亮着几点灯光。两岸的树木、村舍,都睡意未尽地蒙眬着。天上的星星,稀疏地眨着眼。
舱内,乘客不太多。这早班船向来如此,除了像我这种去厦门办完要事在当天来回的,主要是做猪肉生意的商贩。
他们将里脊肉、瘦腿肉挂满椅背上,将排骨、猪尾骨披在坐椅上,就握着装上柄的刀片,忙着刮削猪蹄上的鬃毛,动作麻利得很,一只只猪蹄刮得光洁鲜亮。这样忙完了,船也就快到厦门了。他们把刮好的猪蹄,连同那些挂的、披的,收拾装袋,扎住袋口,准备上岸。
这早班船我常搭,舱内的景象,则每回必见。
我看他们刮猪蹄。一个中年男人掏出一包“七匹狼”,抖动几下,让香烟露出盒口几支,伸到我面前:“我手油渍渍的……”我明白他的心意,抽出一支点上,和他谈起话来。
“这么跑一趟,可挣不少吧?为什么不乘快艇?”
“我和我屋里的,”他指了指对面的女人,“连人带货,一趟来回,船费30多元。乘快艇就要70多元,那就差不多白跑了。”
“不至于吧?”
“你想想,我这些货到厦门,一斤平均赚一元,很好赚了吧?但除皮剥骨,也就挣个40元左右。你都看到了,这些东西不能封在袋里--馊了,谁要?--这样挂着、披着,吹风晾干,单失重就损失六七十元。加上一天的开销,一百来元呢。我们也就只是赚个零头而已。”
“你不知道,”他女人说,“我们这是和鬼在抢吃。天天3点就起来了,要跑几个地方向人家取货……”“你们不是到屠宰点取货吗?”我插问一句。“那你就得整头猪都要。卖肉的向屠宰点取整头整头的猪,我们再向卖肉的要我们所要的这些。”她用手中握着的刀片,对着那些货画一小圈,接着说,“取了货,就赶来搭船,一刻也不敢耽搁。回来,日头快下山了,家里老的小的,都顾不上。”
挣点钱养家,确实不容易。这谁都知道。
那中年男人将一只猪蹄刮好放下,又拿起一只刮着:“我们这都是两头定好了的,都要守信用。要是哪天没去取货,卖肉的把东西留着,找你要钱;厦门这边的酒家、饭店,你一天不送货,他生意损失了,要你赔。人嘛,哪能没个头疼脑热的?但病了,也得出门。反正吃一号饭、诵一号经,就是这样。”
……
船一靠码头,他们就争先恐后地上岸。我给他们让路,为我们这地方历来就有空身人给挑担人让路的规矩,为不妨碍他们争分夺秒地挣钱。
他们挑着重担,挤出舱门,在船头上相互间磕磕碰碰的,小心翼翼地走过跳板,上码头,急匆匆地去了。
我来到闹市的中山路上,许多店门还没开哩,还来得及说一声:“厦门,你早!”想来,厦门也会对我们,包括那些商贩,这么早就到厦门来的所有客人道一声同样的问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