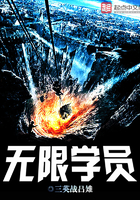冰冷的阳光打在我脸上,我这个乞丐一样的人无家可归。
我没有穿着破衣服,我没有在垃圾桶翻找食物,我没有饱含污秽折磨的双手,只有一样浑浊呆滞的目光。。
八月的太阳是恶毒的妇人,用最凶狠的手段鞭打着每个行人。这条街上人来车往,热闹非凡。太吵了,吵到我听不见任何一个人的说话。
我穿着长衣长裤站在人群中,四周充斥着汗味、烟味、香水味。没有人多看我一眼,哪怕我挡住了他们的路,他们还是低着头飞快的按着手机绕道而行。
我感到巨大的悲伤,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包括我自己。于是我开始嚎啕大哭。其实严格来说最开始我并没有哭,只是干嚎,终于自己被自己的嚎声所打动,终于从呆滞的眼中挤出两行带着眼屎的泪。当一个人自己感动了自己的时候,就是他最能发挥表演天分的时候。
我一声长啸,带着挤出的泪,清亮的鼻涕,白沫子口水,犹如向人群中投放了一颗原子弹。他们“哗——”的一下四散开来,其中一个吃甜筒的胖姑娘一下子跳起来,甩掉了两个冰淇淋球。我在表演之余对她笑笑,以示歉意。但我很快就回到了我的表演之中,毕竟笑太久就骗不了自己了。
惊吓之后,人们的好奇很快战胜了恐惧,以我为中心自动形成了一个圈。其实我实在没什么好恐惧的,只是一个矮个子的男人,瘦得像一根竹筷子。虽然我此时此刻的行为有些怪异,但我相信,一只狗都可以把我打翻。有人拿出了手机对着我拍,有人在打电话说在街上碰见了一个神经病,旁边人立刻纠正:“说不准是失恋了!”
后面的人拼命向前挤,想看看我这个狼哭鬼嚎的人到底长什么模样。前面的人拼命向后退,生怕我是个会吃人的怪物。我看见中间的人进退不得的难堪,忍不住开始大笑,差点忘记了表演。
我听见了所有人的说话声,看到身边围着的越来越多的人,越是卖力的表演。可惜体力不支,嚎着嚎着感到瞬间的头晕,不禁向后倒去。于是人群又是一片惊呼,纷纷往后退让,我“咚”的倒在地上。意识还算清醒,因为有什么东西磕着我的后背,疼的我说不出话来。我多么想有人拉我一把,让我站起来继续嚎叫,让我继续毫无意义的宣泄。
当然没人愿意。
我看着围上来的人脸,不得不以仰视的姿势低人好几等。阳光射得我眼睛发酸,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我向背后摸去,摸出一颗蓝色的玻璃珠子。我把玻璃珠子放在眼前,上面刻着两个字,蓝珠。我想这不是废话么,类似于在人身上刻上人字。
一个白裙子姑娘靠上前来,“你在这儿呀!我找了你半天!”我不知道她是谁,但是我立马答道:“是啊,我在这儿呀!”我火柴一样的身体被这个姑娘一把拉起。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没见过人啊还是怎么着!”姑娘发出与她纤细的身材一样尖细的声音,像一只叽叽喳喳的麻雀。众人作鸟兽状迅速散去,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去,一切回到十分钟前。
我坚持要把玻璃珠子放在眼前,好让我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
姑娘道:“走吧!”
我问道:“走哪去?”
“从哪儿来回哪去呀!医生说你现在还不能到处走动,你以为你还跟以前一样壮的像头牛?“
我有点不明白了,看样子这个姑娘跟我是认识的,可是她提到医生,提到以前,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周围实在太吵,我便对着她的耳朵说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姑娘叹口气:“你怎么又开始了。“
她拉着我挤过浑身汗臭的中年男人,挤过肥胖的妇女,挤过穿超短裙露脐装的年轻女性,挤过抱着小孩的夫妻,挤过带着狗的单身青年,挤过人山人海,终于找到一个阳光都不愿洒进的黑色小巷。
我盯着脚边一滩肮脏的呕吐物,还散发出阵阵难闻的味道,一群苍蝇围着它狂舞,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你叫王二今年二十二岁初中毕业没有文凭一直在洗车场给人洗车上个月十八号就是七月十八号你在洗车场被人撞了脑袋坏了医生说你得了短期失忆症每天睡一觉就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认识的人忘了你的过去总之就是什么都忘了。”
姑娘叭叭叭的跟我说了一堆,就像背台词一样通顺流利。王二?我怎么叫这么个名字,也太草率了,又不是什么连续剧里出现的路人甲。
“那你是谁?”
姑娘翻个白眼,继续道:“我叫白菲是你女朋友蓝珠最好的朋友你出事以后蓝珠就不见了就消失了反正就是谁也找不到她。”
蓝珠?我摸出那颗蓝色玻璃珠子,看着上面的两个字发呆。
“她是不是因为我出事了所以就不愿意见我了,就躲着我了?还有你说话能不能带点标点符号?”
白菲叹口气,“她一个大学毕业生跟你一农民工在一起七年了,要分早就分了。“
说实话我心里有点暗喜,没想到我竟然还有女朋友,而且看这个白菲的样子,那个叫蓝珠的姑娘肯定也不会差到哪去,人以群分嘛。
我的心情有些许好转,不再那么难受像吃了蟑螂还卡牙缝了一样慌张。
白菲继续道:“医生说你到以前生活的地方去走走看看也许会对你的记忆有所帮助,既然你都已经出来了,我等会儿打个电话给医院通知一声找到你了,再带你去你租的房子和你工作的地方去看看。“
我心里琢磨着,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是谁,也无法完全相信白菲所说的话,因为总有个说不上来奇怪的感觉,就像你身上痒痒,但是就是找不到准确的痒痒的地方,挠哪里都不对。不过反正我一男的,跟一女的单独在一起也吃不了什么亏。
我决定跟她走一趟,说不定真能唤回我以前的记忆。
白菲并没有给我太多考虑的时间,抓着我的胳膊便走,道:“你手上那颗蓝色玻璃珠子不是你送蓝珠的么,怎么又到你手上了?“
我道:“我不知道,我刚刚躺地上时这玩意儿就在我背后磕着我。“
白菲并未回话,只顾拉着我上了一辆计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