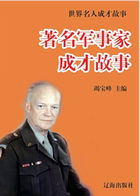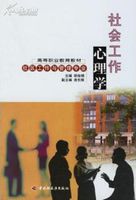大概是三十年以前罢,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疯子。
那时我不过七八岁,我的家乡的住了三代的老屋对门是一家卖水果的;他家除了沿街的两间铺面,后边就是一块空地,据说是“长毛”烧了一直就没有钱再造起。空地后边就是河,小小的石埠,临水有一棵老桑树和栀子树。就是他家,出了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疯子。
因为他家那块空地是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的好所在,我那时差不多天天到他家去玩的。他们是卖水果的,上午很忙,下午却空闲了,他们的小儿子阿四也许到城隍庙前的书场上听“程咬金卖柴扒”,他们的老当家就坐在铺门边的竹椅子上打瞌睡;和我们几个一般是邻舍的孩子在空地上玩耍的,总是他们的六十多岁的老婆婆,还有一位不曾许人家的二十多岁的姑娘叫做阿绣。我们不大喜欢阿绣。因为她拉住了我们不是问谁做的鞋子,就是问我们妈妈梳的新式的髻叫什么名字,再不然,就是捉得我们中间一个叫骑在她膝上,她使劲地摇,嘴里哼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调子。我们顶喜欢缠住了那老婆婆要她讲“长毛”故事。
老婆婆的“长毛”故事总从她家这块烧掉了房子的空地开头。她指着空地上一块半埋在土里的石墩儿,或者是那棵老桑树,就讲她那反复过无数次的故事。照例听到后来我们一定要怕的,我们先是大家挤紧在一堆,不敢再望一眼那石墩或桑树,然后,我们中间有谁忽然怪叫了一声,于是我们也都一齐叫起来,带怕带玩笑似的一齐跑进了屋子,老婆婆的“长毛”故事就这样从来没有讲到过尾巴。
我们跑进屋子去,十回有九回是找他家的左手两个指头缺了一节的阿三。也是卖水果的,但不及阿四那样会唱曲子似的叫卖,并且下午闲了也不上书场去,却躲在他屋里玩他的玩意儿。他会画红面孔大胡子的关帝,白脸的曹操,或者赤发金脸的奎星。他画奎星特别拿手。活像他家隔壁文昌阁上那一个。但是他画来画去只这三位,而且或坐或立,也总是那一套的样子。虽是那么着,我们却也看不厌,我们总是从空地上一哄进来就挤在他四周;他像有点嫌我们打扰了他似的,不过也不作声,正正经经画他的。有时我们中间有谁太放肆了,弄他的画笔,或是骑到他坐着的那张竹椅子背上去,那他就要慢慢地站起来,一脚踏在竹椅子上,右手拿一根他自家做的戒尺,举得高高地横在头顶,睁圆了眼睛,鼓起腮巴,朝那个太放肆的孩子“胡”地喷一口气。据说这是赵玄坛打老虎的姿势。于是我们都笑着拍手。但他的画儿也这样画到一半搁起。
除了画关帝,画曹操,画奎星,这位阿三又能塑菩萨。那一定是弥勒佛。也就在自家空地上挖点泥,晒干了研得细细的,然后搀了水塑起来。他的弥勒佛可不及他的画儿高明,只有那大肚子和拉开了的笑口叫人看了想到这尊菩萨是“笑弥陀”。然而那张笑口一定大得过分了一点。我们说阿三左手断脱的那两节指头可以给那小小的泥菩萨含在嘴里。阿三听了倒也不生气,——从没见他笑过,却也没见他开口骂人,他只是捧着他的作品横看竖看,看过一会,就悄悄地放在板桌上。等过一两天,泥菩萨不见了,他已经把它还原为泥。
阿三同他老子娘以及弟弟妹妹都不大说话。他们背后都说他有点疯疯癫癫,——一个疯子。那时我常常想:疯子也怪有趣的。
然而后来叫我第一次辨味着“疯子”这个名儿的意味的,却不是这阿三,而是他的弟弟阿四。
阿四本来是他家最能干聪明的人儿。他家的买卖是他一个人在那里主持。他看见了我们孩子总是笑嘻嘻的,有时还笑嘻嘻给我们一些水果,枇杷,金橘或者半个里半个的石榴。但是我们不常同他在一处玩,为的他除了笑嘻嘻,就是个没嘴的葫芦。他倒实在同阿三有点像,跟那也算能干姑娘的阿绣可就不像是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阿绣是顶爱说话,一天到晚咭咭刮刮只有她一张嘴。
现在我已经不记得怎么一来这个聪明能干笑嘻嘻的阿四忽然就疯子。我只记得那是在阿三失踪——大家都说他出家做和尚去了,而且在阿四娶了老婆以后。阿四这老婆,原是童养媳,然而据说领来后只住了半年光景就又颠倒寄养在一个乡下人家里,每月贴饭钱。这回是年纪大到再也搁不下去了,这才领回家来同阿四成亲。有一天,我照例到他家去玩,忽然看见一个陌生面孔的身材矮小的女人在扫地,阿绣就拉住我悄悄地说道:“这个新来的,就是阿四的新娘子。”
又过了几天,就听说阿四成亲了,我们看见他穿了新做的蓝布短衫裤,头上破例戴个瓜皮帽红帽结,一条老是盘在额角上的辫子居然梳光了垂在脑后;他本来生得白皙,这么一打扮,看去也就很像个新郎官。
但是娶了老婆以后的阿四却更加寡言,嘴角上的笑影也一天一天少见。晴天午后我们照常到他家空地上去玩,有时在门口碰着了他,也不像从前那样朝我们嘻开了嘴笑,也不再给我们什么枇杷之类,他却用了阴凄凄的眼光望着我们,或者,拉住了我们中间一个,钉住了看一会,于是忽然拍拍手,叹一口气,就自顾走了。他这拍手,后来成为一种习惯,——也许是他自己发明的表示烦恼的方法;每天早上我们刚起身就听得街上传来了拍拍的声音,我们就知道是阿四站在他自家门前朝天拍手了。晚饭时,我们在饭桌旁敲着碗筷等候开出饭来,也常常看见小丫头好奇似的跑来报告道:“对门的阿四又在拍手了!”那时大家听了也不过一笑,并没有想到那拍手是一幕悲剧的开头呀。
这样拍手的早晚课继续了一些日子,就又添出新花样来:是在拍手的时候又把腿用劲地踢。再过后不多几天,又添了第三项:嘴里嘘嘘地吹。早晚两次,他拍得吹得很响,一天比一天响,隔一进房子也分明听得出。好像他是因为要引起人家的注意,所以隔了几天就增加一个新的动作,并且把声音弄得一天响似一天。到这时候,人们就常常说阿四也有点疯疯癫癫了。不过他还能够照常做买卖。而且拍手踢脚嘘气的早晚课做过以后,他静默地不开口,一点异样也没有。
是有什么极大的烦闷在阿四心头罢?那时我并不明白。我只记得我们到他家去玩的时候,竟不觉得他家早已多于一个新娘子。我们,老婆婆,阿绣,同在空地上玩笑的时候,那新娘子从不露脸。而老婆婆和阿绣也从不谈到他家这个“新来的人”。有时我们凑巧早上就到他家的小石埠上钓鱼,凑巧那新娘子也在那里洗衣服,凑巧老婆婆和阿绣都不在跟前,那时候,新娘子就要笑迷迷地朝我们看,问长问短。原是怪和气的。我们都觉得她比咭咭刮刮的阿绣好。然而说不了几句话,阿绣就像嗅到了气味似的跑来了,一双眼睛怪样地东张西望。新娘子就立刻变成哑口,低着头匆匆洗衣服,我们问她话,她也不回答了。不一会,提着湿淋淋的衣服急急忙忙走了。这当儿,阿绣的眼光时时瞥到她身上,而她却头也不抬,似乎非常局促不安。
这样的情形,后来又碰到过好几次。我们小孩子也不大理会得。可是有一天,我和邻家一个小朋友在将吃中饭的时候闯到了他家去,阿绣和老婆婆正忙着做饭,空地上只有那新娘子一个人在扫地,她看见了我们不理,我们也自顾采了些凤仙花坐在一块石头上玩。她扫地扫到我们跟前时,忽然立定了,像要说话似的朝我们看。“新娘子!”我们这样叫着,我们是一直这样叫她的。她听得叫,就把脸色一板,拿起那芦花扫帚的柄,用手比一比,意思是这就算人头罢,却把右手扁着像刀似的砍在那扫帚柄头,低声喝一句“杀”,又伸手偷偷指着厨房那边。她那神气是这样的阴森可怕,我们都忍不住惊叫了起来。她连忙对我们摇手,淡淡一笑,就走了。这一幕哑谜,我那时不懂得,就到现在我还是不很明白,但那时我的孩子的心似乎也依稀辨到了阿绣和新娘子这两个女人中间好像有仇似的。什么仇呢?我那时当然不会知道。我回家把这事情告诉了大人,他们都喝我“不许多说”。但后来,我听得烧饭的老妈子悄悄告诉我祖母道:“对门的老婆婆不让她儿子在新娘子房里睡觉,都是阿绣搬弄口舌。”于是我确定阿绣和新娘子有仇了。我的孩子气的心倒是帮着新娘子这一边。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觉得她比咭咭刮刮的阿绣好。
这以后不多几时,母亲忽然禁止我到对门去玩,说是他家的阿四当真疯了。我不大肯相信,却也当真不去玩了。因为他们一家的人似乎都有点变样了:老当家午后不再坐在门口的竹椅子里打瞌睡,却上书场去了;老婆婆代了老当家坐在那里,却老是叽哩咕噜骂些我听不懂的话;阿绣呢,脸总是绷得紧紧的,脸上几点细麻子分外明显,看去叫人怕;阿四连生意也不肯做了。
早晚两次的拍手踢脚嘘气,阿四仍然没有忘记。不过又新添了一项:嘘气的时候叫着两个字,仿佛是“杀胚”,这两个字使得我们孩子听了很怕,以为疯子者就是那么想杀什么人的罢,同时我每逢听得他这么叫,我就记起了他家新娘子用扫帚柄比着头低声说的一字“杀”,我觉得他家迟早总要弄出杀人的事来罢。
但是有时在街上远远地看见阿四,觉得他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只在走近了时,才看得出他的眼光不定,面色青白;而且他像避猫的老鼠似的在人们身边偷偷地走过,怀疑地偷相着别人的面孔,似乎一切人都会害他。
不是他想杀人,倒是他怕被人家谋害罢!——我常常这样想。
两年后进了学校里去住宿,我就只在星期日回家的时候还听得阿四仍然做着他的早晚课,但听说他的老婆已经被他的老子娘卖给乡下人家又做新娘子去了。我听得了这消息就忍不住想道:“那家乡下人是不是也有一个像阿绣那样的咭咭刮刮的大姑娘?”
新娘子去后,阿四似乎有一个时候比较安静。人们说他间或也做做生意了。但不久忽然又发作起来,不吃饭睡了几天,起来后就站在门口骂人,不知他骂谁,人们也不去理会他。就我所知,阿四骂人,这是新记录。
以后就添了一项新功课,早晚两次站在大门口骂人。走路的人谁朝他看了一眼,他就要骂;骂些什么,从来没有人听得明白。
这样也继续了半年光景,终于有一天阿四也同他哥哥阿三似的忽然不见了。过了半月,有人说镇外近处河里浮起一个死尸。阿四的老子去看了回来说:“不是阿四!”究竟这人到哪里去了。始终没有人知道。
卖水果的这两老儿,就剩了咭咭刮刮的大姑娘阿绣。她还在“待字闺中”,虽然年纪总快要三十了。而这阿绣,后来永远是那样咭咭刮刮,也不用担心她会疯。“因为她是这样咭咭刮刮,所以不会疯罢?”——我常常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