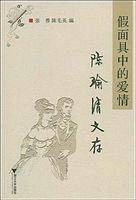他们两个一声不响地躲在灌木丛里,大气也不敢出。他们屏住呼吸,警惕地听着不远处嘈杂的脚步声,它们时远时近,时轻时重,显然是他们不甘心离去。
直到最后的脚步声在空气中消失,他们这才站了起来,只感到浑身酸痛难受极了,因为他们从一大清早到现在已蜷缩了大半天。他们从低矮的灌木丛里探出半个头来,又警惕地望了好一阵后,他们这才真正放心地相拥在一起了。
他说:“现在,我们自由了。”
她的身子仍颤抖着:“自由了,我们去哪里自由呢?”
自由后该去哪里呢?仍然回那个小村庄吗?当然是一个十分愚蠢的想法!
“我们肯定要逃,逃到天涯海角,逃得越远越好。”他用力拥住她的腰身,坚毅的嘴角挂着一丝胜利后的喜悦。
“不!”她竟抬起头果断地回绝了他,“我想,我们还得回去。”
“回去?你不是疯了么?”他吓了一大跳,涨红了眼瞪她,“你父亲和那个大款男人我们怎么去打发?我们逃吧!”
“不!”她从他的怀里挣开来,竟然一脸平静说,“我想了,我们还真和要回去。
他涨红了的眼睛淡了下来,正午时的太阳的光线使他很轻易地看清了她迷离而又俊秀的表情,这正是他熟悉而又欣赏的东西。他一直默认着一个女人在大事面前能拥有这些是一种无言的美丽。可现在它却成了他们之间的一道障碍。
他把眼从她的脸上移开。灌木丛里的深处,顺着山势长就的林子泣着贼亮的青色,有几只快活的小鸟跳跃着,“蓬的——蓬的——”拂动的声音毫无乐感地点缀在午时的空气里。
还是回去!这几年他们不就是等着这一天么?四年前,他俩从离村20多公里的乡里回来就私立了终身。他说他挣够了彩礼的钱不来娶她。可这向年间,他家里出了大变故,他承包的果林眼看就要挂果,却被一阵无名火烧尽,哪来的彩礼钱呢?
说好了一起逃,怎么到了这节骨眼上她又要变卦呢?害怕了吗?大款男人有的是钱,人也很不错,长相也不错,也口甜,只不过年纪稍大了点。谁让大款男人也像个男人呢?难道——他不敢再往下想,眼睛回到她身上。她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满脸的汗珠正游离着阳光中的那份七彩的美丽。
“不!”他痴痴地看着她说,“我情愿过着流浪乞讨的日子,却不能忍受和你不能相见的生活。”
可是她仍然没有当初那份出逃时期盼的欲望了。
他绝望了。他不甘心地一把抓住她那双颤抖不已的手说:“我们走吧,我们逃得越远越好。”
她顺着他从灌木丛里出来。上路了,她却挣脱了他的手朝着村子方向走去。
他叫不住她。他只试着拉住她的手去阻止她。他大声说:“你难道忘记我们在苦楝树下立过的誓言么?”
她听了,竟呆呆地站住了,眼眶里就滚出泪来。她望着憔悴的小伙子,说:“我没忘,相伴到永远。我怎么能忘记呢?”
午后的阳光里,他们又一次相拥了。他们都浑身战栗着,他说:“你害怕了么?”
“不!我在为我产即将到来的胜利而高兴。”
“我们是不能战胜他们的。”
“不!我们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失败。躲在灌木丛的这个上午,我想了,我们这样相爱着,没有任何人能够打败我们。我们得回去告诉他们,我们只不过跟他们玩一场无谓的游戏。我们有权利相爱,这是最得要的。”
说完,她伏在他的肩上撸了撸满脸的泪水。给他带来一朵欣慰的笑容说:“我们就这样回去吧!”
回村的路上,午后的太阳黯淡了许多,一股无比清凉的风踏着灌木的枝叶“咝咝”地荡过来,他们就在这痒痒凉凉的风里相搀着朝着炊烟渐起的小山村走去。
远远的,他们看见几个人,几十个人朝着他们跑来。
她挽紧了他的手臂笑着说:“他们来了”。
是来了!近了,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