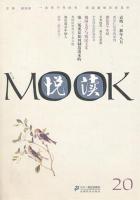……这根牵着心的细绳,需要多少鲜血才能染成!百年过去了,它颜色依旧。年轻的我们也许不会知道,在那岸、水和岛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根粗粝而鲜红的绳呢?
有人,痛切地告诉我;有梦境,令我悲泣;有山巅,牵引着我朝向的目光。正是岸与岛被水分隔的那一天,心血把思念染成绳。
我常在历史正本的字里行间中爬行,我的视觉已被血淋淋的行文碾得支离破碎灯影朦胧。我只能借助幼小的触觉将它掀翻一页。我不知道会有多少像我这样的少年,让历史的恶靥,沉沉地兜在心坎里,深深地积在受伤的手掌中。
多少年来,那页被我嗅觉撕碎的耻辱,常常闯进我的梦中,在我的眼前闪动。我看见了挂辫子的先人原有的笑容,他们为一船满载而归的鱼,光着膀子,就着酒,歌声炒红了晚霞的海风。岛上,亦是那炽热的目光在等待,桅,隐隐现了;船,浅浅现了;木炭条的大汉,晶亮亮现了。一夜的月光,把岛上的美丽看得如此清楚,这里的夜太清,无牵无挂的月色把五谷丰登、鱼跃虾跳的富足照得那么的亮堂。
你们要走了,你们怎流泪了呢?
你们要我看,那里有一桌酒菜,旁边还摆着一本随风而翻的条约……
你们是要我明白。我明白,但我怎么会舍得放开你们的手,我的先人。我知道,那一天,一个流浪归来的儿子,是双鬓斑白,泪也烛干了。
你们就住在我南边的一个岛屿上,可是你们常年不能回家了。是那么近,又是那么远,兜在书包里的历史引着我好想去看你。在清晨,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么?在黄昏,又是彩霞满天的祥云朵下么?
赶着牛,牧着羊,在松松青青的山脊的草沿上,我经常看见一位老人。他看上去是那么孤单,他的眼只望着一个方向。
我问,老人家,您在看什么?
老人看也不看我,答:看远方。
我问,远方在哪里呢?
老人仍不看我淡淡地说,远方在心里!
我想了想,兴奋地说,老人家,我经常梦见一个叫澳门的地方,它好像是在远方,难道它其实就在我的心里么?
老人听了,突然浑身颤抖起来,他慢慢地扭过身,摸索着在我嫩嫩的脸上揉了一下。我看见自己的脸红了。我听见了内心幼小的力量轰然燃旺的火花。我沉浸在一种点化了后的境界时,我却发现那么孤单的老人蓦地不见了。我愣愣地站在那里,“百年思念织成绳”,我是不是在今天接过了老人手中那染红了的绳头呢?那位老人又是不是我蕴含思念的化身呢?
那岛、那梦、那山永远不会从我的心中消失。我知道,远离的游子也在思念着,思念着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