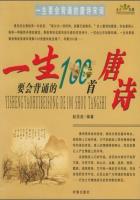费晓明是我的同班同学,在乡中同班同组不同座。那时念书只知念书,多是一些平淡的校园生活,没看得出友谊在哪里,印象中他倒比几位女生要淡一些。
后,上高中,就分开了。我考县七中,他考县六中。再后,我转了校,他也转来,但不同班。经常在饭堂见见面,球场上见见面,再是周末碰巧一趟车回家,各打各的票,也没显出尴尬来。说来,那时我们就是同学了,除了同学,就没了。
我们真正相知时,是高三那年的全校作文比赛,我得了一等奖。他那天赶到我们教室向我祝贺,拿起我证书看了又看,眼就暗了下来说:我没这本事,我写不出像你这样爱父亲的语句来。
他说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庄户人,本分,厚道,又不爱开口说话儿。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忠厚的父亲是普天下最好的。
我就知道了他是一个比我还爱父亲的角色。
此后,高考,我俩双双落了榜。秋天,我又去原校复读。费晓明却在学校附近开了家饮食店,经营早餐、面包什么的。我也时常被他扯着去店里坐坐,听他说起他父亲的事儿,他的眼总是红红的。
隔年,我终于去了城里一家学校念书。同学费晓明也来了城里干了大事。我们联系采取电话的形式,隔五差十的我叩他。电话里说上一阵约个时间见见面,小吃小喝,友谊那东西就变成了隔一阵子没见着倒心慌的样子了。
有段时间,他很忙,有次叩他时,他在那头说:事情搞妥,你的学费我全包了!从那后,我就真的有半年没叩他。我不稀罕他的学费。我担心他的腰包鼓了,我们的友谊就没了。
没想到半年后,他找到我的学校来了。他说的第一句话口气凶凶的,眼也红着:怎不叩我?我笑说:你忙嘛?他听了,半晌没回神,糊糊涂涂就给我一拳,你小子精哩,担心下回我揍你。
我想,你还没变呢!
那天,他没提学费的事,我就大大地放了一下心。可最后还是让他耍了。学费没给,倒给我拎来了几条说查私的烟,害得我老担心烟让指导老师没收去。
这两年,我终于挽回了几年前严重偏科的损失,发些文章。还得了个伪“作家”的称号。而这时,我们的联系更密了。他直说,这几年他一直没读什么书了,也不喜欢读书。但他还是支持我去写作,喜欢读我的东西,就像读高三那年我的获奖作文样,他读我的东西时往往感觉到那是他自己的,很熟悉很亲切,就这样说不清。我说我很感动。他说他也感动。怪了。
去年,我的一篇作品获了全国小小说奖,小城的报纸、电视台都发了简讯,说了这事儿。那日,我在办公室赶材料,电话响了,是他!劈头劈脑一句:待大家知道了,才告诉我,行么?我待解释,他却笑了,说:小子,行,今晚我请客!
晚上,我们终于还是选了间排档店坐下。
喝着酒,脸红了,话就多了。正说时,他放在桌上的手机老鼠样尖叫了起来,我拿眼看他,他也拿眼看我。我说:电话!他笑了,说,别信它,这里这全是屁话。说完“啵”地关了机。我调侃他说,这电话也许就是钱呢!
他红着脸问我,钱!你说钱比什么贵重呢?
那一夜,他醉了,我扶着他回时,他忽然对我说,我这一辈子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化人,但我又想,待我儿了长大了就交给你,让他成为一个有钱的文化人,不知行么?
这些日子,我倒老在想他的那句话儿了:等我们大家的腰包鼓了,每个人都有闲心有耐心写文章,写得专业作家都失业了,那不是很高兴很有趣的事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