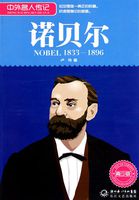陈毅接着说:“如果把王先生与敌人联合攻打新四军的行为公诸于世,非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不可!到那时,王先生难堪,作为抗战最高统帅的蒋委员长更难堪!”这下王仕韬可害怕了!他想起蒋介石在长沙大火之后,为了推卸责任平息舆论,将张治中撤职,将灃悌、徐昆和文重孚枪毙的事,吓得魂飞天外。“感谢陈先生对我的启迪。”王仕韬胆战心惊地说。他的整个精神支柱被彻底击倒了。“感谢王先生对我的尊重。”陈毅的语气平和了。王仕韬的嘴唇张了张,欲言又止。他沉思片刻,对喻世震说:“请喻副官去通知伙房准备酒菜,为陈先生一行接风。”“谢谢王先生!”陈毅说,“国难当头,一切从简,随便吃点就行了。”“也是略尽地主之谊嘛。”王仕韬随即嘱咐喻世震说,“请喻副官注意,我刚才与陈先生交谈的问题,暂时对任何人都保密。在我没有公开之前,有谁知道了,拿你是问!”喻世震应了声:“是!”神色紧张地走了。人的思想感情就是这么奇特,当不可告人的秘密未揭露之前,总是拼命地遮掩隐瞒,秘密一旦公开,就是那么一回事,反而变得坦然而轻松了。现在,王仕韬感到再没有什么可以躲躲闪闪的了。无疑,他下面这番自我剖析的话,与他把喻世震支使开有关。他说:
“陈先生!当年,在井冈山,我的躯体成了你的俘虏,但精神仍然属于我自己。今天,躯体属于我自己,而精神上已成了你的俘虏。”人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真情。王仕韬的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动了陈毅,他激动地站起身来,紧紧地握着王仕韬的手说:“王先生!你的精神仍然属于你,而且是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让我们在神圣的抗战中,永远团结在一起!”“谢谢陈先生对我的理解!”王仕韬从口袋里掏出酒井发给他的那份“梳虱子”的电报,起身递给陈毅,“这是今天上午八点收到的。”
陈毅着了电报,开怀大笑一声,成竹在胸地说道:“酒井要‘梳虱子’,我们要请他碰钉子,而且要让他碰得头破血流!”他旋即收敛了笑容,望着王仕韬,关切地问,“面对酒井的疯狂,王先生打算怎样应付?”
“我的整个思维像一团乱麻。”王仕韬恳切地说,“请陈先生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叫我如何是好?”陈毅沉思一会,问道。“王先生身边的参谋长和师、旅、团长中,有没有顾祝同先生的亲信?”“没有。”王仕韬说,“他们是跟随我多年的同事和下属,都很听我的话。”
“那么,建议王先生来个假戏真做。”陈毅说,“你们仍然与酒井、刘培绪两方保持联系,仍然按三路进军,仍然听从酒井的指挥。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方,比如说,在他们能够听到枪炮声的荒山野岭开开枪,放放炮,使他们不辨真伪。”
“好!”王仕韬已把陈毅当成真正的朋友,“如果陈先生抽得开身,希望你在敝军多待几天,等这场戏演完了你再走。”
“恭敬不如从命。”陈毅一脸胜利的微笑,“我给王先生当参谋。”
日出日落,转眼过去了三天。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九点左右,由刘培绪直接指挥的第四师第十六、十七两个旅,已经进入溧水西面刘家冲北面的金凤山和南面的栗树山。刘家冲是个近百户人家大村庄,据刘培绪派出的前哨部队报告,这里驻扎着一支新四军部队,人数不少于一百人。刘培绪听到报告之后十分高兴,他对下属们说:“新四军的战斗队一般只有二三十人,看来他们把刘家冲当成前哨阵地,在这里摆了个连队。好!这回‘梳虱子’,先梳这只‘大虱婆娘’。”
其实,这里只有新四军的两个班,由于刘培绪把他们看成“大虱婆娘”,计划派三个营的兵力包围刘家冲。
现在,刘培绪带领几个旅、团、营军官,登上栗树山的最高峰,他举起望远镜向山下的刘家冲窥望,见村子里有十余家的屋顶上炊烟袅袅,猜想这些人家来了客人在烧茶吧!见村庄东南角的上空飘着一面红旗,心想那一定是新四军连队的营地。于是,刘培绪自信地下达了包围刘家冲的命令:我们的兵力十倍“于敌,要多抓活的!你们暂时把全村老百姓集中关在一起,等部队在村子里吃了午饭,然后把他们统统杀掉,把可吃可用的东西带走,再放火把房子烧光!”
一个团的和平军从四面八方向刘家冲包围过去了。可是,他们中了新四军的疑兵计。村子里一个新四军战士也没有,老百姓也早已转移了。
刘培绪进入溧水后的第一仗落空,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却升起了一股彻底消灭新四军的更大冲动。他命令两个旅以连为单位,连与连之间保持半华里的距离并肩前进,使五十四个连队形成一把二十多华里长的大梳子横梳过去,哪颗“梳齿”碰上了“虱子”,左右的连队合作展开包围。
他吩咐完了,与姨太太各骑一匹大枣红马,带领军司令部机关约二百人的队伍进入刘家冲,计划在这里稍事休息,吃了午饭再走。
下午两点三十分左右,刘培绪午休起来,吸过鸦片烟,见部下已挨户抄家完毕,正准备吩咐部队放火烧房子。忽然,脑顶上空响起了四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四颗迫击炮弹先后落在村庄的四周,惊得他目瞪口呆!
“我们被新四军包围了?”刘培绪本能地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怎么办?”他一时乱了方寸,眼木木地望着副官、秘书和警卫连长。
他们进入刘家冲已经四个小时,大队伍至少行进到十里以外的前方。远水救不了近火。副官、秘书和警卫连长都诚惶诚恐,一筹莫展。但是又不能不说话。尽管说的话毫无价值,在这紧急关头,总得有所表示。
“估计新四军顶多一个连,我们身边的兵力比他们多一倍,突围出去!”副官说。
“只有突围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秘书紧接着说。
“突围中,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保证军座和太太安全脱离险境。”警卫连长赌咒似的说。这时,又有四颗迫击炮弹在村庄四周爆炸。刘培绪的姨太太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吓得一声尖叫,哇哇大哭。“你妈妈的!”刘培绪粗野地骂着,把满腔惶恐、慌乱和手足无措,都集中在给姨太太的巴掌上,“你哭死!”
刘培绪刚骂完,从对面的山坡上传来了喊话声:“请刘培绪先生静下心来听我们喊话!你们已被新四军重重包围,走投无路了!请立即派代表过来,商讨刘先生与我军二支队张鼎丞司令员面晤,以及双方进行停战谈判等有关事宜。只要你们停止对新四军的进攻,我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
喊话声是通过铁皮喇叭筒传过来的,洪亮,凝重,好比铁锤敲在铁砧上。
“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刘培绪对新四军的料事如神,感到可怕。
一片哑然。是的,对刘培绪的提问,谁也回答不了。
原来,张鼎丞遵照陈毅的战斗部署,一边派出几支精悍的小型侦察部队进行侦察,尽可能地掌握刘培绪军每天的动向,一边布置各战斗队在与敌人的前哨部队交战中抓“舌头”。昨天傍晚时分,驻扎在刘家冲的新四军,与刘培绪指挥的这一路约一个营的前哨部队,在距离刘家冲约半里远的一个小山包上打了一仗。和平军人地生疏,又见天已将黑,不敢恋战,慌忙派人回到八里外向刘培绪报告,糊里糊涂说刘家冲驻扎有百把人的新四军队伍。当敌人的前哨部队撤走,新四军准备追上去抓“舌头”时,发现敌人丢下的十多具尸体中,有两个人还是活的。这两个人都伤了大腿。新四军把他们抬回去,让卫生员给包扎了伤口之后,分别进行审讯,知道了刘培绪的具体动向。今天上午,刘培绪领着部队登上栗树山时,有两个新四军侦察兵与那两个敌伤兵,正躲在栗树山一个名叫神仙岩的岩洞口观察,得知骑枣红马的是刘培绪夫妇。
“他们称我先生?”刘培绪在惶惑中,似乎获得某种安慰,“他们的支队司令员与我谈判,说是河水不犯井水?”他在凄楚中,又似乎获得某种启发。
“看来新四军对军座比较尊重。”秘书浑身微微颤栗,希望刘培绪接受新四军的意见。
“新四军说话近人情。”副官和秘书想到一起了。
“他们至少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警卫连长这话的意思,是对方没有骂他们为汉奸?对方的喊话声又紧迫地传过来:“请刘先生速战速决,如果愿意派代表过来交涉,请朝天连放三枪!”“我们得相机行事,”刘培绪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放枪!”警卫连长举起手枪朝天连放三枪之后,刘培绪让秘书当代表,带领四名卫士前往。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秘书回来了。
“情况怎样?”刘培绪焦急地问。
“非停战谈判不可!”秘书的表情很复杂,紧张中包含着轻松,轻松中包含着惊讶,惊讶中包含着感佩,“新四军对十七日上午军座带着我在上海费利溥先生寓所参加开会的情况,以及整个三方联合反共会议的全部内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连十八日上午八点,酒井发给我们那份‘梳虱子’的电报,接见我的人一字不漏地背给我听。”
“噢!”大家一惊。刘培绪的脸拉得长长的,副官的眼睛睁得圆圆的,警卫连长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新四军已做好一切迎战准备,如果我们不与他们谈判停战,跟酒井先生和王先生他们打下去,势必遭受严重损失,”秘书以肯定的语气说,“可以预料,他们一定会比黄桥战役打得更加主动!”
“接见你的是个什么人?”刘培绪胆怯地问。
“他只说他姓黄,没有介绍身份,说话很有水平,也平易近人,可能是支队司令部的什么官儿。”秘书说,“黄先生说等待与军座进行谈判的是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先生。他介绍说,张先生是福建永定人,青年时期即投入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说张先生是闽南农民暴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当过闽西军委书记和红军第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曾经与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朱德一起转战赣南;说张先生还当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新四军成立之前,在闽西南打了三年游击战争。”他望了陷于沉思的刘培绪一眼,“黄先生这么将张先生介绍一番,那意思好像是说,别看他是个支队司令员,可他是共产党一个有声望有地位的老资格哩!”
“如果不抱成见看问题,共产党里的确有许多人才。”刘培绪说,“我与张先生在什么地方见面?我的安全问题你向那个姓黄的提过没有?”
“黄先生说,如果我们同意与他们进行停战谈判,张鼎丞先生来刘家冲与军座面晤。”秘书满意地微笑着,“因此,军座的安全问题不存在了。”
“噢!张先生来刘家冲?”刘培绪、副官、警卫连长同时发出意外的感叹。这意外,说明新四军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说明新四军对停战谈判抱着一片诚意。刘培绪在感叹之余,又为自己的贪生怕死而感到愧疚。
“建议军座在谈判中拖住时间,我们马上用收发报机与主力部队联系,命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来,迫使对方向我们投降!”副官打着满意算盘,说得眉飞色舞。
“胡闹!”刘培绪斥责道,“人家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十足的把握,敢于上我们的门?如果按照你设想的办,非引起一场激战不可,非双方同归于尽不可!”他见副官面红耳赤,一副尴尬相,也就不再骂了,把脸转向秘书,“张先生来刘家冲,是你去接他,还是怎么的?”
“约定由我们再连放三枪。”秘书说,“张先生听到枪声,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估计他眼下住在三华里以外。”
其实,张鼎丞和他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栗树山的半山腰那个神仙岩洞里。这是个可以容纳三百人的岩洞,过去岩底高低不平,是长虫、蜥蜴、壁虎的藏身之所,黄羊、狗獾、野兔的出没之地。半年前,驻扎在这里的新四军战斗小队为了更好地与敌人周旋和转战,决定把神仙岩作为第二营地,放火烧死岩洞里的害虫,用黄土将洞底填得平平坦坦。张鼎丞掌握到刘培绪的动向,用收发报机与陈毅取得联系之后,于昨夜十二点左右,带领三十多名指战员和两门迫击炮,从八里外来到这个岩洞里。今天上午,见刘培绪指挥的主力部队已经开走,刘培绪等人已进入刘家冲,利用敌人不明新四军底细的弱点。虚张声势,迫使刘培绪接受停战谈判。
现在,张鼎丞见刘培绪又连放三枪,知道对方的算盘珠子完全由新四军拨动,沉着地对大家说:“虽然已迫使敌人就范,刘培绪已听从我们的支配和控制,但是,我们的力量毕竟薄弱,千万不能大意。”在昏暗的桐油灯光下,他的表情更显得老成持重。他进行必要的嘱咐之后,决定让第三团团长黄火星当他的临时副官,再带一名警卫员前往刘家冲。
四十岁的黄火星,原是闽南游击队副司令员,刚才与刘培绪的秘书接头的就是他。
半个小时左右,刘培绪带领秘书、副官、警卫连长来到村庄前面的小石板路口,迎接张鼎丞等人。他见对方只来了三个人,又一次感到意外,自己被新四军严重控制的感情也更为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