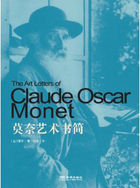皮卡比亚给达达主义领袖查拉画过一幅肖像。
我没见过查拉的照片,不知道这个当时的风云人物到底是什么样子。以为皮卡比亚的画会告诉我查拉的长相。意外的是,皮卡比亚的画名虽然很直接地说是《查拉的肖像》,我却怎么看也看不出来。
因为那不是一幅肖像。
画面只有很简单的五个圆球,那些圆球很像是金属制品,最下面的圆球干脆就是个乌黑的圆锤,两边弯曲的线条像电阻丝。一根金属线将它们像零件一样吊在一起。画面从上至下有几行字母。鉴于皮卡比亚是法国人,我只能姑且认为那是几行法语。对一幅画来说,文字看不看得懂并不重要。皮卡比亚毕竟是在画画,不是在撰文。
不知道查拉怎么评价这幅画。画的毕竟是他,无论如何,被画者应该有个说法。但查拉从来没就这幅画说过些什么。作为反对一切的达达主义带头人,他似乎满意得都忘记要夸奖画家几句了。
查拉是不是真的满意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这幅画。
皮卡比亚为什么要将人画成一串有模有样的球型金属令人很感兴趣。尽管他晦涩的画作很多,这幅画看起来却着实有点过分。我不太想说达达主义,一是我不大喜欢,二是它很短命,只有四到五年。它的短命和我的不大喜欢没有关系,要说清楚却是另外的话题,没必要在这里展开。但有两句话又不得不说。第一句是查拉的话,他解释达达主义者都“厌烦这个被战争折磨的世界,厌烦令人生腻的教条,厌烦因袭的感情,厌烦卖弄学问,也厌烦那无所事事、而只是反映这个极有限的世界的艺术”;第二句话是《达达》杂志出到第三期才算出来影响。但恰恰这期,是由于皮卡比亚的积极介入才得以问世。
或许对所有的达达主义者来说,皮卡比亚才是最彻底的。
查拉说这个世界极有限,这个世界的艺术也极有限。有限当然就是有边界。达达主义者都想突破边界,皮卡比亚也当然不会例外。问题是,想突破是一回事,能不能突破又是另一回事,甚至,找不找得到边界来突破,更是另外的另外之事。
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流派,达达并非无的放矢。20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时,虚无主义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达达当然很虚无,因为它反对一切,但正因为它反对一切,所以把虚无也反对了进去。认为“什么东西也没有”便成为达达的宣言。皮卡比亚将查拉画成一串金属圆球,大概他想说的是连人也没有。
这就有点惊世骇俗了。说“什么东西也没有”的查拉并没有把人包括进去—因为人不是东西;皮卡比亚却声色不动地做到了人的取消—因为人是个东西。他嘴巴没说,但画面却说得明白,他突破了没有谁敢去突破的边界。
在今天,因为读不懂,查拉的诗歌已经鲜有人读;但同样看不懂,皮卡比亚的画却始终有人在看。想想很有道理。我们面对今天,已经看见统治世界的不再是人,而是人发明的机器。皮卡比亚把人画成金属,已经有未卜先知的意味在里面了。
迟早有一天,机器会把人也统治进去。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在很多地方都能读到。哲学家们说过,社会学家们说过,人类学家们也说过。皮卡比亚用他的绘画语言,在很早很早以前就说过。
大凡越过边界的艺术家,预言都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