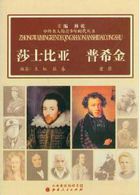婚后不久,他们的差异便在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上显现了出来——王赓办事认真负责,为准备授课经常埋头研究,而生性风流的陆小曼则喜欢游乐,三天两头就往外跑;主修军事出身的王赓为人刻板,不会取悦女人,对妻子只能做到“爱护有余,温情不足”,而陆小曼却浪漫天真,富于幻想,渴望温存。
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所以在王赓看来,陆小曼并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也没有守住妇道人家的本分;而陆小曼则认为王赓不够体贴不解风情,一个出过国、留过学的男人还能如此古板实属少见。
就在这种长期压抑的寂寞与失落中,陆小曼变得越发苦闷和孤寂,甚至更加渴望那种真正的爱情出现。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当诗人徐志摩带着无尽的激情与浓烈的爱意闯入她那孤寂、平静的情感世界的时候,最终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得到爱情,得不到快乐
在一次偶然的舞会上,陆小曼终于与当时已经十分著名的诗人徐志摩相遇了。在两个人共舞的过程中,早就渴望着爱情降临到自己身上的陆小曼充分领略了诗人的魅力。而在随后的交往中,两个人又惊讶地发现原来彼此之间有着太多的共同之处,于是一场干柴烈火般的爱情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飞快速度开始了。它是那样的浓烈和炽热,以至于世人对此只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惊讶感觉。
而在当时的那个一切尚处于绝对封闭状态中的时代里,作为有妇之夫的徐志摩和作为有夫之妇的陆小曼之间的爱情显然是不受欢迎的。即使是对于这样的两位文坛名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还是难免从刮目相看逐渐变为瞠目而视,流言飞语铺天盖地般地倾轧在二人的身上。可是越是遭受到非难,两个人的感情反而却愈加深厚。尽管徐志摩在最初还有所克制,而且也曾为了逃避这段感情在1925年的时候赶赴欧洲,但是当他惊闻爱子在家乡夭折的消息,同时又接到陆小曼病重的电报后,他毅然地回到了北京。从此以后,这一对倾心相爱的人更是难舍难分,而此时徐志摩的旧婚约也已解除。
后来,王赓经好友刘海粟的劝说和开导,表示同意与陆小曼解除婚约。这样一来,在经过对于双方家长的反复劝说之后,陆小曼与徐志摩终于如愿以偿地结成了眷属。陆小曼也为了爱情敢于抛弃一切的做法,也成了中国现代文人情史上最为轰动的一章。在那个人言可畏的旧式社会里,个性淳厚的她的这种选择,竟使她无可避免地成为了社会上所认为的那种不道德的女人。
就在陆小曼满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准备开始全新的感情生活的时候,婚后的诸多事实却无情地证明了她费尽周折所得到的爱情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得到了理想中的爱情,却没有得到理想中的那种快乐。婚后的徐志摩和陆小曼一度被严父禁锢在老家浙江海宁硖石而不许外出,这种遭遇使得自负自尊的陆小曼在新婚不久就因肺病而病倒。再加上徐、陆两个家族都因为不满意这桩婚姻对他们采取了经济封锁,所以回到上海后的这对夫妻只能在艰难中开始了他们原以为美满但实际上却并不成功的婚姻生活。
从小的养尊处优使陆小曼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所以即使是嫁与徐志摩后花起钱来依旧大手大脚,而且生性风流的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穿梭于各种社交场合,并很快就成了上海社交界的中心人物。而只是擅长文学事业、没有过多财富的徐志摩却因此陷入了一种窘迫不堪的狼狈处境中。为了让陆小曼过得舒适一些快乐一些,心中郁闷的诗人不得不频繁地四处奔走讲学,课余时间还要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除此之外,他还倒卖古董字画、做房地产掮客,不顾疲惫地去赚更多的钱。但即便如此辛苦,所得到的收入还是无法满足陆小曼的那种奢靡生活。
渐渐地,陆小曼开始觉得徐志摩不如婚前对她那样好了。她觉得婚后的志摩只是管她而不再爱她,她开始对他有些失望。关于这件事情,她曾对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抱怨:“照理讲,婚后的生活应该比过去甜蜜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随着蜜月激情的逐渐平淡,对现实过于理想化的想象使两个人在性格上的诸多差异终于露出了端倪。
爱到两败俱伤
对于夫妻感情出现的裂痕,尽管陆小曼失望过也抱怨过,但她却并没有更多地在意,而是继续昏天黑地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而此时的徐志摩已经辞去了在上海的职务,应胡适之邀赴北大任教。他曾劝说陆小曼随他北上,可因为陆小曼依旧留恋上海的花花世界,所以执意不肯离开。无奈之下,徐志摩只得在上海与北平之间来回奔波,并最终因为搭乘的飞机失事而在1931年以英年早逝的不幸结局为自己的辉煌生命画上了句号。
直到此时,仍然深爱着徐志摩的陆小曼才如梦初醒。得知噩耗后,她悲痛欲绝,她在事后写给胡适的信中也说:“我受此一击,脑子都有些麻木了,有时心痛起来眼前直是发黑,一生为人,到今天才知道人的心竟是真的会痛如刀绞,苍天凭空抢去了我唯一可爱的摩,想起他待我的柔情蜜意,叫我真不能一日独活。我的眼泪也已流干,这两日只是一阵阵干痛,哭笑不能。”
徐志摩死后,29岁的陆小曼独自背负起害死诗人的莫大罪名,并在悔恨与孤寂中艰难度日。于是,为了摆脱无边的寂寞与悲伤,近于绝望的她愈加沉迷于“诱人”的鸦片之中而不能自拔。
尽管此后的陆小曼也曾与徐志摩的好友翁瑞午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她主动向翁瑞午约法三章,既不许他抛弃发妻,也绝对不会和他结婚,而是宁愿保持不明不白的关系。她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一是因为她始终不能忘情于徐志摩,二来则是因为翁瑞午的发妻是那种传统的老式女子,离异后必无出路。尽管她曾坦言自己对翁瑞午“只有感情,没有爱情”,但是当许多朋友都不赞成她与翁瑞午的这种关系,甚至以断交作为威胁的时候,她也还是不为所动,更不肯终止与翁瑞午的关系。或许,这也是她真性情的一种体现吧。
平淡的最后归宿
陆小曼的晚年过着虽谈不上富裕但却足以称为悠悠然的日子。她与人来往,但与世隔绝。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年过半百的她也决心离开病榻,去为国家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朋友的鞭策下,她还戒掉了与之纠缠了近半生的鸦片,身体也由此逐渐康复起来。
1956年,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曾安排陆小曼成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此后,她还成为了农工民主党徐汇区支部委员,并被上海画院吸收为画师。1959年,她又被选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为政府筹集书画,还为陈毅画过扇面,给杜甫草堂补过壁。同年,她被全国美术协会评为“三八”红旗手,身兼农工民主党员、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美协会员数职。除此之外,陆小曼还与王亦令合作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如《泰戈尔短篇小说集》和艾米丽·勃朗特的自传体小说《艾格妮丝·格雷》等经典作品。
比起年轻时的轰轰烈烈,晚年的她过得平淡而舒心。回首往事,她曾无限感慨地说:“过去的一切好像做了一场噩梦,酸甜苦辣,样样味道都尝遍了……我没有生儿育女,孤苦伶仃,形单影只,出门一个人,进门一个人,真是海一般深的凄凉和孤独。”
1965年4月3日,一代佳人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63岁。她走得很安详,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临终的最后一个心愿就是与徐志摩合葬。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最后的心愿一直也未能实现。直到她的一个在台湾的侄儿后来在苏州为她建造了一座衣冠冢,才算为这位曾经有着绝代风华的美丽佳人那充满坎坷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并不十分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