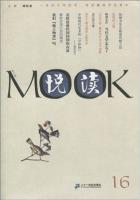匪兵们一听招唤,迫不及待地往伙房跑去。熊武也大摇大摆地跟着匪兵后面往伙房走去。
走在后面的鲍元才心有余悸地对父亲说:“爸。吃完饭,我们就走了……你一定要小心呀……共军很快会到枫桠坪来的,他们可不是好对付的……也许天真的要变了……”
进了城的孙玉穗哪闲得住。正好这几天,大哥大嫂都在忙着开会,工作队的大小领导也都去参加会议,研究工作。她怎么会在屋里老实待着呢!这个在北方农村长大的姑娘,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南方来,第一次走进四面都有高墙的康阳城,这对她来说,什么都是新奇的。她登上高高的城楼,在城楼上漫步。他用手摸一摸城墙上那坚固的石砖,放眼俯瞰那完全与家乡不一样的景色——泛着碧绿波纹的怀江,葱茂湿润的田野。她深吸了几口含着香味的空气。一路上的行军,一路上的劳累,仿佛都涤荡得一干二净。
逛了城楼,她又走上街道。她缓缓走着,慢慢看着,那紧挨着的一栋一栋木板房,那伸出小半个街面的屋檐都吸引着她,她真想进里面去瞧瞧,去瞧瞧南方人睡觉的床,难道那能比家乡的土炕睡得舒适、实在……她犹豫过几次,但她还是没进去,她知道工作队有严格的纪律……
街上的铺子都开着张,里面玲琅满目的好东西太多了,她目不接暇。她身上没有钱……再说了,她要那些小花布,首饰、胭脂、口红之类的东西有什么用,她不稀罕……她心里暗想着。她顺着香味不知不觉地来到卖食品的一条街上,卖食品的老板们扎堆经营,铺子一间挨一间,一长溜的都是卖吃的。一见到有人走过来,伙计们都使劲儿吆喝着,各夸各的食品美味无比,天下第一……那些油果子、麻酥饼、锅盔、小笼包都没能吸引她,但当她走到一间卖糯米甜糕的铺子旁,脚好像被粘住一样,怎么也挪不动步子了。那刚刚蒸出来的,还散发着热气的米粉甜糕,被一片竹刀切割成一个一个公公正正的方块放在绿油油的荷叶上,甜糕表面上有一层像玉一样洁白光滑的薄皮,皮上还点着像红宝石一样闪亮的红江米粒,表皮下面则像是被压缩成方形的松软棉花。当甜糕被放置在荷叶上后,尤如绿叶中的一朵白花,更显得晶茔剔透,秀美好看,还散发出一种她从来没有闻到过的淡雅、清新的香味……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她想,哥哥、嫂子肯定也没有吃过……她思想里斗争了好久,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取下手腕上的银镯子换了四块糯米甜糕,然后让伙计把它包好,包严实了,自己小心地把它捧在手上,一路蹦蹦跳跳地往卫生所跑去。
一进卫生所的大门,她就看到二哥孙玉平正在扶着墙一步一步练习走路,拐仗早扔在了一边。
孙玉穗:“二哥。你怎么起来了?……医生不是叫你多躺几天嘛……”
孙玉平:“我看好了,就起来走走……老躺着怪难受的……”
“不行!不行!还没好利索哩!……快上床去……”孙玉穗用左手拿好甜糕,右手执拗地又扶又拉地把孙玉平带到了床上坐下。随后,自己也在床沿上坐好。
“二哥。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孙玉穗边说着边并紧两腿,小心地把手中的纸包放在两腿上面。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包装纸一层一层打开,好像生怕它会被碰破似的。最后,四块白嫩的糯米甜糕出现在他俩的眼前。
“玉穗。你哪儿来的钱?可别违犯群众纪律……”孙玉平惊奇而又担心地问。
“放心吧!二哥。我知道……我不会违犯群众纪律的……我是拿我的银镯子换来的……”孙玉穗欢欣地说。
孙玉平:“银镯子不是娘给你的吗?你从小就带在手上……”
孙玉穗:“二哥。我现在已是工作队员了,还带那玩意儿干什么……多不方便……干脆换好吃的东西得了……”
孙玉平:“你呀……什么时间才能长大……”
“二哥……”孙玉穗拿起一块甜糕送到孙玉平嘴边,“快吃,还热着哩……”
“玉穗。你自己吃,哥不吃……”孙玉平推辞着。
“二哥。你尝一尝吧……我这儿有四块,我们一人一块,还有两块给大哥和大嫂留着……”孙玉穗说着,拿着甜糕不收手,硬要往孙玉平嘴里塞。
孙玉平没办法,只好把甜糕接过来,还犹豫着。
“二哥。我可有一个重要的好消息告诉你……你要不吃,我就不说……”孙玉穗想出一个主意说着。本来,她就是要把这个喜讯告诉二哥的。
孙玉平拗不过淘气的妹妹,只好把甜糕送给嘴里。孙玉穗看哥哥开始吃了,也高兴地拿起一块,她一小口一小口,舍不得似的慢慢吃着,她要品出甜糕的滋味来。
“真甜呀!真香呀!……二哥,甜不甜?”孙玉穗故意地问。
“甜。”孙玉平点点头。
“二哥。我要把好消息告诉了你,你就不光是嘴里甜,心里头会更甜……”孙玉穗神秘地说。
“能有什么好消息?你这鬼丫头,拿你哥开什么玩笑……”孙玉平不好意思地说着。
“真的……”孙玉穗把最后一小块甜糕塞进嘴,有些急了,忍不住地说:“二嫂已经怀上我的小外甥了……”
“真的?”孙玉平脸上现出惊喜。
“那能有假?!”孙玉穗在自己肚子上比划了一个大起来的手势,“娘可高兴了,天天都盼着抱孙子……我们离家也快有半年了,没准儿二嫂已经为你生了个大胖小子哩……”
他俩都开心地笑起来,笑得是那样的甜蜜。孙玉平心中腾起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自豪和幸福……
何新生这几天也闲得无聊。大家都在忙事情去了,只有他与几名重伤员在卫生所里休息。他看病房里没有领导,也没有医生,只有几名老乡在照顾重伤员,他干脆溜了出去,一个人在城里瞎逛起来。
他是在大部队开拔时听说伤病员要留下来,就装着拉痢疾,全身发软,走不动路被留下的……跟着大部队,每天不是行军,就是打仗,太累、太苦、也太危险,还受纪律约束。这样的日子过了快一年了,他实在受不了了。原以为日本鬼子赶走了,部队哪还有什么仗可打?!自己闲着也是闲着,参加县大队,就在家乡,有吃有喝,也不用再为三顿饭发愁,还很光荣。没想到县大队很快就编入了野战军,又要跟国民党打仗。这样打来打去,不知道哪天是个头?他曾几次产生过开小差的念头,但他毕竟是个胆小鬼,他怕开溜后,部队把他抓回来,说不定真要执行纪律,把他枪毙了。他还怕,即便跑回了家乡,家乡的群众一定会把他作为逃兵关押起来,说不定还会投入大牢……他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行军他跟着走,冲锋躲在后头,他庆幸自己命大、福大、造化大。一路南下,大大小小的战斗也参加了不少,却没有牺牲……
这次他耍滑头,死皮赖脸地留下来,本想过几天舒服日子,恰又赶上守城之战。当敌人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肩膀时,他大哭小叫的。心想这次算完了,要到阎王爷那儿报到去了。可是被担架队抬进了卫生所后,他才看清只受了点轻伤。子弹只是在他的肩头上擦破了一层皮,他又庆幸起来……守城之战告捷,全城群众欢庆,他觉得自己“挂了花”,大小也算个英雄,心里总是美滋滋的,走在大街上,也神气了许多……
何新生一个人在街上瞎转着。店铺里各种各样穿的、用的倒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只是餐馆里飘出来的肉香对他的诱惑力太大了。他看了看天色,估计也快开晚饭了,自己的肚子也真有些饿了。再摸摸衣兜,里面还躺着几块热乎乎的银元哩……那是他在部队攻进城后打扫战场时,从国民党死去士兵的身边捡到的。他当时悄悄地把它藏进了衣袋里,一直没有交公……唉!现在大小领导正忙着呢,哪还顾得上他呀……他壮了壮胆子,但还是有些担心,特意在背街找了一个偏僻、不起眼的小餐馆走了进去。
进了餐馆后,他找了张靠墙脚的桌子坐下,点了几个卤菜,一碟花生米、还要了一壶酒,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真香啊……何新生在心里对自己说……部队里的伙食太差了,十天半个月也难见到一点浑腥。他觉得自己瘦了许多……唉!一个人没有爹痛、没有娘爱,又生了天生的一张馋嘴,怎么办?只有自己心痛自己,自己照顾自己,自己想办法吃好、喝好,要把自己的损失补回来……哪管以后会怎么样……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何新生自斟自饮,也不知吃喝了多长时间。他像要扒本似的,把一壶酒喝了个精光。把盘子里的菜吃了个底朝天。当他从餐馆里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漆黑了。
这是一条小街,没有路灯,只有靠街两边房屋里映起来的亮光,才能勉强分辨出街道的轮廓。何新生嘴里哼着:“好酒。好酒……比北方的烧酒好喝……”可已经感到头上有些打转,腿也有些发软,两脚就像是踩在棉花堆上似的,难以走稳。他只好扶着街边房屋的板墙,借着微弱的光线,小心地往回走。
街道上的穿堂风夹着夜晚的凉气不停地向他袭来,他感到头越来越晕。走着走着,走到一栋亮着小红灯笼的房屋前,没想到门是虚掩着的,他一把没支撑住,反而把门推开,手上一空,脚下一滑,他一下子跌倒在这家门前,肚子里的酒肉在翻江倒海,他实在憋不住,“哇”地一下全吐了出来。
“呸!呸!是哪个混蛋醉鬼,敢在老娘门前倒潲水……坏了老娘的生意,真晦气……”随着一阵又骂又吼的尖声音,一个女人走出门来。
这个女人,原来是逸仙楼的老鸨。自从解放军进了城,取消了卖淫嫖娼这个行业,查封了逸仙楼后,她也只好从逸仙楼出来了。她别的本事又没有,就在城里背街上找了间房子住下,悄悄开了个暗门子。边做着自营自卖的生意。还边梦想着国民党或者土匪能打回来,能帮她收回逸仙楼……
她虽然已有三十好几了,但由于平时保养的好,加上又会打扮,又很风骚,因此并不显得年龄很大。一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神态。由于她在妓院呆的时间久了,许多人都认识她。但谁也说不出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在妓院中的雅号叫小肚兜,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不仅有城防司令部做她的后台,而且还跟土匪中的头头脑脑来往密切。前几天,山上的土匪小头目猴旦进城后还特意找过她。他俩正在鬼混时,被孙玉华带着民兵捕了个正着。猴旦被抓走后,她一直提心吊胆,闭门锁户了许多天。直到今天,看看没有人来抓她,也没有什么动静后才又做起了生意。没想到刚开门就遇上一个醉鬼,还在她门口呕吐了一大堆,她能不生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