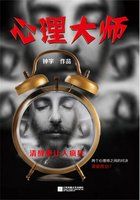矿井深处那盏灯
王晓峰
那年春节,由于受煤炭市场形势的影响,国内大部分煤矿破天荒地都放了长假,五子哥所在的煤矿也不例外。
因为五子哥是单身,放了假回去也没有老婆可抱,队长老曹就让他留下和田牛、立冬几个人下井值班。每班两个人,五子哥和立冬一班。
大年初二那天,五子哥和立冬上八点班。到达工作地点后,他们先去工作面上巷转了一圈,没啥事。10点多的时候,立冬对五子哥说,今天想去女朋友秋月家串亲戚,想提前升井,并说明天他交班,让五子哥先走。
要说在井下值班也没啥事,值班主要有两项任务,其一是开泵排水,其二是巡逻。800米深的矿井下,水、火、瓦斯、粉尘、顶板五大自然灾害,水排名第一,可见其重要性,总不能因为放假让水淹了采煤面吧。再说巡逻,就是要求值班人员每班要到各个工作地点转转,别让谁把东西偷了。据说上一年过年矿上一个生产区队就是因为在井下值班巡逻的人员不负责任,不知让谁把一根长达100多米的电缆给偷剥了,仅此一项,矿上损失几万元。亡羊补牢,所以今年各区队都加强了井下值班人员管理。
队里每班安排两个人值班,一个原因是井下不安定因素太多,怕出了事没人知道,两个人在一起好相互照顾一下。但现在立冬提出先升井,尽管五子哥心里不太愿意,还是答应了立冬的要求。
立冬走后,五子哥顺着工作面往下走,拿着矿灯这里看看那里照照,平日热火朝天的工作面此刻寂静无人,五子哥心里有些空荡荡的。来到下巷中间泵坑处,五子哥看看泵坑,里面的水不太多,说明上班的人没有偷懒。五子哥把水泵的排气阀打开,排出里面的空气,然后按下开关按钮,水泵就隆隆地叫了起来。开了不到一刻钟,泵坑里水就见了底,五子哥把开关关掉,然后顺着巷道往外走。
他向外大约走了三四十米,手中的矿灯猛地一闪,灭了,他叫声糟糕,又扭了扭开关旋钮,不亮,他拿着矿灯头在旁边的工字钢轻轻磕了两下,仍然不亮,五子哥知道这下完了。
没有矿灯,四周顿时陷入一片混沌,他感到四周好像有无数只魔爪向自己压过来。怎么办,怎么办?他在心里问自己。因为是放假时间,他们现在每天都是在二水平平台上交接班,如果等下一班人下来,至少在五点以后,还有,就是下一班人下来,往下巷来不来还是两回事,因为工作面水不大,即使有一班、两班不开水泵也没事,昨天他和立冬就没往下巷来。想到这里,五子哥说,不行,我得走,我不能在这里等。他站起身来,摸着往前走了两步,只听“咚”的一声,安全帽撞在一根弯曲的工字钢梁上,他脑袋嗡地一下还半天回不过味来。他从地上摸到安全帽,然后戴在撞得发晕的头上,嘴里骂了声奶奶的,然后弓着腰继续往前摸去。
又往前不知摸了多远,他脑海里突然想到老矿工们说过,这个采煤面采一分层的时候,队里一个矿工下班时,因为图省事坐运煤的皮带被拉到流煤眼里摔死的事,那时候,他还没参加工作。平时上班的时候人多,他没想过这件事,今天怎么矿灯瞎了,他会想起这件事。他感到自己的头越来越大,脖颈后也是凉飕飕的。五子哥想,我这样摸,不会摸到流煤眼里吧,他感到前面好像有一个人在向他招手。五子哥哥恶狠狠骂了声,日你奶奶,老子不怕你!
但骂归骂,其实五子哥心里还是怕得要命,他直后悔不该听队长老曹的话过年来加班,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的骂自己:胆小鬼,就这还是共青团员呢?人死如灯灭,怕什么呢?但他知道他的心还在揪着,在害怕。小时候在农村打麦场上听爷爷讲过的鬼故事涌进脑海:说有一个卖菜的老汉,天不明就起来赶集卖菜,当他走到河边准备洗把脸时,菜筐子里的秤锤一骨碌滚到了河里,秤锤滚到河里后不仅不沉底,反而在水面上来回翻滚,一会儿飘到河边,一会儿飘到中间,老汉知道是河里的淹死鬼在作怪,他就朝河里吐了一口吐沫,骂了声日你姐,想骗我上当,老子才不上当呢,你就在河里待着吧,一百年也不得脱生。话音刚落,秤锤就沉到了河底。还有一个,说一个人走夜路害怕,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挑一副担子,紧走几步赶上,走近一看,只看见一副担子和两条腿在走路,看不见上半身……
他感到有一股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淌,奶奶的,我不怕,五子哥给自己打气。五子哥突然想唱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随后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他感到发出的声音不是自己的。
他继续往前摸,突然,他感到身后工作面里面好像有一点亮光闪了一下。人在黑暗的环境里对光是最敏感的。他回过头,看到很远处有个灯又闪了一下,虽然很遥远,但他感到应该是一盏灯,大过年的,都放假了,还会有人?他的心又揪了起来……
灯光越来越近,他看清楚了,是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矿工,不知哪单位的?有些陌生。只见来人是一副长脸,大概有四十多岁,走路稍微有些趔趄,好像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留下的后遗症。
五子哥和来人打着招呼,师傅,您好。
那人好像没有一点吃惊,看了五子哥一眼,我知道你的矿灯瞎了,特来和你做伴。
五子哥一惊,你怎么知道?
那人说,我听立冬说你还在井下,就来看看。
五子哥说,谢谢师傅,你哪区的,好像有些眼生?
那人笑笑说,我姓张,以前也在这个队,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你还没来矿呢。
……
有人相伴的路很短。没多大工夫,两人就走出了下巷,开始爬绞车坡。
绞车坡有1000多米长,爬了不到一半距离,五子哥就累,腿像灌了铅,想说歇歇再走,但看那人没有歇的意思,就继续爬。
爬坡的时候,五子哥累得气喘吁吁,但好像一点感觉不到那人气喘,甚至连脚步声也听不到。五子哥想问,但张了张嘴,没问。
终于到平台了,那人说,前面就是大巷了,大巷里有灯,你自己走吧。
五子哥问,咋,你不升井?
那人说,你走吧,我还有事。说完,就顺着绞车坡往下走。
五子哥说,谢谢你,张师傅!
那人说,你走吧。
想起刚才在工作面下巷的一幕,这时候,五子哥一刻也不想在矿井下停留,于是,他顺着大巷,一溜小跑往井口奔去。
走出井口,看到下一班的田牛和李三。田牛问,大过年的,你怎么这时候才上来?
五子哥说,别提了,在下巷的时候灯瞎了,真他妈的倒霉。
灯瞎了,你咋上来了,摸着上来的?田牛又问。
五子哥说,如果不是遇上那个张师傅,我他妈现在说不定还在下巷摸呢。
田牛说,听队长说,今天井下就没几个人,队长老曹还特别嘱咐,在井下两个人别分开,哪来的什么张师傅?
五子哥把张师傅的相貌说了。
田牛有些吃惊,说,你不是说胡话吧。
五子哥说真的。
田牛说,你说的那人叫张福森,可他早都不在了啊。
这下轮到五子哥吃惊了。他说,你说什么?
田牛说,你说的那人叫张福森,他早都死了,就是九四年出事故拉到流煤眼里的那个。
五子哥和田牛、李三去矿灯房查询,矿灯房女工说,今天全矿共下井17人,你是上来最晚的一个。
后来五子哥又问立冬,立冬说,那天从工作面上来一路连一个人影都没遇到。
那个人是谁呢?五子哥百思不解。
老人血
杨汉光
刘东林的父母都去世了,爷爷却还活着。老人已经102岁,在床上躺了大半年,身上臭烘烘的。这天,刘东林从外面回来,听到爷爷一个劲嚷要洗澡,就没好气地说:“都一百多岁了,还洗什么澡?万一死在洗澡盆里,不吉利。”
老人许诺说,如果刘东林帮他洗一次澡,他愿意给20元,说着,还真的摸出2020元钱来。刘东林吃惊地问爷爷连路都走不动了,哪来的钱。老人得意地说:“我是走不动了,可有人送钱来。”他撩起衣袖,伸出枯瘦的手臂,手臂上有一个小小的针眼。原来,今天村主任带一个医生来到刘家,抽了老人的一滴血,给了两千元钱。
刘东林没想到爷爷的血这么值钱,他立刻帮爷爷洗澡,洗得非常仔细。洗完澡,刘东林叫爷爷把两千元都给他,许诺以后天天帮爷爷洗澡。爷爷虽然老眼昏花,可对孙子的为人还看得清楚,他闭上眼睛说:“还是洗一次给20元好。急什么?反正我的钱迟早是你的。”
刘东林可没有耐心等,他当着爷爷的面,翻箱倒柜找起钱来。刘东林整整找了一天,终于在一根中空的床柱里找到了一卷钱,刚好是1980元。看着孙子贪婪地数钱,老人差点没气死。
拿光爷爷的钱后,刘东林还不满足,他想让爷爷再卖点血,就问那个医生是哪里的。老人气愤地说:“我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诉你。”
刘东林只好向村主任打听那个医生的地址,可村主任说,他只知道那位医生姓张,是县领导介绍来的,其他情况就不清楚了。刘东林到县政府去打听,也一无所获。
出乎意料的是,刘东林正为找不到张医生发愁,张医生就打电话来了。接到电话,刘东林才知道,张医生在省城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张医生说老爷子的血很有研究价值,他们研究所非常需要。刘东林高兴极了,说他和爷爷正想再卖点血,请张医生快来抽。张医生却说:“现在还不行,你爷爷身体太虚弱,不但血量少得可怜,质量也太差。我们原来抽的那滴血,就达不到要求。我这次打电话给你,就是请你先好好照顾你爷爷,等他身体恢复健康,血的质量提高,达到要求后,我们再去抽血。”刘东林关心的是钱,他问血的质量提高后,价钱是不是高一些,张医生说:“那当然。”
刘东林看到了发财的希望,主动询问怎样才能提高血的质量。张医生说,主要是让老人营养充足,精神愉快,常买点益气养血的药给他吃。张医生从生活起居到心理安慰,讲得非常详细,要刘东林一一记下来。
刘东林做梦都想发财,他放下电话,就按照张医生的吩咐忙开了。刘东林把爷爷从小黑屋换到全家最宽敞明亮的房间居住,窗台上摆满鲜花,餐餐有酒有肉,每周七天,天天伙食不同,时不时买点益气养血的药给爷爷吃,一有空就坐下来跟爷爷谈心,嘴上说的话比蜜还甜。老人像看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惊奇,问孙子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好了?刘东林装模作样地说:“爷爷,我是你的孙子,理应好好照顾你。我有什么不对,你就说,就骂,打也行。”老人激动地说:“有你这么好的孙子,我就是立刻死掉,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刘东林在心里说:老东西,你可不能死,我还要用你的血换大钱呢。
在刘东林的照顾下,老人渐渐恢复了健康,居然能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门外晒太阳,偶尔还撒一把谷子喂喂鸡。看见红光满面的老人,不明底细的村里人纷纷称赞刘东林孝顺。
刘东林可不稀罕别人的夸奖,他念念不忘的只有钱。刘东林打电话给张医生,说爷爷已经恢复健康了,问他什么时候来抽血。张医生说,表面的健康不等于真的健康,他叫刘东林带爷爷去医院检查一次身体,再把体检单寄到研究所给他看。张医生叮嘱说,一定要寄原件。刘东林知道,张医生是怕自己做假。
刘东林带爷爷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老人的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只有一些小毛病。看来发财的机会到了,刘东林当天就把体检单寄给张医生。寄了体检单,刘东林在心中盘算:凭老爷子现在的身体,抽一瓶血都没问题,按原来的价格,一滴血就能卖两千元,价格提高后,一瓶血能卖多少钱啊!刘东林估计,爷爷的一瓶血,最少能卖二十几万。赚了钱,首先要建一栋全村最漂亮的新楼。
可是,张医生看过老人的体检单后,却说还不合格,叫刘东林继续照顾好爷爷。刘东林有点失望地问:“怎么这么麻烦呀?”张医生解释说,他们搞的研究要求是非常高的,哪怕是一点小毛病,也有可能影响整个课题,他叫刘东林千万不要泄气。
刘东林当然不想前功尽弃,他对爷爷的照顾更加周到。老人见孙子这么好,就尽量多干点活,喂了鸡,又到屋后去摘南瓜花。谁知南瓜叶下藏着一条毒蛇,老人刚摘得几朵南瓜花,就被毒蛇咬伤了脚趾。老人赶紧回屋,脚趾已经肿起来。刘东林像看到新楼倒塌一样,心疼地说:“哎呀,你这个老不懂事的,明明知道自己是全家的宝贝疙瘩,风吹还怕伤身,你摘什么南瓜花?”
刘东林马上请车送爷爷去医院,一路上不停俯下身去,不怕脏臭,用嘴含住爷爷受伤的脚趾,拼命给老人吸毒。到了医院,医生让刘东林先交五千元钱。刘东林问怎么要交这么多钱,医生说老人年纪这么大,交了钱还不一定能救活,他们只有五成把握。
万一交了五千元,又救不活爷爷,那岂不是鸡飞蛋打?刘东林犹豫了,老人也有气无力地说:“我的命值不了五千元了,省下钱给孩子读书,咱回家吧。”
老人的话正合刘东林的心意,他当即假称去另一家医院,把爷爷拉回了家。一回到家,刘东林就打电话给张医生,请他快来抽爷爷的血。张医生说现在还不是最佳时候,刘东林着急地说:“我爷爷被毒蛇咬伤,已经没救了,你再不来,就抽不到他的血了。”张医生还是不肯来,叫刘东林快送老人去医院。刘东林改口说:“要不我把爷爷的血抽出来,送到研究所去给你。注射器我都准备好了,只是不知道怎样保存血浆,放在冰箱里行不行?”张医生终于答应说:“好好好,我马上过去,你可千万不能乱来啊!”
张医生亲自开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刘东林家里。张医生赶到时,老人已经昏迷过去了,他二话没说,把老人抱上车,直奔医院。可惜,还没来到医院,老人就在路上去世了。张医生停下车,轻轻地抚摸着老人雪白的头发,自责地说:“老人家,都怪我来迟了。”
刘东林懊丧极了,望着爷爷的尸体,脱口骂道:“老东西,这几个月我最少在你身上花了一千多元,你怎么说死就死,让我血本无归啊!”
刘东林还不解气,在爷爷的脸上拍了一巴掌,可他的手掌刚贴到老人的脸上,就惊喜地说:“张医生,我爷爷还有点暖,估计还能抽出血来。”
好家伙,刘东林居然随身带有注射器,他立刻掏出注射器,递给张医生。张医生接过注射器,惊讶地问刘东林怎么准备有这种东西。刘东林又掏出一个小瓶子,得意地说:“我做事从来是想得很周到的,看,还有酒精棉呢。”
刘东林请张医生快抽爷爷的血,张医生却摇头说不必了。刘东林急了,一把抓住张医生的手,按到爷爷的身上说:“你摸摸,我爷爷的身子还暖暖的,肯定抽得出血。我知道死人的血不能跟活人的比,以前你抽一滴给两千元,现在按一滴五百元算,行了吧?”
张医生把注射器还给刘东林说:“真的用不着了。”刘东林以为张医生嫌贵,就咬咬牙说:“这样吧,价格由你定,给多少钱我都没意见。快,再不抽就来不及了。”张医生见刘东林不接,就把注射器扔到车窗外说:“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们研究所只要一滴血就足够了,即使你爷爷活着,也不再需要他的血。”
刘东林呆了一会儿,才气愤地问:“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张医生说:“你爷爷的生活连猪狗都不如,我那天是流着眼泪抽他的血的。为了让老人过几天好日子,我不得不骗你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