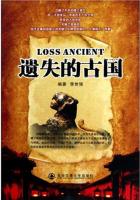还有几位老婆婆靠墙坐着。她们对面,坐着几位老伯,似乎是在集体对话,但更像是在集体婚介会上“见面”。见我们去了,就都闭上了嘴,只朝我们笑——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敬老院领导跟我们说,已经有十来对老人“好上了”。比如有一位60多岁双目失明的荣誉军人,赢得了一位小他几岁的聋阿姨的“芳心”,俩人互相照顾,取长补短,一个给对方当眼睛,另一个给对方当耳朵,都觉得生活变得特别美好,前方有无限幸福在等着他们,日子不再是黄连,还变成了蜜,他们活也活不够了。面对这种种新“情况”,敬老院领导们也都替老人们高兴,还一次次买了糖,替他们办喜事,笑得其他老人合不拢嘴。
我们又去几位老人的“家”里看了看:有的两人一间,有的一人一间。每人一张大床,挂着蚊帐,被褥整齐干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电视机、收音机以及热水瓶、闹钟等生活用品,有的还摆着花。几位老婆婆拉着我们的手,拼命地朝我们绽开笑脸,嘴里喃喃说着“好啊,生活好啊。”
一位陪同参观的工作人员指着一位婆婆说,她孤身一人,没进福利院时候,整天在县城和附近乡村捡拾垃圾,饥一顿饱一顿,身上脏得人见人躲。进了福利院以后,几个星期再见,咦,人怎么变化这么大,穿得简直像干部了,面皮也精致了,像做了美容似的。
哦,我这才突然想起来,这些天在定南县城和一些村镇上跑来跑去,真的没见到大街上有乞丐,也没有脏兮兮的流浪者、老人或儿童,似乎连丧家的狗和猫也没见到。大街上,穿着时尚的姑娘媳妇不少,带着孩子奔忙的中年男女不少,也有不太老的老人们围坐着打麻将,拉胡琴,唱戏,谈天说地。定南人似乎都很安乐,也活得很有把握,很自信。
话说回来,这家集敬老院、福利院、光荣院于一体的社会敬老院,唯一与《桃花源记》有点出入的,是“黄发”多而“垂髫”只见一人。他是一位智障青年,此刻,安静地坐在轮椅里,面对院外被阳光照耀得一片金红的青山,不知在想些什么?旁边,是一位敬老院供养的60来岁的婆婆,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刚出生不几天的小小婴儿,一言不发。院领导说,那个可怜的小婴儿是前天清晨被发现的,夜里他被狠心的父母丢在敬老院大门外面,只因他是个兔唇残疾儿。哎呀,兔唇是可以通过手术矫正的,大家都深深叹了一口气,并衷心为这大难不死的孩子庆幸,祝福!
走出敬老院的大门,我才看清楚这里的地势:景致太好了,四面环山,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聚宝盆,把养老院颐养在中央;周围全是蓬蓬勃勃的绿树和碧草,简直把白云都染绿了,空气的清新不用说天天一级;离县城不远,一条柏油路蜿蜒地旋过山脉,丝绸一样滑进养老院的大门里,也把新鲜的瓜果梨桃和信息和幸福送进院民们的心田……我虽不懂风水一类,但也可以看出,这里的气象不凡,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据说,也是有大亨看中它,出高价,想在此修建度假村,没有得逞。
虽然来自首都北京,但我居然很羡慕这里的老人们——他们的后半生是不用发愁了。现在老年人的生活很有危机,说是中国已经有60岁以上老人3亿多了,而且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逐年飞速上升。城里虽然也有养老院,不过老人们都不愿去住,甚至畏之如虎,视之为子女们的不孝。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此归结为观念的问题。但不去养老院也不成,一个独生子女哪能对付得了四个老人的生老病死,他们自己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还担负不起呢,硬扛也扛不起。如此,各级政府再不重视和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则“和谐社会”会成为大空话。
[材料四]几个村子的新气象
(据历市镇、龙塘镇材料)
1、历市镇中圳村方屋排新农村建设点现有5个村民小组,农户78户,主要以禾笋、种果、养猪和外出务工为收入来源。近年政府投入140多万元,拆除空心房3680平方米,拆除破烂危房和厕所1826平方米;硬化村组道路2600多米,硬化便民小道1320米;改水52户,改水率5%;改厕51户,建公厕1个;硬化水沟790米,硬化房屋檐阶1860米,新砌水渠568立方米,整理粉刷墙面9720多平方米。
2、龙塘镇白驹村辖19个村民小组,社区功能完善,设备齐全,居住地集中,集村部、留守儿童幼儿园、卫生所、超市、休闲健身广场、宣传文化长廊于一体。组织成立了腰鼓队、龙狮队、老年人协会,设立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经常性开展活动,促进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明建设,营造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谐发展的村落社区环境。
3、长富村岗上新农村建设点是一个依山傍水,环境秀丽的自然村落,东江支流从村前面流过。村民受文化教育情况良好,村中无文盲。通过从“路、水、厕、房、墙、阶、池、能”8个字入手(即:修好一条路,改好一管水,改好每户厕,拆完破房栏,粉好内外墙,硬化户檐阶,布好垃圾池,安装太阳能),对建设点进行合理的规划和整治,并尽量保持其原有的建设风格,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较好地体现出客家文化特色。
[韩注]
这说的是中国农村吗?说的是中国农民吗?——尤其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赣南山区一向落后的农村吗?
我是工人出身,“文革”中期初中毕业进工厂,做工8年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有幸考入大学中文系,从此走上媒体从业者之路。除了中学时下乡“学农”,我基本没下过乡,也一向不喜欢农村,因为印象中的中国农村,道路泥泞,鸡猪暴走,畜粪遍地,环境脏、乱、差,百姓穷、苦、愁。特别是有一年到过欧洲的几个小镇之后,我仰天长叹,发明了一句名言:“中国和欧美不差在大城市,而大差在村镇,至少差了300年。”这是痛定思痛之后的大实话,一点儿也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更没有不爱祖国的意思。
可是这次到定南农村,看到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山区各个村镇的变化,真是吃惊不小。由衷慨叹:今日之中国农村,确然然是“换了人间”呀!
中圳村方屋排的村口特别美,几款高大的竹丛有二层楼那么高,宛如一个个巨大的天然盆景,把脚下的石板小路摇曳得风情万种,像是到了植物公园。池塘里的荷花残红,莲蓬却昂头挺胸,把自己丰硕的果实高高举过头顶。公鸡母鸡们都集中在一个三、四十平方米宽阔的鸡圈里,自由奔忙,谈情说爱,无暇顾及我们这些生人。养鱼池边,有一位50多岁的老农在洒饲料,鱼池方形,有三五十米见方,水泥质料,像游泳池一样干干净净的。他介绍说,依据鱼们的生活习性,池里养了鲤鱼、青鱼、白鲢等好几个水层的鱼,构成了一个科学的生态小环境。石板小路边,不时见到玻璃或木质的宣传橱窗,上面是《村民公约》或好人好事的事迹。
一切都好,特别是村子的干净整洁,实获我心,让我心情大好。只是,我有一点不太理解,这个村子为什么叫“方屋排”呢?看看她的农舍,并不像有些北方新农村那样,是统一划齐的一排排房屋,而是各自依据着不同的地形地势,建成了不同风格、不同朝向、不同式样和不同颜色的“家建筑”,有的是平房,有的是二层或三层小楼,外面围着一个小院子,内里种着一些花草什么的。
走着走着,一抬头,我毫无思想准备,竟然突然看见了一个古老的客家建筑——“虎形围”——顾名思义,就是一个老虎形状的客家围屋。
已是下午5点多钟,在不远处苍山的衬映下,暮云四合,“虎形围”还真像是趴在沃野中的一只老虎,有着一种苍茫的山水田园画意:它的直立面大门,象征着勇猛的虎嘴;灰色的多层门罩,象征着标有“王”字图案的虎额;两个圆形的窗户,象征着炯炯有神的虎眼;正立面两侧的两座雕楼,象征着两只蓄势待发的虎爪;围屋后立面的那座雕楼,象征着刚烈的虎尾。俗话说,“虎为百兽之王”,这栩栩如生的猛虎形围屋,被一个个建筑文化元素体现得如此精巧,在全国全世界别的地方还真没见到过,大饱眼福。
而听了有关它的人文故事,则更是心有所动:原来,“虎形围”系当地的方氏家族所营建,该家族于明代洪武年间于江西信丰县迁入此地。“虎形围”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它对周边生态环境的选择,是按照传统的风水理论进行的。围屋选址在一个山间小盆地,四周砂山屏立,现青龙昂首之姿态,呈藏风聚水之格局。“虎形围”的建筑文化意象,对内寓意着围屋的主人虎虎有生气,无往而不胜;对外彰显出赫赫虎威,神圣不可侵犯。数百年间,方氏家族在其中劳作生息,繁衍丁口一千余人,还养育出了当代名人方其道。方自幼饱读诗书,做过教师、记者、报社经理等职,还对字画、碑帖、拓片颇有研究。他亦是刘和珍的未婚夫,俩人已订婚6年,只待刘毕业后完婚。刘和珍在1926年的“3·18惨案”遇难后,方其道悲痛万分,慨然为她写下悼词:“生未同裘,死难同穴,疆场共有约,六载订婚成一梦;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劳燕惜分飞,白宫溅血泣黄泉。”
想不到,在定南这偏僻的大青山里,竟还珍藏着这样独一无二的客家建筑,还流传着这样动情和悲愤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