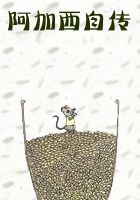竺可袖确实打心里喜欢这位“BabyProfessor”,师生们也都欢迎娃娃教授王淦昌。他年轻,有学问,由于师承叶企孙、吴有训两位导师的教学精神和教学方法,既重言教更重身教,既重理论也重实践,特别在实验物理和实验制备方面的杰出表现,都给人以美好的印象,这更引起竺校长的特别关注与依赖。竺可桢在笔记中不乏对他的记述。王淦昌参加攀登西湖北岸葛岭的比赛,《竺可桢日记》也有记载:王淦昌只花了8分钟,就到达峰巅,争得第一名,获奖品《小男儿》本。
刀茅巷记事
竺可桢不忘许诺,很快派人去江苏常熟支塘镇帮助王淦昌搬家。他的一家终于能团聚了,住在学校附近的刀茅巷内。房屋当然是房东的。那是一个小院落,一排共五间,有桃李树,也有几丛幽篁,甚宜家居。他只祖住两间平房,用泥糊竹篱墙隔成小四间,安顿全家六口人。王淦昌热情,妻子又很温顺娴静,儿女们受父母影响,都很乖,因此,房东甚为喜欢王家,逢人都说,小院里迎来了一个有学问的人家。
不久,朱福抖和张绍忠两教授应聘从南开大学来浙大任教,无住处,王淦昌与朱福抖虽是头一次见面,却心无芥蒂,主动邀请他与自家同住。他去与房东交涉,将院内剩下的三间房以相同的租价租给朱福抖一家住。房东感于他助人为乐的精神,欣然出租,说,王先生的好友,肯定也是好人家。
朱福抖一家只有三口,却能住上三间,过意不去,多次提出要将三间换王淦昌的两间,王始终不同意,还开玩笑说:“现在论间数,我已比你多一间了呀。”但此事让朱福抖看在眼里,挂在心上,望着他们进进出出的一家人,尤其是两个上小学的年幼的孩子,心里总有某种内疚感。一遇到适当机会,他总要有所表示。比如远方来的故旧,乡间来的亲戚,非留宿不可时,他知道后,总要招呼年长的孩子到他家,搭个临时铺位,以解燃眉之急。两位教授相让方便的情谊,深深打动了房东的心,房东教育自家儿女,学他们的榜样。
吴月琴虽然出身于殷实人家,但由于多年单独理家,很会调理家庭生活,钱花得不多,却能给全家做出美味可口的饭菜。她但凡做出新鲜的菜肴,都要孩子送去给邻居尝一尝。由于每家都很爱护邻居,自然而然给王淦昌和朱福抖造就了优良的生活环境。
王淦昌更是因为有朱福抖这样的好友为邻,感到非常满意,他俩一有闲暇就在一起研讨从外文期刊上发现的科技前沿问题,或者交流教学经验。往往是,一壶龙井茶,一席饶有兴味的交谈。朱福抖对王淦昌敏锐的科学才思甚为赞赏,他为自己能与这么一位热情而又有才华的好友为邻感到万幸。他们的往来如此密切,以至谁半夜里有什么问题,或者解决了哪一个难题,都会情不自禁地去敲邻居的房门,一聊,就聊到天亮。
事实上,竺可桢校长上任不到一年,确实像哥廷根大学的爱结交优秀学者的希尔贝特教授一样,吸引来其他大学的着名教授。有这样一个教授群体,浙大将如旭日东升,光耀全国教育界与科学界,并将成为东方的“剑桥”或“哥廷根”。
从此,王淦昌再不感到孤单了,他一心扑在教学和研究上,每天都去庆春街那幢深绿色的号称阳明馆的楼房讲课,或带领学生做实验。他常对学生们说,没有实验研究,中国的物理学就很难达到国际水平,更难获得物理学的领先成果。他自已首先一头扎进图书馆。浙大的图书馆藏书较丰富,世界各国的物理学家的着作或理论期刊比较齐备,国内堪称一流。他埋头阅读德文、英文的各类物理期刊,摘录其中有关章节整理成卡片,以备教学研究之需。在经费紧张、条件欠佳的情况下,他带领学生做实验仪器。搞一个云雾室,没有橡皮膜,就找一具破球胆代替;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手工打气筒,逐步搞出了一套颇具规模的实验设备。他一心要想做的是建立一个云雾室,以便开展研究工作。为此他多次向校方提出建议,企望得到支持。
然而他也不是那种只知终日埋首书斋和实验室的呆子。毕竟年轻,满腔热血,对于国家兴亡,民族的命运时刻记挂在心。最忘不了那个历史性的一天。那是1936年抗日声浪高涨的一年,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在抗战关键时刻,发动了着名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到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宣布取消“西北剿共总部”,并提出一系列的抗日救国主张,一时间风云色变,引起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王淦昌一向关心国家安危,对此事格外留心。忽然有一天听说蒋介石被放出来了,他想到实验室听广播,匆忙中忘带钥匙,便急中生智,从气窗翻进去,打开收音机,听取“西安事变”的新闻。那轻捷灵敏的翻窗动作使观者无不叹服,于是众人便赠他“燕子王三”的绰号。这亲昵的称呼包含了师生对他的喜爱。
此前的1937年5月,世界物理巨人、欧洲三大科学中心之一的哥本哈根大学的领袖尼尔斯·玻尔来华讲学,不久,来访浙江大学。他的到来,宛如穿透乌云的阳光,给这座西子湖畔的大学带来极大的喜悦。
众所周知,尼尔斯·玻尔创立的氢原子理论,出现在量子力学诞生的前夜,被认为是量子力学发展的里程碑。物理学界都说,他是一位最能唤醒人们沉睡着的最大才能的导师,但他的最伟大之处,是创立了科学界同行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和谐的自由讨论的学风,世称“玻尔学风”。一位科学史家说:“玻尔是个帮助观念诞生的产婆。”他像苏格拉底一样,深信通过自由讨论发现真理的方法是最理想的。
玻尔热情而随和,他身上没有一般科学学府首脑所固有的两个特点一既是教育家,又是暴君。无论谁对他的思想进行批评,他都微笑着听,甚至对粗暴的批评者也总是微笑以待。1930年,学生们根据他的性格特点,编出讽剌剧《浮士德》上演,剧中的神显然是玻尔本人,而恶魔梅菲斯托就是他的学生鲍利,鲍利经常无情地批评他。
玻尔最突出的缺点是口才不好。往往在讲到最重要的问题时他就压低嗓门儿,把德语、英语、法语混合在一起,使人弄不明白他是故意迫使你费力去听呢,还是他在语言上的糊涂,但效果却是异乎寻常得好。玻尔的疏忽与健忘更为显着,在美国,他曾使一再叮嘱他千万别暴露原名的情报局保镖难堪,当他遇见一位熟人时,居然纠正那人对他的称呼,说:“我现在不叫尼尔斯·玻尔,我被可敬的先生们更名改姓了。”他的这些缺点常常引起同行们友好的微笑。然而,他对真正重要事情的专注精神更为突出,因此能在科学上做出卓越的贡献。1932年,丹麦政府为了感谢这位丹麦最有学问的人,把卡里斯堡城堡交给他使用。
这位卡里斯堡城堡的主人,在希特勒驱赶犹太学者的黑暗岁月中,把他的领地作为受难者的安全岛,使许多着名教授团结在他周围,组成一个和睦的国际大家庭。甚至德国外交家的儿子卡尔·弗里德亚希、冯·魏茨塞克和被驱逐而离开德国的爱德华·泰勒等不同阵营的学者也能友好相处。这都有赖于尼尔斯·玻尔的成就和他的为人。他,既能团结上帝也能感化魔鬼。5月20日,尼尔斯·玻尔一家应邀到上海讲学。浙大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教授前往迎接,23日陪同他来到杭州。
这一天,对于浙大是个极为重要的日子。王淦昌在德国留学时未能去北欧的哥本哈根,现在终于能如愿会见玻尔,而且还见到玻尔的一家,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玻尔虽健忘,却是记得他看过王淦昌与迈特内发表的那篇论文。据说,王淦昌的那篇博士论文对反应堆之父费米教授某一课题研究曾有所启发。琐事糊涂的老玻尔,对重要的科学课题却是从不忽略的。他在与丽丝·迈特内的交谈中,自然得知王淦昌的来历,尤其是那个令这对师生遗憾的事件。
“我知道你在达列姆小镇留下一个遗憾。当然,迈特内的叹息声也久久萦绕在威廉皇帝的围墙里呢。”尼尔斯·玻尔一见面就与王淦昌热情握手,开玩笑道,“不过,您爱运动,到底翻过了皇帝的围墙一迈特内说,您是科学界优秀的猎手,不管是谁,不管你猎运如何只要能钻进去,准能发现科学前沿的径迹,而且能想出妙法,玩捉迷藏一样,会很巧妙地捕捉粒子世界里的猫。”
王淦昌抱愧地笑道:“可是,我在达列姆没逮到猫’只抓到耗子。”
尼尔斯·玻尔天真地笑:“发现鼠洞的人,何愁抓不到猫呢,我敢肯定,你将捕捉到老虎。”
24日上午,他陪同玻尔一家去游西湖,玻尔参观了三潭印月、虎跑泉、花港观鱼、苏堤、雷峰塔等景点,赞叹不绝。在听他的儿子汉斯·玻尔说,西湖是个迷人的美女后,他笑着问王淦昌,汉斯的比喻可否有诗意。
王淦昌吟诵宋代苏东坡的诗给他听: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巧秀美,无论怎样翻译,也难使这位欧洲学者理解,但他凭直觉已领略到享有“人间天堂”美誉的西湖的秀丽了。
王淦昌呢,却一直在探询物理美,他不失时机地向老玻尔请教。玻尔则一边游览,一边向王淦昌介绍关于原子核的复合核和液滴模型的思想。
玻尔谈话时爱抽烟,但烟斗里的烟灭了,他却不知道,依然吸。他的夫人见他干吸,便温婉地笑着划火柴把烟点燃。
下午,玻尔在浙大新教学楼阳明馆三楼大教室讲演《原子核》。演讲会主持人是文理学院胡刚复院长。胡教授热情且健谈,往常,他一打开话匣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总难打住。
这次,按拟定的程序,先由他讲几句开场白,即请玻尔演讲。不料,胡教授一开口,就忘了时间,讲了15分钟,兴犹未了时,尽管随和的老玻尔笑微微地不介意,玻尔夫人温雅而娴静地坐着,准备为父亲放幻灯片的小玻尔颇有耐心地坐在放映机旁,一家人都显现出高度的涵养,王淦昌他们却都急出汗来。人们悄声议论,再不提醒胡先生,这个讲台就没有玻尔的份儿了。于是,王淦昌给胡先生递个条子,请他把时间留给玻尔。他看一眼条子,即说:“对不起,对不起,请玻尔教授讲。”玻尔笑,台下的听众也笑,全场的人都笑得很开心。
玻尔的讲演,由浙江电台同期向全省广播,不仅使浙大师生受益,全省学界也受益匪浅。
玻尔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演讲。他用英语讲《原子核》,王淦昌做概要翻译。他介绍了原子的内部结构,原子核的组成部分,以及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又讲了放射现象,原子蜕变理论。为了帮助理解,玻尔的儿子还放映幻灯图像,让人们看到核衰变的迹象和宇宙线产生的簇射。
会后,王淦昌就这些学术问题与玻尔热烈讨论。25日,他在与束星北教授送玻尔一家到离杭州40公里的长安车站途中,继续与玻尔探讨了宇宙线中的联级簇射,这是他当时想研究,至今仍很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束星北教授则询问玻尔他本人与爱因斯坦发生歧见的根本原因。
玻尔也回答其他问题,略略描述欧洲科学家的处境。他问王淦昌今后的打算。
王淦昌说,努力去探索一些新问题。
一声凄厉的车笛划破长天,车到站了,离别的时刻也到了。尼尔斯·玻尔送他下车,在站台握手良久,末了说:“无论多么艰难,路总是伸向未来的,猎手是不会在森林里迷失目标的,我深信……”
此后,王淦昌难有机会见到玻尔,但这一次,却是他终生难忘的会面。1985年,在玻尔逝世20年之际,他为玻尔诞辰100周年写了一篇题为《深厚的友谊,难忘的会见》的纪念文章,发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纪念玻尔专辑上。
就在玻尔走后两个月,也就是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我中华大地。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从此,拉开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画卷。“八一三”事变的爆发,标志日本侵华战争已从华北扩大到江南地区。
王淦昌和所有爱国知识分子一样,难以安坐家中,他和物理系实验室管理员任忠英一道,走上街头宣传抗日,鼓励大家捐钱捐物。一些人便捐出家中值钱的东西,甚至有些过路的陌生人,也乐意掏一掏腰包。
动员了别人,他自己能捐多少呢?他心中没底。谁知深明大义的吴月琴,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包银圆端出来,说是自已从娘家带来的,足有十斤重呢。同时,还撸下自己的金手镯,摘下金耳环,一并放在那堆银圆上。
王淦昌深受感动道这是侬(你)结婚时戴的,怎舍得呀?”吴月琴叹口气道:“眼看国家都快保不住了,还有舍舍不得呀?只要侬(你)活着,儿女都活着,有国有家,比啥都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