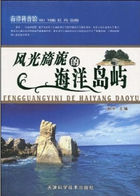犹太人的上述两项特征,我认为是最为本质性的。这些标准和理想渗透在犹太人做的一切事情之中。在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中,在朋友间的闲谈中,在宗教的经典中,随处可见这种传统的存在,而这个集团的公共特征,也就是这种传统。我觉得,这些独特的理想是潜存在犹太人性格的本质之中的。当然,这些理想也无法在这个集团中得到完全的展现。然而,介绍一个集团的根本特征的最好办法,就莫过于描述集团的理想了。
在我的想象中,犹太人是一个有着公共传统的集团,可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对我这个观点都表示反对,他们经常说:作为一个种族,犹太人有着独特的行为,并且是由遗传基因造成了这些行为。几千年来犹太人内部通婚这一事实,似乎为这种看法提供了基础。一个种族的确能通过这种习俗来确保其种族的纯粹性。然而,这个种族如果本来就是一个多种族的混合体,也就谈不上什么种族的纯粹性了。而毫无疑问,正如同我们文明国家中的其他集团一样,犹太人同样是一个混杂的种族。对于这一点,人类学家不会有任何不同意见。
犹太人集团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受到敌视和压迫,这才是它兴旺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着独特的传统。它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犹太人集团的总人口大概是一千六百万,大约是今天波兰人口的一半,这个数目连全人类总数的百分之一都不到。他们在政治方面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们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栖息、游走,却缺乏一个整体的组织,因此无论在什么方面,他们都无法统一行动。
如果仅从敌视犹太人者所描述的犹太人形象来看,你们会得到这么一种感觉:犹太人是一种世界性的势力。乍一看去,这好像颇为荒诞,然而我觉得,却有些东西藏在其中。作为一个集团,犹太人的力量或许不足为道,然而人们随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成员所取得的成就,即便是在通过了重重障碍之后他们才获得了这些成就。个人的力量被此集团的精神所激励,因而各个人都积极从事着艰苦卓绝的工作。
所以,犹太人就受到了那些有专权野心的人的仇视。人们理智上的独立是他们所畏惧的,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让他们这么畏惧。现在德国之所以如此猖狂地迫害犹太人,这就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在纳粹集团的眼里,他们不仅仅将犹太人当成转移人民敌对视线的工具,他们更是觉得,犹太人是他们无法同化的,犹太人是不会屈服于他们的,犹太人只要依然存在,就严重地威胁着纳粹的权威,因为人民群众会从犹太人那里获得理性判断的能力。在篡夺政权之后不久,纳粹就搞了一场隆重的焚书仪式。我上述看法所触碰到的核心问题,从这件事中就可以看出。
社会科学以及政治学领域中弥漫的抽象理论,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当这种抽象理论紧紧地控制思想的时候,特殊因果关系就无法对事物作出合理的解释,就会不公正地判断事件的复杂性。然而就另一方面而言,对抽象理论的放弃,也就是对认识的彻底放弃。因此,我相信抽象理论的存在是必须的,只要我们能时刻警惕抽象理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些,我才愿意将自己对排犹主义的看法谨慎地说出来,我就是从一个带有抽象理论的观点出发,从而形成这种看法的。
有两种相反的、互相斗争的倾向在政治生活里起着作用。乐观的倾向是其一,它认为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状态能通过个人和集团的自由扩展来形成。这种倾向意识到,一个高于个人和集团的中央权力是必须的,然而这种权力的作用被限定在调节和组织上。悲观的倾向是其二,它认为社会会被个人和集团所破坏。所以,有着这种倾向的人就试图以权威和盲从来建构社会的基础。事实上,后一种倾向的所谓悲观也仅仅是相对的:因为对于那些掌握权威和权力或有着这类野心的人而言,这种想法是乐观的。第二种倾向的信徒都天然地敌视独立和自由,因而也是独立和自由的敌人。政治上的排犹主义,也就是由他们造成的。
美国的人们最起码在表面上都对第一种乐观的倾向表示支持。然而,美国依旧存在着第二种倾向,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隐藏着。这种倾向在美国是迂回前进的,它通过对生产手段的控制,一点点从精神和政治上统治人民,排犹主义和敌视他人这件武器已经被它的倡导者所注意到,然而因为人民的政治本能较为健全,截至目前,他们都还没有得逞。
未来也会一直延续这种情况,然而我们只要坚守这么一条准则:做好自己的事,特别是在他们煽动仇恨之时能洁身自好,那么,他们的阴谋就永远无法得逞!
为建议研制原子弹给罗斯福总统的信
尊敬的阁下:
通过费米和西拉德近期的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铀元素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新能源。这一情况是政府必须密切关注的,若是有必要,更应该果断地行动起来。所以,我认为这些事实和建议是我有责任向您提醒的。
在铀中建立起原子核的链式反应已经成为了可能,这要得益于法国约里奥以及美国费米和西拉德四个月的辛苦努力,才会有巨大的能量和大量放射性元素从这样的反应中产生而出。就当下的局势而言,这种可能和现实之间并不遥远。
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炸弹能通过这种新现象制造出来。若是在港口引爆这种炸弹,足以完全摧毁整个港口以及它周围的一部分地区。这种炸弹可能会很重,所以空中运送是无法做到的。
美国只有少量品位很低的铀矿。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加拿大都有不错的铀矿,而比利时属的刚果,则是铀资源储藏最重要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政府应当密切联系这批物理学家。政府若完成这件事,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一个您信任的人,让他以非官方的资格承担这项工作,大概是目前最可行的办法。他要做到这些:
a)定期将实验情况汇报给政府各部,并且对政府的行动,尤其是在铀矿供应方面的行动提出建议。
b)加大预算开支,改善实验设备和实验条件,努力加快实验进程。
德国所接管的捷克斯洛伐克产出的铀矿,已经被德国停止出售。他们想要在这方面领先一步,也许能够说明他们已经行动起来的事实之一就是,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里面可以看到德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儿子冯·魏茨泽克的身影。
您的最诚恳的
A.爱因斯坦
1939年8月2日
客观世界的完备定律及其他
——1949年9月7日给M.玻恩的信
你的信我已经看到了,感觉非常愉快,以至于迫不及待地想给你回信。
有一件大概发生在二十五年前的事,你是否还记得?我们那时一同搭乘电车去国会大厦。我们坚信可以给那里的人们以有益的帮助,将他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使之成为民主的坚定支持者。那时我们都已经40岁了,可是如今回想,竟然是那么天真,所以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还忍不住笑话自己。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搞清楚,较之于脑髓,脊髓更有力地支配着人们。
我现在之所以要回忆起这件事,就是为了使自己那些往日里的悲剧性错误不再重演。我们确实不应该惊诧于下面的事情:绝大部分的科学家都无法逃离这条规律。当然,也有例外之人如劳尔,那是因为他有着不同的个人气质。在强烈的正义感的驱使之下,劳尔一点点和那些好战分子划清了界限。医务工作者在伦理规范方面一点贡献都没有,和医务工作者一样,那些有着特殊的和机械的思维方式的纯科学家,同样不会试图对这样的状态做出改变。你准备让尼尔斯·玻尔担任合适的圣职,我赞同你的这个想法。我希望你这样做会产生这样的效果:玻尔会把他教士的一方面从物理学里面剥离出去,而用其他方法来实现它。先不论玻尔如何,仅仅就你打算做的这件事而言,你还是不要抱着太大的希望为好。对于那些已经变成了事实的事情,我们应当做什么又不应当做什么呢?对于奇迹的发生,我是不抱有期待了。当社会上布满了流言飞语,个人就只能做好自己,将自己树为榜样,将伦理的信念坚定地举起来。这种自律的精神是我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依靠它我才获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绩。你在信中说:“我感觉自己已经老了……”这样的感觉我也是有的。这样的念头有时会突然蹦进我的脑子里,不过很快就又会消失不见。因此,对于你说的“老了”这句话,我不打算将之当一回事儿。若是大自然这么安排了,我们就宁静地接受就是,让自己慢慢回归到大地之中。
我也读了你对黑格尔主义讲话的反驳之言,并且对这些很有兴趣。某种堂吉诃德式的东西体现在黑格尔主义的讲话之中,它是否在诱导我们反感并反对当局的做法呢?凡是顽固的反对派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都会出现这种坏事。所以,我坚信他们杀不绝“犹太人的物理学”。有一句格言在我读了你信中的一段话后自然地冒了出来:“青年****——老年固执”,特别是我在想到麦克斯·玻恩的时候,这句格言就一直在脑子里回响着。你说通往后一范畴的道路已经被你彻底地奋斗了出来,我对此却不大相信。
在对科学的期望之中,我们已经成了对立的两极。我信仰有完备的定律和秩序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你却坚信上帝在掷骰子。我正试图用某种发散性的思辨方式对这个世界进行把握。对于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即:肯定会有个比我强的人,会将一种更合乎实在论的办法找到,从小处而言,就是会将一种更确定的基础找出来。量子理论在开端所获得的成就堪称伟大,然而我依旧无法相信世界在本质上就是这种骰子游戏。假如我年轻的同事们听到我的这个观点,肯定就会说:“爱因斯坦已经过时了!”虽说最后的结局现在还处于迷雾之中,然而我们的话会在历史中得到验证,到了那个时候,就自然清楚我们谁对谁错了。
科学家的道义责任
——1950年10月给“意大利科学促进会”的贺信
首先,对于因身体原因而无法参加此次会议,我深表遗憾,并且诚挚地感谢你们的盛情相邀。若是身体没有问题,我是很想前往的。既然情况已经是这样,我也就只能在重洋之外的家中写这么一封简短的贺信给你们。在这里,我没有什么高深的观点想要陈述。然而我想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明确的目标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躁动不安的,所以,也许仅仅将自己的信念表白一番,也不无益处,虽然这些信念如同所有的价值判断一样,一经推敲就漏洞百出。
如今我们面对着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把工作的唯一目标设定为对真理的追求?换而言之,是否有某些其他的目标凌驾于对真理的追求之上,比如对于“实用性”的考量?我们无法根据逻辑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无论我们给出的答案是怎样的,只要它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在道义和思想上的判断。那么,我的表白是这样的:我觉得,对真理的追求是诸多目标的其中一个,若是缺乏了这个目标,一个人就是再有思想,其对待生活的积极而自觉的态度也会逐渐消失。
在本质上,我们对于真理的追求其实就是:一方面想要将众多人类的经验都总结起来;另一方面,又总是力图在总结的时候遵循经济和简单的原则。因为我们的科学知识还说不上极为丰富,因此对于这两个目标能够并存还是没有怀疑的,此时,这个问题又进入了信仰的范畴。若是缺乏了这种信仰,我对于知识的独立价值的强烈而坚定的信念就会崩塌。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科学家的这种态度跟宗教的态度很相似,他们的整个人格都受到了这种态度的影响。只有那些由逻辑的规律和经验的积累中所得到的知识,科学家们才会去相信。于是,那种个人的自相矛盾的状况就出现了,即他竭尽全力地对客观事物进行研究,然而就社会的观点而言,他却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最起码就原则上而言,科学家相信的只有他自己的判断,除此之外的所有事物都要被他打个问号。所以这样一个判断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历史上,同时出现了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以及个人主义精神,并且至今为止它们依旧形影不离。
有的人或许觉得,这种纯个人主义的科学家,就像假设中的“经济人”一样,实际上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科学家如果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那就不可能有我们现在所谓的这门“科学”,即便有,它也无法拥有现在的这种生机和活力。
当然,在我看来,并不是所有看上去似乎在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工具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科学家。只有那些有着生气勃勃的科学精神的人,才是我心目中的真正的科学家。
那么,在对待当下的社会的态度方面,现在的科学家又是什么样的呢?很明显,他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的工作帮助人类将经济生活彻底改变,将手工劳动从历史中淘汰。然而就另一方面而言,因为科学家的工作被那些当政者所掌控,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因此又感到苦恼。他还认识到,他的工作所带来的那些技术方法,已经使少数人能够并已经掌控了经济权力乃至政治权力,群众的生活被他们完全控制。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金字塔塔尖站立的人越来越少,他们不但在经济上控制科学家,并且科学家也因此而逐渐丧失了精神的独立。科学家真正独立人格的发展,因为政治施加在科学家身上的精神影响而受到阻碍。
所以,就好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现在的科学家正跋涉在悲惨命运的道路上。他们以超乎常人的努力对人格独立和科学真理奋力追求,但却制造出了可怕的工具,当政者利用这些工具从经济上奴役他,更从精神上毁灭他,在那些专权者的压迫之下,他只能委曲求全。他似乎成了一个士兵,不得不将别人的生命消灭并要牺牲自己,虽然他也明白这是种愚蠢而荒谬的牺牲。他非常清楚:历史的发展已经使得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了国家政权的手中,所以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他同时也明白,要想将人类从可怕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就必须创建一个以法律为根据的超国家制度。然而科学家并未这般行事,他们已经是如此堕落:他们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国家政权强加给自己的奴役,心甘情愿地让自己成为毁灭全人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