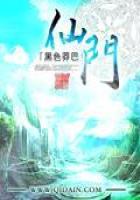在看了康塞普西翁之后,我不知道有多少居民没有受伤,许多房子向外倒下,因此在街道就形成了砖瓦和垃圾小山。鲁斯先生是这里的英国领事,当第一次震动警告来临时,他正在吃饭。在他的一边房子如同雷打一样地崩塌时,他刚刚跑到院子中央。他有逃生的现成主意在脑海里:如果他能跑到那些屋顶已经掉落的废墟上,他就能安全逃生。在大地震动之时,不能站立起来,于是他用他的手和膝盖向前爬,不久就爬上了稍高一些的地势,很快,另一边的房子也向内倒下,大梁木紧贴在他头上飞过。他的眼睛被蒙住了,他的嘴巴也被灰尘堵塞了,这些灰尘把整个天空染黑,最后,他终于来到了街上。震动接踵而至,在间歇的几分钟里,没有人敢靠近震毁的房子。
没有人知道他最亲爱的朋友和亲人是否伤亡或需要帮助。那些抢救了一点财产的人不得不一直睁大眼睛防止小偷光顾,每一次小余震发生之时,他们都用一只手打着他们的牲畜,叫喊着上帝保佑,另一只手则攥着从废墟里找来的东西。茅屋顶着火了,火焰向四处乱闯。几百个人知道他们自己的财产毁掉了,很少有人能找到食物。总的说来,圆拱门或窗户比房子别的部分更经得起震动。无论如何,一个贫穷瘸腿的老人,依照他的习惯,在地震时钻进了一个门道里,这一次被压成了碎片。
地震后很快就看到3到4英里远的地方来了巨浪,到了海湾中心,轮廓显得十分平滑。但是到了岸上,它撕裂了村舍和树木,横扫岸上的一切,气势不可阻挡。在湾头,形成一道可怕的白色浪花,冲起的浪花离潮面的垂直高度可达23英尺。它们的力量应该相当强大;在城堡,一个加农炮连同它的运具,估计有4吨重,被推了15英尺远。一艘纵帆船被刮到残垣断壁间,离海边有两百码。后两波潮水紧随着第一波而来,在潮退的时候带走了许多漂流残骸。在港湾的一个部分,一艘船被高高地抛向海滩,又被潮水带走,再一次被送到海滩,又被海水卷走。在另一个部分,两只停靠得很近的大舰船被转来转去,它们的缆绳3次缠结在一起。
虽然抛锚在36英尺深的地方,它们有时还会搁浅。大波浪也许会移动得稍微缓慢一些,所以塔尔卡瓦诺的人有时间跑到镇后的小山上去。一些海员,在海浪到来之前向海里奔跑,能成功地跑到船上,安全地乘风破浪。一个老妇女和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冲到一艘小船上,但是却没有人划船,这条船结果撞向了锚,裂成两半,老妇女淹死了,小男孩抓住船的残骸,几小时之后被救了上来。咸水坑依旧滞留在残垣断壁之间。小孩子们用旧桌椅制成小船,显得很高兴,但大人们却愁眉苦脸。然而,在这场灾难之中,去观察居民的积极性和高兴指数,应该是很有意思的。鲁斯先生,以及他带领着的一大群人,第一个星期生活在苹果树下,像野炊一样,民众还显得很高兴,但不久就来了大雨,引起许多的不便。他们没有一点点可遮蔽风雨的地方。
生活在塔尔卡瓦诺的普通居民认为,地震是一些印第安老女人引起的。印第安老女人两年前被冒犯了,她们阻止了安图科火山的爆发。这种愚蠢的想法很有意味,因为它显示了经验教导他们去观察:被压制的火山爆发和地面震颤有关系。
特别是这种情况下,据船长菲茨·罗伊说,有理由相信安图科没有被影响。然而,在大地震发生后的20日,此地西北方向360英里的胡安·费尔南德斯岛,却在剧烈地摇晃,许多树都被震得互相撞击,而靠近海岸的一座海底火山迸发出熔岩。这些事实很引人注目,因为这座海岛在1751年的地震中,比起其他和康塞普西翁同等距离的地方受到了更大的影响。看起来,这两个地方有地下的连接。
奇洛埃,康塞普西翁的南部340英里,比起瓦尔迪维亚附近的地区,这里震动得更加剧烈,然而,瓦尔迪维亚的维拉莱卡火山没有被影响到,而在奇洛埃对面的科迪勒拉的两座火山同时强力爆发。这两座火山以及附近的火山的爆发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10个月之后又被康塞普西翁的再次地震影响。一些人在这些火山之一的山脚附近砍柴却没有感受到20日的地震,尽管整个附近省份都在颤抖。
这里成了我们的一个减轻火山灾难的地方,一个地震避难所;根据一般人的信仰,如果安图科的火山没有被巫师封住,那么康塞普西翁可能也会一样。2年3季度后,瓦尔迪维亚和奇洛埃又地震了,比起20日的,这次的破坏性更大。在乔纳斯群岛的一座岛屿永久地被增高8英尺。我们可以自信地下结论:这些刚发生时轻微、慢慢抬高了大陆的力量和那些在随后从火山孔喷出物质的力量,是一样的。
很值得注意的是,塔尔卡瓦诺和卡亚俄(靠近利马),这两个地方都处于很大的很窄的湾头,在每次严重地震中遭受海啸波浪之害;而坐落在深水边缘的瓦尔帕莱索,虽然经常遭受到震动,但没被完全击倒。
我不试图去描绘康塞普西翁所展露的所有细节,因为我感到很难去传递那些乱七八糟的我经历过的感觉。一些船上的官员在我之前就去看过,但他们的语言却没能描述出那个场景的凄凉。
看到花了那么多时间和劳动完成的成果在一分钟之内被摧毁,那是很痛苦和羞耻的事情。然而,在人们所说的时间长河的一定时间里,由于看到了许多事情的令人惊讶的发展,我们的同情也差不多没有了。我的观点是,自从离开英格兰以来,我们很少看到这么有趣有意义的事情。
单单地震就足以摧毁任何国家的财产,如果潜伏在英国脚下的地下力量能显示出它的威力,那么在以前的地理年代毫无疑问显示过,那整个英格兰会变成什么样呢?如果干扰性的新时期开始了,在死气沉沉的夜间爆发了一些大地震,那么,高楼、浓密的城市、大工厂,以及美丽的公有和私有大厦,将会变成什么样子?那种大屠杀多么可怕,英格兰会马上破产。所有的纸张、记录和书籍将从那个时刻消失。政府不能去征收税收,无力保持权威,暴力和劫掠不能受到控制。大城镇的饥荒即将开始,流行病和死亡也随之而来。
5月14日,我们到达了科金博,晚上,船长菲茨·罗伊和我以及英国此地的居民爱德华先生一起吃晚餐,一个短暂的地震开始了,我听到了远方传来的滚动声,但是,这时传来了女士的尖叫声,仆人的跑动声和几个绅士冲出门口的声音,所以我分辨不清那个声音了。一些妇女随后恐惧地哭叫,一个绅士说他晚上不能入睡,如果入睡了,就会梦见房顶掉落下来。这个人的父亲最近在塔尔卡瓦诺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他本人于1822年在瓦尔帕莱索勉强躲过一块掉落的屋顶。他提到一个有趣的巧合,他当时在玩牌,一个德国人,也是牌友,站起来说,他永远不愿意坐在这个国家中房门紧闭的房间里。出于他以前所遇到过的危险,在科帕坡差点丢掉老命。于是,他打开了门,很快就听到他大叫“它又来了”,着名的地震开始了,屋里的所有人都逃走了。危险不在于地震发生时没把门打开,而在于墙壁震动时门被卡住了。
然而,对土着和老居民的过度恐惧,我不会太过惊讶,这些土着以及老居民,虽然他们的一些人是很强的意志力控制者,普遍经历过地震。然而我想,这种过度的恐惧可能部分地应归结于控制恐惧的习惯性缺乏,这不是一种会让他们感到羞耻的情感。实际上,土着居民不愿意看到漠不关心、冷淡的人。我听两个英国人说,在一个可知地震即将来临时他们正在空旷的地方睡觉,知道没有什么危险,所以连爬都没有爬起来。那个土着愤怒地大叫:“看,这些异端,他们甚至不从他们的睡袋里爬出来。”
降雨
从瓦尔帕莱索沿海岸向北出发,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荒芜。这里的山谷,很少有足够的水能用来灌溉。附近的地面相当裸露,草少得不够山羊吃饱。春天,经过几场冬雨后,贫瘠的牧场迅速变绿,牛群从科迪勒拉山上下来,能在一小段时间内吃到青草。去考察草和其他的植物如何使它们适应这样的雨量(好像是习性),是很有趣的。雨水落在海滩沿岸的各个地方。在远北科帕坡的一次降雨对植物的作用顶得上在古尔斯克的两次降雨,顶得上在肯查理的3到4次降雨。在瓦尔帕莱索,冬天是如此干燥,以至于会伤害到草场;而古尔斯克会产生最不寻常的丰收。在肯查理,瓦尔帕莱索60英里以北,不到5月末是不会有降雨的,而在瓦尔帕莱索,一般是在4月初降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