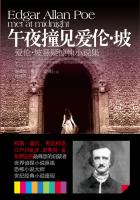式欧向看守人道:“我已经同你们主人说好了,要在这里住十天半月,只好劳动你代为备办火食茶水。听说你是有家眷在这里的,大约不致十分麻烦。”说着就拿出一叠钞票道:“你拿去随便办理,几时用完了再向我要。”白萍看式欧给的钱很多,约近百元,暗想两人十天伙食,又何致用这些?式欧未免太大方了。看守人接钱出去,送进茶水。迟了须臾,又送上早饭。四样菜儿很是丰盛。白萍暗诧这饭做得也太快。怎才给了钱就有饭吃呢?式欧见他疑惑,忙解释道:“这一定是看守人自己的饭,先送来给我们吃。”白萍也未入心。及至把饭吃完,看守人来收家俱,式欧便和他说闲话,问主人可常到此来住?”看守人回答:“主人今年还没有来过。只是数日前有主人的亲眷王小姐,带着小婢前来,住在大楼中。据说主人或者要来静养几日,所以这几日很忙,正扫除大楼那边的房屋呢。”式欧道:“我只当园中没有别人。原来大楼里还住着女眷,以后出入倒要检点了。”看守人道:“没关系。大楼那边另外有门通着外面,出入不会遇见,他们女人胆小,这边草高树密,太清冷了,一向都不敢过来。”看守人说罢出去。式欧也陪着白萍到山中游散,直跑了半天。到夕照西料,方才回来。进门便用晚饭。饭后各据一榻,一面闲谈,一面看带来的书,很早的睡了。次日仍是如此。清净中度着时光。
到第三日午后,看守人忽然送进一封信来,交给式欧。式欧拆看以后,忙向白萍道:“这信是式莲来的,说家中发生了一点小事,得我回去亲手办理,现在只好赶着去一趟。若能搭着适合时候的汽车,今天或者能当日回来。如其不能,明天一早也要到的。对不起,你自己寂寞一半天吧。”白萍虽不愿他走,但也无法挽留,便道:“你有事请便吧。只希望早来,我一个人太冷清。”式欧点头笑道:“那是自然。不过我若今天不回,你最好到山上跑跑,叫身体劳乏,回来吃过饭就睡,不要胡思乱想。惹出花妖木怪来寻你,弄成像聊斋里所说的,某生者读书山寺,忽涉遐思,夜半有美女入户相就……那可就庥烦了。”白萍笑道:“果然如此,倒也不错。不过你念聊斋只念了一半,最末后的结尾,还有患瘵而卒一句呢。我只盼这句话实现。”式欧又笑说几句,便自走了。
白萍独居无聊,又不愿出去,闷得睡了回午觉。醒后见满屋金光闪烁照眼,原来是西沉的夕阳,穿过柳树枝叶,将光线筛入房中。白萍闭了闭眼,才下床趿着鞋,拿了两本书,到了楼下,将一把藤子睡椅,拉到楼外临水之处,高卧看书。这时树上蝉噪,草内虫鸣。鼻中闻着水气土香,和草木发出的清味。又加阵阵凉风,从水面吹过,真觉胸怀俱爽。心中自念,人生苦味,业已尝尽。以后只有两途可走,一是重入社会,做个冷酷无情的人,专心尽力地做一番事业。一是避开人境,逃入山林,去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就现在的情景看来,明白入世就有人事缠扰。若没摆脱能力,仍要作茧自缚。又哪如独善其身,萧然世外呢?倘然这别墅是我的产业,我就立志老死于此,永不出门了。白萍方在沉思,看守人送了饭来。白萍就令他掇张小几,放在面前,草草吃过。看守人收拾饭具,又送进一壶茶。
这时夕阳已将沉落,白萍望着眼前水滨生的芦草,高可隐人。却从那芦草尖端上,望见对面大楼的红色尖顶,被几株大叶杨树衬映着,颜色分明可爱。从大树的缝隙中,隐约可见一两面楼窗。那窗子是开着的,里面白衣飘拂,似乎有人在临窗外望。白萍猛想起前天看守人的话,暗想主人的亲戚女眷,携着一个小婢,住在园中。居然能忍受这寂静的环境,真也算胸襟不俗了。都市的女子,那一个不征逐繁华,怎肯这样淡泊自甘呢?就以我这样饱经忧患的男子而论,住在此中,本是最适合的境遇。但今天式欧走了,乍失伴侣,便有些清寂难堪,女子恐怕更不行了。但是那女眷还有个小婢作伴,也许能朝夕谈心,毫无所苦。接着又想起环境随心境变化,自己一人在此不胜冷寂。倘然在当初芷华未离之时,或是淑敏未死之日,能两人同栖在这里,恐怕就变成洞天福地了。白萍正在思想着,远近树上的鸣蝉噪晚,初听聒耳,久听就党若有节奏,像火车轮声似的,有了催眠的力量,白萍不自觉的竟然睡着。醒时张目,突见奇景。当头一弯凉月,挂在柳梢,好似入了另一个世界。白萍替瞢腾腾,自疑还在梦中。这时面前有个虾蟆,由岸草中跳入水内,噗咚一响,才把白萍神智唤醒,想起自己现在何处。低头看树影满身,好像一个个的银点儿,随风闪动。坐起摸摸茶壶,已然冰冷。知道自己这一觉睡得很长,料想不能再睡了。便饮了口凉茶,立起疏散一会,仍坐到那里看月。过了一会儿,自觉清寂无聊,重复立起,踱到小桥之上。立了片刻,见桥那边儿不远露着凉亭的尖,想过去看看。便过桥去穿花拂柳,向小亭而行。将走近了,忽见眼前横着一道密行的小洋松,顶端剪得甚齐,约有四尺多高,好似隔了一道短垣,无隙可入。白萍只得沿着这道松垣向北走,这时已能瞧见那座大楼的全部轮廓了。白萍猛想起这楼中住着女眷,不好走近,欲待退回。又转想此际楼中人定早睡了,自己又不向距楼太近的地方去,料无妨碍,便向前走。到了松垣尽处,转将过去,仍靠着松垣的里面走。快到那凉亭近前,眼前又是一排龙爪槐树,浓阴相接,好像一柄柄张开的伞,成行排列。白萍从树隙中挨身而过,立觉目中豁然开朗。原来这边另是一种景况,那座大楼周围,竟是城市中的式样。旁边是一方平坦之地,收拾成小花园,许多花畦,种着各式各样的花儿。那凉亭却和大楼一南一北,遥遥相对。白萍从凉亭边树中钻出来,先看见大楼的巍然巨影,其次瞧见被月色铺满的花畦,心中一半惊诧。这园中构造曲折,自己本不要近走大楼,但竟被曲折的树排,引到这别一洞天中来了。一半羡慕园主的匠心不凡,当日必然大费经营。这些思想在白萍脑中,不过几秒钟的颤动。他由树中挨身出来,只一扬头的当儿,猛听背后有人声嗷的叫起来,忽然惊极而号。
白萍也吓了一跳,急忙回头看时,只见凉亭的栏杆上,坐着一个穿灰色素衣的女子。长发披肩,却用手掩着脸儿。白萍才明白自己出现得太突兀了,这女子定是那看守人所说的主人戚眷,在此望月独坐,见我从树中钻出,怎会不大惊欲死?于是万分后悔,不该过来乱闯,便向前走了几步,鞠躬说道:“女士不要怕,我也是来借住的客人,就住在那边小楼上,无意中走了过来。想不到叫女士受惊,真是该死。请您不要怕,多原谅。”那女子原本坐在矮栏上,月光照着全身。白萍看得很清楚。她听着白萍说话,缓缓立起,但是手儿还没离开脸儿。月光也被凉亭的茅檐遮住,只瞧到她颈际以下,脸儿隐到阴影中了。及至白萍把话说完,满以为定能止住她的惊恐。不料那女子听完白萍的话,才把掩脸儿的手离开,忽又咦的一叫,手儿重掩到面上,身体摇动了几下,扑地又坐到栏上。但是身体重心已失,竟向后倒去,跌入凉亭中,脚儿还翘在栏上。
白萍也大惊起来,心想自己虽然使她受惊,但已用言语安慰了。怎她一看自己,倒更惊得跌倒?难道我今天面上有了什么怪状?或者真是花妖木怪附了体么?这时也顾不得仔细思索,就跳进栏内,蹲身将那女子扶起,坐在地上。那女子的手仍掩着脸儿,但身体却颤抖得十分利害。白萍忙和声道:“女士,我已经对您说明白了,您为什么还害怕。请您细看看,我实在是个人。若知道女士在这里,万不敢深夜过来。”那女子只不作声,半晌才用极细的声音说道:“你请走吧!”白萍听着这声音甚是耳熟,也没甚介意,就道:“我吓着了女士,怎能自去?我送你上楼去吧。”那女子摇了摇头,又低下去。她似乎要挥手叫白萍走,又不肯把手离开脸儿,便只见臂肘摇动,低声道:“请,请。”白萍以为她讨厌自己,就不敢再坚持送她回楼,只可缓缓立起道:“既然女士叫我走,我只可从命。一切请您多原谅。”说着就跨出栏外,由原来的树隙中钻出去。心中暗自纳闷,这女子好生奇怪,竟被自己吓成那样?而且紧紧掩着脸儿,不敢相看。自己说了许多抱歉的话,她并不答言,却只管挥之使去,未免太奇怪了。莫非有神经病吧?白萍心内寻思,脚下便停住了,立在树下正然怔着,忽听隔树那女子嘤然一呻,哀叫道:“白萍,白萍,你真走了。走了也好。我本怕见你啊!天呀!我为什么在这里遇见他……”白萍听得清清楚楚,大吃一惊。立刻悟到是芷华的声音。只觉精神震动欲狂,猛一回身,仍由树隙钻回凉亭之侧,向里一看,那女子仍坐在原处,却高张两手,向空就抱。借着月光反映,瞧出果是芷华。白萍叫了一声,直向前奔,却忘了前有栏杆,把脚绊住,立时全身倾侧,向前倒去。正跌到芷华身边,也顾不得疼痛,更不暇起立,伏在地上就叫道:“芷华!你呀,我可又遇见你了。你方才怎不叫我看见你的。”芷华这时张目如痴,但是手儿却不自主的抚到白萍头上,微喘着道:“你……你怎又……回来……跌着了么?”白萍已挣扎着坐起道:“不不不要紧。你怎也在这里?”芷华满面泪痕,低声道:“我是式连带来住的。”
白萍大悟道:“我也是式欧陪伴来的。哦,我明白了。这是弄的圈套,故意叫我们遇见。”说着仰首吁气道:“我该谢谢他们。”芷华却低语道:“我可怨恨他们。”白萍一怔道:“你难道不愿意见我么?”芷华摇头一叹,也没答言,就自立起,由栏杆的缺口走出亭外,白萍怔了一下,也立起随在她身后,低声道:“你为什么不愿见我?”芷华向前慢慢踱着,悄然答道:“相见只有难堪,岂不是多此一见?实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三五日里就永远离开这里了。又何必在这时多一次无谓的见面。”白萍这时脑筋略觉麻木,冲口说道:“你是要回沈阳去么?”芷华忽纵声笑道:“或者如此,你问的很好。”白萍猛然醒悟,知道芷华再不会与仲膺结合,而且仲膺业已远走高飞,不知所往了。便痴痴地在她身后跟着,却半晌无语。芷华忽缓缓立住回身说道:“你还是请走吧,我若是可以跟你见面,方才又何必那样遮掩。与其相对着大家难堪,不如快些离开。”白萍突然握住她的手道:“我不能走,并且更不能离开。”芷华道:“为什么?”白萍道:“因为我是你的丈夫。一芷华道:“怎你现在还说这话?我已经不是你的妻了。”白萍也反问道:“为什么?”芷华道:“因为我作了许许多多对不住你的事,并且曾跟边仲膺结了婚。”白萍摇首道:“我不承认你已和仲膺结婚,是出于你的本意。并且我也未曾和你离婚。”
芷华一怔道:“你这又是什么意思?难道要翻老账,举发我重婚的罪?”白萍道:“不不。我只要主张我应得的权力。”芷华大愕,半晌说不出话。白萍悲声道:“芷华,一切我全明白了。最初只由于我所见太偏,才弄出这许多波折。倘然第一次我能原谅你,你定能立时悔过,仍作我的贤妻。然而我总疑惑你偏爱仲膺,屡次不由衷的推让,以致害你颠沛流离,受尽精神痛苦。如今经过这次变故,我完全觉悟。知道你对我的爱情始终不改,并且仲膺也已远行不归。咱们的旧事就叫他永远过去。你应该恕过我以前的错处,重度咱们的新生活吧。”
芷华听了,泪珠莹莹地道:“你能这样原谅我,我是感激极了。无奈我的身体灵魂,完全污损,绝不配再作你的伴侣。白萍你听明白,我可不是不爱你,更不是惦着别人,只为我绝没脸儿跟你复合了。而且你是个男子,也不能这样不顾名誉的重收覆水。便是勉强重合,我这羞耻惭愧的心,一世也无法忘却。你越是待我好,我越是难过,这是为我打算。至于为你打算,收了我这不贞洁的妻子。以后怎能抬头见人?所以我劝你收起这个念头,再不要理会我吧。”白萍叹息道:“你不能这样说。我只为当初执着偏见,抛弃了你。离家出门,遇了很多意外的事。第一得到龙珍,第二遇到淑敏,种种行为,简直倒行逆施。所以落到这不幸的结果,把我的心已然灰到万分,再没有丝毫生趣。你若不能允许我,我真没有再活下去的必要了。还是方才的话,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你我全有不是,谁也不要记忆了。至于外人议论,根本无须理会。何况一班朋友,以前尚能对你原谅,对你同情,经过这次讼事以后,大家更敬佩了。只看这回咱们遇见,你是式莲陪来,我是式欧陪来。分明是他们预定的计划,叫咱们在这冷静地方见面。式欧是淑敏的哥哥,他妹妹由我而死,他居然能这样好事,可见他是十二分敬服。至于式莲祁玲等人,就更不必提了。再说我经过一番风波,业已灰心上进,只求精神上有所安慰。咱们大可以换个地方居住。谋个足以养身的职业。去度劫后的生活,享受老年伴侣的快乐,岂不很好?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芷华听了,沉思半晌道:“我作了不好的事,放荡够了。因为仲膺已去,无所倚赖,又回到你身边,这真是无耻妇人的行为。”白萍瞪目望着她道:“这是什么话?难道我还不知道你的心。”芷华苦笑道:“我不这样说,旁人也这样说啊。”白萍道:“旁人知道你的,绝不会这样说,你要知道这是咱们两人的事,何必管旁人?”芷华道:“就为咱俩着想,我也是不再跟你的好。何必把这不贞洁的身体再作你的累赘呢?”白萍听她言语中已不甚坚持,就道:“你自己的意思不能作准,我和你并没离婚丈夫有向妻子要求同居的权力。现在我十分需要你,你得允许我。”芷华道:“可是我已经又和仲膺结过婚了。”白萍道:“那个我不知道真假。便是真的,在法律上也不能生效。”芷华道:“再说我也没脸再跟你。”白萍道:“那是你自己疑心。作妻的回到丈夫怀里,什么叫没脸儿?我要强制你同居了。”芷华道:“你何苦这样逼我?固然你用正道来责备,我没法违抗。比如你立刻要我同居,我也只有服从。因为咱们法律上的关系并没断绝。你又不承认我和仲膺的婚姻,我若执定说曾嫁仲膺,此身已玷,那就不啻自己检举所犯的重婚罪。所以现在你是主动,我是被动。一切不能自主,不过你要明白,我已然是失贞的妇人了。比方你有件衣服,曾经落到粪坑里,沾满污秽,你重又拾起,把表面刷洗一回,仍旧不嫌弃的穿到身上,这时你对那污秽衣服的恩惠,可算到了一万分。但是你自己时时想起这衣服是曾经污秽的,能不心里作呕吗?倘然这衣服再穿到十年八年,恐怕你要害神经病吧?”
白萍摇头道:“你这比喻说得完全不恰当,我也作一个比喻。有一对燕子,同住一巢,十分相爱。但是公燕子长日出去打食,不能常常在巢,因而使母燕受到寂寞的痛苦。于是母燕偶然受了别的燕子引诱,发动海阔天空的性儿,出去高翔了些时。如今回到旧巢,听着公燕哀鸣,难道还不投到他的怀抱么?”芷华听着涔然下泪,忽把袖子掩了脸儿。又听白萍说道:“你应该想我们当初结婚后爱情的浓厚,家庭的快乐,和以后老年伴侣的趣味。”芷华挽着白萍的手臂,二人循着树排向大楼那边走,转瞬间没入大楼阴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