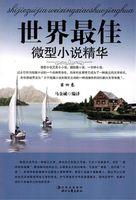先打听了开车钟点,当日的早车已开,只夜间十一点还有一趟。龙珍不敢耽搁,早走早得安心。便在白天算清店账,出了旅馆。在外面闲走,挨到黄昏。寻个馆子吃过饭,又到市场里遛了两点钟。天到十点半,她奔到车站。再一打听,真想不到火车恰于昨日改了钟点。东行的晚车,已在十点开了。龙珍很为恼悔,只可出了车站另寻一家旅馆住下。挨过一夜,次晨她七点多便起,出旅馆到车站等车。不想去得又晚了,最早的一班东行车,在七点已开。只得等九点的一班。她便买了张三等票,立在月台上等候。因为她没有经验,想不到车站上是官人侦察的要地,所以没有惊恐,很坦然的又溜上天桥闲踱。待到八点四十分,从北京来的东行车,还没影儿。但由关外开来的西行车,却将打点进站。龙珍询问路警,才知西行车得开到总站,和由北京来的车错车,东行车才能开过来,还得等二十分钟,龙珍只得耐心等着。须臾东边来的车已蜿蜒近站,停在第三月台。许多旅客潮水般拥上天桥,龙珍身倚桥栏。向他们闲望着,不大工夫旅客行将过尽。
忽见稀疏的人队中,有个长身玉立的少妇,身穿着件很朴素灰色呢子大衣,手提皮包,正低头弯腰的向桥上走。到桥上平坦处,猛一直腰,扬起脸儿。龙珍无意中看到她的面目,不由失声叫道:“咦。”这一字才叫出口,立刻悟到自己处在现在的境地,不应当被她看见,便想转身回避。不料那少妇闻声瞥见龙珍,也呀的叫出来,赶过她面前。龙珍知道躲不开,只得再转回脸儿,却心跳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颤声道:“芷华姐,你。……你这从哪儿来。”芷华看着龙珍叹道:“一言难尽。你在这里干什里?”龙珍张口结舌地道:“我没事。芷华道:“那么你随我走,咱们上旅馆谈谈。”龙珍因车票已买,急于脱祸,怎肯随她去,忙拿出车票道:“我是到车站送人,票子已替买了。还等那朋友来,现在不能陪你。你下车住在哪儿?少时我找你去。”芷华望着她把眼珠转了转,笑道:“妹妹你不必骗我。你绝不是送人,简直送你自己。”龙珍还强辩实是送人,并且赌咒发誓地说少时定去访她。芷华道:“你若真是送人,我可以在这里等着你。好在东行车十分钟便到,你送完了朋友,咱们再一同走。”龙珍知道芷华不肯放开自己。只得说道:“姐姐你真……咱们走吧。我也不送人了。”
芷华见她服从,便不再说话,挽着她的臂儿,一同走下天桥,出到站外。龙珍道:“咱们上哪里去呢?”芷华道:“你同我走吧。”说着就喊来一部野鸡汽车,坐了上去,吩咐开到明星饭店。车中两人都默默无言。到了地方下车,付了车资,便进饭店开了个房间。芷华照例把手续办了,等茶房出去,便闭上房门,向龙珍道:“妹妹咱们经年不见,想不到你竟会变成这样老练,作出惊人的事来。”龙珍如闻晴天霹雳,愕然问道:“你……你说我作了什么?”芷华冷笑道:“你还反问我么?这件事恐怕通国皆知了。难道我还没有点儿耳风?”说着就从行箧里取出一卷报纸,递给龙珍。龙珍接过一看,只见都是沈阳的报纸。上面把北京报上所登淑敏被害的种种消息,都转载过去,一段不剩。连白萍狱中对记者的自述,都首尾完全。看着不由万分惊恐,强定住心问道:“姐姐,给我这个看是什么意思?”芷华道:“我现在还没决定有什么意思。因为我在……现在把我的事先告诉你吧。你既曾住在淑敏家里,总该知道我的事。我本来已经到公司去看护白萍的病了。但是那位祁玲女士,对我说了许多道理,劝我离开白萍,随仲膺走。她的话都不足打动我的心,只有一句,说白萍和淑敏已然到了热恋的程度。我使想自己是失了贞操的妇人,不该和人家纯洁的少女争爱。而且白萍事业正在发展,也应该有个淑敏那样的贤妻作内助于是我就甘心退让,随仲膺走了。我又因为伸膺年来受我的影响,把有用之身将要变成颓废,所以鼓励他作一番事业。仲膺应许我的请求,想起他有位旧同学在沈阳作督署的军医处长,就带我投奔了去。到沈阳居然很劳那旧同学关照,在军医界得了个很好的位置,安心伴着他直到现在。前天看报,见淑敏被害死了。已然吃惊,接着又见报纸上几日连续登载,才晓得是你办的事。而且是你要害白萍,误杀淑敏。我真作梦想不到你会作出这样事来。又寻思不出是什么原因,又急又闷。直到前天,我瞧白萍的自述。知道他的性命是极危险,久困狱中,已足致命。何况出了狱他还许自杀。我感觉自己也是局中人,对这件事应该有所补救,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恰巧前天仲膺要用一件应用东西,我想起天津宅里有,便藉词回关里来。好在仲膺每日工作极忙,平常就不大看报。我在这几日又把报纸隐藏着,不叫他看见。所以他对北京发生的事,毫无所知,还只当我是特为替他取东西来呢。我所以在天津下车,就为把那件东西先给他寄去。然后奔北京探望白萍,并且想个善后的法子。现在我的事说完了。你可以把你的近况告诉我了。”
龙珍道:“姐姐你既然看见报纸,想必把我的近况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报上所登只是我的行为,却不能表出我的苦衷。姐姐,你该明白,咱们都是同病相怜的人。你呢,前事不提。只说最近,本已和白萍团聚了,却为祁玲几句话,又害你们生生离散。我呢,当初和白萍也有过一度关系,但是以后我自知不配作他的伴侣,久已甘心退让。哪知这次到了淑敏家里,淑敏倒是很好的人,并没有丝毫令人难堪之处。只有祁玲在中间竭力作弄,她好似把白萍当作淑敏的禁脔,代为防卫得十分严密。这还不算,她还怕我万一对淑敏有碍,居然异想天开的,用尽千方百计逼我嫁给我的姐夫。外面是继承我姐姐的位置,但是我姐姐仍然存在。实际是姐妹同事一个丈夫,这简直把我挖苦透了。我当时气得几乎发昏。及至明白了祁玲的意思,便横了心肠,要和她争斗。就先允许嫁给畏先,随后才决计走那两败俱伤的道儿。拚着害死白萍,我再一死相从地下。叫淑敏落空,还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想要祁玲将来明白我的铤而走险,完全出于她的逼迫。淑敏的终身痛苦,也完全是她的赐与。直到死也要受良心责备。”芷华听到这里,便插口道:“你只为和祁玲负气,就要谋害白萍,这也未免太过了吧。”龙珍道:“是啊!我自己也明白这事作得太残忍,太无情,太不像人类。可是当时在气头儿上,简直没法抑制。可是我事先也曾和命运赌博了一下。在我和畏先结婚的第三日,白萍在淑敏家吃饭,我和畏先闯进去,对白萍报告了我嫁畏先的事实。这样本已进于玩笑。倘然祁玲看出可疑,就应该防备我了。然而她正在志得意满,以为我这一举更足使淑敏地位稳固,并没介意。我当夜又将祁玲请出,给她一封信。假说不能忘情白萍,这次嫁畏先是别有难言之隐。求祁玲保存着我这封信。等到淑敏死后,或是白萍将死之时,再行发表。祁玲接过那信,允许照我的话办。其实我信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信封上虽是写着要白萍亲展,但信内却是直接写给祁玲。说明我负气的原因,和预备害白萍的计划。这就是对天卜卦,倘然祁玲不守信用,偷着开封看,我的阴谋就算一败涂地。倘或她守信用不看,那就算白萍命该如此。但是祁玲在这件事上,倒对得起我。只看我投入公司作事,她并没阻拦,就知道她没偷瞧信里的内容。及至我把一切手续都弄好了,她也毫无知觉。不过这里有两件阴错阳差的事情。一件是我原意要害白萍,却想不到害了淑敏。第二件我下毒原注重茶壶,不料倒是暖瓶收了功。而且看报上的记载,好像他们还不曾知道茶壶中也有毒物,倘有人用那壶喝水,可就糟了。现在我的情形都已说完。姐姐方才在车站那样严厉的拦阻我,又把我带到这里来盘问,定有你的意思。是想把我怎样呢?”芷华道:“现在我是局外人,莫说你害死了淑敏,便是杀了白萍,我也没有处治你的理由。”龙珍道:“是啊,姐姐本来和我处在同病相怜的境地。”芷华接口道:“话不是这样说,你莫当我赞成你的行为。妹妹,论起你的心,可真太狠了。白萍虽然因为种种岔头,没有和你同居长久。但是自始至终,他却很少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又何认为和他人负气的原故,毁害他的生命?倘真把他害死,你便是得以安然无事,良心上能自安么?如今阴错阳差,算是淑敏替白萍死了。然而淑敏并不是你的情敌,因为她并没从你手里把白萍夺过。倒是她先和白萍有了相当友谊,你才投到她家里去的。淑敏的为人,我很知道,待朋友极热肠,你竟忍心把个忠厚的东道主人害死了。”
龙珍听着愧恨非常,半晌才道:“这事我也知道作得太狠了。但是姐姐你是没瞧见祁玲拨弄我的情形,多么可恨。”芷华道:“那你就该直接对付祁玲啊。”龙珍强辩道:“我想淑敏或者与祁玲同谋,叫祁玲出面拨弄我。”芷华道:“这你可是昧心的话。淑敏那人和我是一样性情,宁可牺牲自己幸福,也不会用阴谋争夺爱人。妹妹,这件事据我的揣测,大约你口里虽说不爱白萍,但心中总不能忘情于他。又加祁玲作事过于操切,叫你受的刺激太深,所以作出这倒行逆施的事来。再说一句不怕你生气的话,你总以为别的女子像貌美丽,很容易得到爱情和幸福,你却只有白萍这一条希望,眼见他被淑敏得去,在自己绝望中,不觉竟生出毁害他人的念头。这是心理上的变态。我很能原谅你,但在法律上就难说了。”龙珍被她这几句话刺入心坎,不由呜呜地哭起来。芷华又道:“你想想吧,这件事办得多么拖泥带水。淑敏是枉死了,白萍景韩祁玲畏先都禁在狱里,嫌疑很难洗刷。这到什么日子是个了结?”龙珍怔了半晌道:“不瞒你说,我方才在车站,实在要乘车东去,到关外躲避。若不遇见你,我现在己走出百十里路了。当初我本因为绝望,才作出此事,已把死生付诸度外。但到作出来之后,我又胆怯了,才起意逃跑。如今听了姐姐的话,我又觉悟了。像我这样的人,无论走到哪里。活到多久,也要在痛苦中挣扎,再莫想得到人生乐趣。还不如及早自首,替淑敏抵命。既安了自己的良心,也免得多少人受累。”芷华听了,暗惬心意。她原想劝导龙珍令其自首,好救出白萍,徐图善后,便道:“妹妹,你真要这样作么?”龙珍道:“回头咱们吃过午饭,就趁午后四点的火车回北京去。姐姐你在后面跟着,看我进了公安局再走。
芷华听她说出这话,便不再向下逼迫,只淡淡地道:“这件事本不是我该参预的。但只有一句话,是行吾心之所安。你以为该作的便作,不该作的便不必作。我何必跟你上北京,瞧着进公安局呢?”龙珍点头不语。芷华痴思半晌,才道:“妹妹,在这儿等我,我出去一趟,取东西给仲膺寄去,省得他等得着急。今明日咱们再上北京。”龙珍应着。芷华立起穿了衣服,本想要叮嘱她不要自己偷走,但话到口边,便又咽住,转身出去。
龙珍这时倒拚出去了。想到活着也没生趣,还不如自首抵命。了此残局。当下心里倒安静了。芷华走后便倒在床上歇息,过一会竟自睡着。午后四点,芷华才回来。手里带回个纸包儿,放在桌上。脱了外衣。回头见龙珍在床上酣睡,不由望着她暗自叹息。便按铃唤茶房泡茶,又买了筒纸烟,便坐在沙发上吸烟饮水,悄然静思。暗想龙珍也真可怜,生了一付丑貌,又自小便在不良环境中度日。不想遇见白萍,只几日的相处,竟变成个通达明理的人,但是一面也造成冤孽。如今事势已经变幻,她受尽颠连磨折,结果逼成奇祸。推原溯委,也着实不能怪她。无奈到了这般境地,白萍等困在狱中,若非由她作解铃人,怎能了结?想着忽然脑中一动,影影绰绰的忆起一事,好似自己在公司中看护白萍的时候,白萍对自己说过,曾在北京旅店遇见龙珍。龙珍假说她业已嫁人,又说她曾见自己凄恋白萍的情形,所以白萍感动。即日回津去看自己,结果虽因遇见仲膺,突生波折。但是龙珍对自己的心,总算仁至义尽。看那时候,龙珍一点争夺嫉妒的意思也没有。现在却因何把人变了,作出这凶事呢?大约祁玲给她的刺激太深的话,是不错的。只是她当日对我既有那样好心,如今她作了祸事,本想潜逃。自己却拦住叫她投入死路,这未免太负心了。再说这种孽事,完全是自己造因。当日若非自己意志不坚,弄成三角恋爱的局面,白萍何致离家?又何致遇见龙珍、遇见淑敏,落出这般惨恶结果?事到如今,自己既算与仲膺同组家庭,却又不能忘情于白萍的患难,千里迢迢地前来。现在算是事情恰巧,遇见龙珍,把她留住,有了救白萍的把握。但是白萍出狱以后,一定心碎神伤,未必不自投绝路。那时若不管他,就是救他等于枉费。若是救他,除了我还能给以精神安慰,挽救他的残生。但是我已经正式作了边仲膺夫人,难道还能寡廉鲜耻的再反覆一次么?”想着发怔许久,又望着龙珍半天。立起来回踱着,忽然切齿道:“我自己造的罪孽,还是自己承受了吧。以后无论怎样办法,我的良心也不易安了。不如趁这个好机会寻归宿吧。”说着又连连点头,说了好几次就是这个主意。当时就唤茶房去买浆糊和包皮纸,将那带来的纸包封裹严紧,才叫醒龙珍。
龙珍下床道:“姐姐回来了,怎这么晚?”芷华道:“别提了。我取了这件东西,本待立时寄到沈阳,哪知到了邮局,竟说不能寄了。交涉半天,还是不成。仲膺那边要得又紧,真是叫人着急。我在这里还有许多事要办,哪能回去。”龙珍看了看桌上的包裹道:“这包裹也许太重了。”芷华含糊应道:“是的,这可把我急煞了。说句实话,我千里迢迢,只为来见白萍一面,还要给他善后。绝不能匆匆东返。这临时又没人可托……”龙珍接口道“可惜在这时候,我急于回北京自首投案。否则倒可以替你送一趟。”芷华想了想道:“妹妹,我有个无理的请求和你商量,因为我太急于见白萍,真不愿回去,而且回去了便没有理由再出来。只可求你替我走一趟,到沈阳把这东西交给仲膺。好在来往只须三四天。我先到北京把情形告诉白萍,叫他安心等侯。妹妹你肯替我辛苦一回么?”龙珍道:“我去一趟倒没什么,不过要害白萍他们多受苦几日。再说还怕姐姐不放心。”芷华道:“这你倒是多想。我为什么不放心?你要走在我方出门时早就走了,何况你便是一去不来,与我又有什么关系?”龙珍一笑道:“好吧,那么就请你写封信。我带着去。”芷华道:“信倒不必写。因为我没有不回去的理由。最好你到沈阳,见了仲膺就说咱们在天津相遇,恰值你要到沈阳,所以托你把东西带去。他若问别的,你就全推不知道”说着把仲膺的详细住址告诉了。龙珍道:“那么我今天晚车便走,还可以用这一次买的车票,早去早回。”芷华道:“这样更好。”又谈了一会,吃过晚饭,龙珍便自己上车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