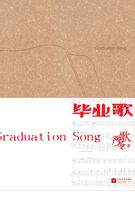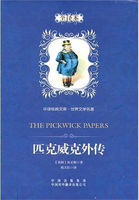圣旨原文是:“左宗棠奏逆酋帕夏自毙情形,并统筹全局各一折。据称:安集延逆酋帕夏经官军击败后,众心离散,遂于四月间仰药自尽,其子海古拉率党西窜,亦被缠回截杀。等语。该逆逼胁回众,占据南路各城,肆其荼毒,罪恶贯盈。
今既穷蹙自毙,余众势必涣散,事机极为顺利……喀什噶尔为叛弁何姓所踞,自应乘此声威,速等殄灭。左宗棠拟俟新秋采运足供,鼓行而西。刻下已届秋令,着即檄饬各军,克日进兵,节节扫荡。各城回众,素受逆酋胁制,非尽甘心从逆。此时大军西行,咸知效顺,自当分别良莠,剿抚兼施,以安众心……左宗棠所陈统筹新疆全局,自为一劳永逸之计。南路地多饶沃,将来全境肃清,经理得宜,军食自可就地取资。惟目前军饷支绌,近虽借用洋款五百万两,亦是万不得已之举,可一而不可再。若南路一日不平,则旷日持久,饷匮兵饥,亦殊可虑。该大臣所称地不可弃,兵不可停,非速复腴疆,无从着手等语,不为无见。着即督饬将士,戮力同心,克期进剿;并揆时度势,将如何省费节劳,为新疆计久远之处,与拟改行省郡县,一并通盘筹画,妥议具奏。所请敕部将咸丰初年陕、甘、新疆报销卷册各全分及新疆额征、俸薪、饷需、兵制各卷宗,由驿发交等语,着户部、兵部查照办理。”圣旨中所谓何姓者,指的是原清军将领后投靠阿古柏的何步云。
接旨的当日傍晚,左宗棠即着文案将圣旨分抄多份,由驿路送达关外各统兵大员阅看,又单给刘锦棠写信一封,会商大军推进师期。
转日,署乌鲁木齐都统英翰由京师风尘仆仆地赶到肃州来向左宗棠禀到,商量出关赴任等事。
左宗棠于是又提起精神,与英翰周旋了两天,直到英翰出关才得歇息。
望着英翰的背影,左宗棠悄悄叹息了一声,不由暗道:“乌鲁木齐新复,边务正当繁重,朝廷却打发来这么一个大烟鬼出任都统,也真做得出来!”
左宗棠发此感慨不是没有缘由的。
英翰是满洲正红旗人,萨尔图氏,字西林,一榜出身。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拣安徽以知县用,累官宿州知州、颖州知府、安徽按察使、布政使,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升授安徽巡抚。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配合李鸿章“剿捻”,因功授两广总督。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入觐,晋二等轻骑都尉世职。总督两广期间,因吸食鸦片成瘾,加之随员招摇,为广州将军长善所劾,被褫职召还京师。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初,赏还世职,又赏二品顶戴命署乌鲁木齐都统。
英翰先以体弱多病累疏辞缺,看看实在延捱不过,这才不得不行。
英翰这一年尚不到知天命的年龄,但因吸食鸦片过深,却早已经面黄肌瘦,弱不禁风,提早进入了老年。
朝廷打发这样一个人去做乌鲁木齐都统,乌鲁木齐以后的前景,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英翰抵达乌鲁木齐后,很快便与成瑞办了一下交割,他便全身心地躺进卧房里,狠狠过起瘾来;所有公事,全交给随员料理,任由一班人胡作非为,他也无力过问。
乌鲁木齐刚刚稳定的局势,眼见有些波动。
这一天,因身边的一名随员,看好了当地一户维族百姓家的闺女,便带着几名军兵把人抢了来,惹恼了当地百姓。
众百姓见官军胡作非为,马上便会同闺女被抢走的那家人的父母兄弟,飞跑到都统衙门来鸣鼓喊冤。
那鼓被敲得震天响,赛似后膛开花大炮的声音。
英翰当时正卧在榻上让人伺候着吞云吐雾,冷不丁鼓声传来,登时便把他的烟枪吓掉,认定是驻扎在伊犁的俄国人打过来了,就使出全身的力气往起挣。
挣了三挣,不仅没有挣起身来,反倒把他的魂魄挣出了窍。
伺候在侧的人眼见他瞪大了双眼,还把手指向门外,接着就长出一口大气,整个身子便软将下来。
家人弯腰把掉在地上的烟枪捡起来递到他手里,他却不接;叫他,他又不应;推他,他全身都动。
家人忙用手去摸他的鼻息,这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人世享清福去了。
闻报,伊犁将军金顺打马飞奔到这里,自然是先将抢来的人放掉,然后又给左宗棠发信,给朝廷拜折,最后才为英翰料理后事。
得知英翰死在任所,左宗棠连日给朝廷拜发《请以金运昌接署乌鲁木齐提督行都统事》一折。上准。
同年(公元1877年)七月十七日,新疆南路秋高气爽,瓜果遍地,正是这里最迷人的季节。
就在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照伯克·胡里所请,向南疆中俄边境大肆派兵的时候,在吐鲁番、托克逊一带驻扎的老湘军、嵩武军各营,也开始起寨拔营,向南路继续推进。
此次向前推进,清军共投入马步四十八营兵力,计有刘锦棠统率的老湘军马步三十二营为前锋先行,张曜统率的嵩武军马步十六营为后队跟进;张曜跟进的同时,并为前路兼筹粮运和办理善后。
此次对敌作战,主要由刘锦棠一路担任。
为防后路空虚,更为了防范敌军掐断粮道,在大军推进的同时,徐占彪统率的蜀军马步六营在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地驻守。
为稳妥起见,刘锦棠先派四营分两路先行,到曲惠安营。
先行的四营每路两营,一路走苏巴什、桑树园子、库米什、榆树沟、乌什塔拉大道,一路则由伊拉湖小道前进。
刘锦棠命令两路人马沿途搬运柴草,挖掘坎儿井,节节预备,以备大队继进顺利。
越两日,刘锦棠见前路顺畅,决定大队拔营跟进。
他传命步兵各营走大道,自统骑队各营走小道,两路人马在曲惠会合。
刘锦棠抵达曲惠的当日,便有百余骑安集延打扮的敌兵前来窥探消息,后见官军马、步各营陆续到达,即掉转马头向来路狂奔。
官军骑兵追赶不及。
刘锦棠见官军动向已被敌方侦知,便决定不在曲惠耽搁,转日即命提督余虎恩、黄万鹏二将,率马步十四营取道乌什塔拉,顺博斯腾湖南岸,悄悄疾驰库尔勒侧背,此乃奇兵;为吸引敌军的注意力,刘锦棠亲提主力,大张旗鼓地由大路向开都河推进。
当时正逢汛期,加之是年南疆雨水偏多,使开都河水猛涨。
海古尔?胡里眼见洪水滔天,顿时心生一计,竟然派出数百将士决堤放水,几天光景便导致两岸一片汪洋,深处可达三米开外,浅亦没及马背,阔涉百余里。
开都河源自天山之麓,汇而南趋,贯库尔勒、喀喇沙尔之中,下流注于博斯腾淖尔。古所谓泑泽者,即指此也。
刘锦棠师至,遣人在多处探路,均不得通过,只好传命各营舍弃淖路,全军绕行近七十余里,方见到一块一眼望不到头的碱地,将士已是疲惫不堪。
刘锦棠见天色已晚,不便夜行,只好传令各营就高地扎营,埋锅造饭,休息一夜再行。
刘锦棠的行止很快被细作报与海古尔?胡里。
海古尔?胡里闻报之下,不由仰天大笑道:“刘锦棠小魔鬼,你连开都河都过不去,还想过神溪吗?”
海古尔?胡里口里所说的神溪,就在碱地前行四十余里处,隐蔽在碱地的中央部分,把碱地一分为二。该溪清澈见底,水寒透骨,深达丈许,让人望而生畏。
当地人俱把此溪称之为神溪。
神溪者,顾名思义,非神仙不能通过也。
第二天,大军行到溪边,自然无法通过,探马只好急报刘锦棠。
刘锦棠闻报大惊,急忙策马来到溪边,但见该溪宽约三十余米,深不可测,用手试水,感觉冰凉透骨,全身充满寒意。
说是小溪,莫如说就是一条隐藏在碱地的河流。
刘锦棠苦思不得良策,只能挑选军中会浮水的军兵二十名,每人喝了碗辣子汤,然后拉着早就备下的绳索游过对岸,用绳索搭建浮桥。
直到午后,浮桥总算搭建成功,全军于是陆续通过,整整过了两个时辰。
稍事休整,刘锦棠传令全军奋勇前进。又走了约一百余里,于傍晚时分方到达开都河的东岸,刘锦棠传命各营就地扎营,派马步五营快速搭建浮桥,令马步四营奔至开都河上流,用石沙堵塞河道降低河面水位,大队人马则开始抢修道路,修堵河堤,以保证粮运通畅。
一日后,大军直逼喀喇沙尔,但却未遇一兵一卒抵抗,分明是一座空城。
刘锦棠带亲兵五营进城巡视,但见地面积水盈尺,官署民舍均被大水淹塌,荡然无存。全城上下不仅无人,连牛羊等物也不见一个。
不用问,这显然是当伯克.胡里、海古尔?胡里得知官军已经通过神溪后,便赶在官军到达开都河之前,将城中百姓、牛羊等物悉数掠走,使官军在此地闻不到半丝的人烟。
此时的喀喇沙尔不仅仅是一座空城,分明是一座死城。
刘锦棠传命各营快速向库尔勒进发。
刘锦棠督军行至中途,便与余虎恩、黄万鹏两部人马相会合。两军合为一军,疾奔库尔勒,力图抢在守敌逃跑前赶到。
库尔勒倒不见积水遮地,但同样是一座死城;不仅不见一人,亦不见牛羊等物,全城活着的是遍地乱窜的老鼠和在空中盘旋的百鸟。
全军经一路狂奔疾行,上下早已饥肠辘辘,全盼着到库尔勒后便埋锅造饭,孰料库尔勒并无敌人,而全军所带粮食,却只有不足百斤。
依刘锦棠最初本意,只要各路人马能在喀喇沙尔或库尔勒与敌军遭遇,就算全军不随带粮食,军食亦能在战斗中解决。
刘锦棠甚至认为,粮食、牛羊、战马,随便哪一项,都能让全体将士饱餐上一顿,不至于断炊。
但匪酋的决堤放水,开都河意料之外的汹涌泛滥,打乱了刘锦棠脑海中的那套固有的战争模式,使他不仅仅失措惊慌,而且是实实在在地惊出一身冷汗!
他一面派出快马传令后路迅速转运接济,一面就紧急把道员罗长佑、提督余虎恩、黄万鹏、汤仁和、张春发以及总兵董福祥、张俊等人召集到一起,开始商量对策。
董福祥这时说道:“刘大人,我们民间有句老话,有老鼠的地方就有粮食,有鸟鸣的地方必有果实。大人不妨传个令下去,让各营分散开来,来个跟鼠要粮。据卑职所知,喀喇沙尔与库尔勒都是南疆的大城,每地居民住户都以万计。何况,我们回民又素有掘地窑粮的习惯,怕的就是抢掠和兵荒。”
余虎恩这时也道:“大人,想起卑职从前跟着老统领在陕甘一带南征北讨时,每逢缺粮,老统领都打发人到大地里去掘地找食,每每都有收获。正像适才董总镇所说,回民因连年经历战乱,都不敢把收来的粮食全存在明显处,怕遭抢后日子过不下去。现在,匪酋虽把百姓、牛羊全部裹走,但难保把百姓埋藏的粮食都能全部起走。何况,百姓也并非真心与官军为难,实在是惧怕匪酋手里的枪械,不得不跟着走。卑职如此说,也并非就能保证我们当真能掘到粮食,大人还要做第二手准备,是否要派出一营骑队去后路接应一下粮车,以确保万一。”
刘锦棠皱起眉头想了想,只好按董福祥与余虎恩二将的话办理,内心却对追敌过急大是懊悔。
就在老湘军上下开始在库尔勒城内外四处探寻鼠踪找粮的时候,在肃州的左宗棠,此时却正在行辕里跪接一道加急送到的圣旨。
旨曰:“郭嵩焘奏英人照会调处喀什噶尔事宜,并传闻阿古柏病毙各折片。
据称:英国首相德尔比屡遣威妥玛为喀什噶尔调处,照会章程三条,意在护持安集延;又闻喀什噶尔阿古柏病殁于古拉尔地方等语。该侍郎所奏各节,于新疆南路军务得手情形自尚未悉。着左宗棠将郭嵩焘所奏体察情形,斟酌核办。原折、片、单着抄给阅看。”
左宗棠接旨毕,又把随旨下发的郭嵩焘上给朝廷的奏折、附片、单等全部阅看一遍,便传起稿师爷进来,口述《复陈办理回疆事宜》一折。
折子这样写道:“……上年官军克复北路数城,英人乃为居间请许其降,而于缴回各城、缚献叛逆紧要节目一字不及,经总理衙门向其辩斥乃止。兹德尔比、威妥玛复以此絮聒于郭嵩焘,彼意以护持安集延为词,以保护立国为义,其隐情则恐安集延之为俄人所有。臣维安集延系我喀什噶尔境外部落,英、俄均我邻国。英人护安集延以拒俄,我不必预闻也。英人欲护安集延,而驻兵于安集延境,我亦可不预闻。至保护立国,虽是西洋通法,然安集延非无立足之处,何待英人别为立国?
即欲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兹虽奉中国以建置小国之权,实则侵占中国为蚕食之计。”
左宗棠接着气愤地说道:“英人以保护安集延为词,图占我边方各城,直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从前恃其船炮横行海上,犹谓只索埠头,不取土地,今则并索及疆土矣!彼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向我商议,欲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
该折又写道:“帕夏于库尔勒地方服毒自毙,英国既有所闻,赛德尔意仍照郭嵩焘前议办理,德尔比意欲饬署理公使傅磊斯赴总理衙门会议,茀赛斯亦拟来京调处。此皆无关紧要。彼向总理衙门陈说,总理衙门不患无词;彼来臣营陈说,臣亦有以折之。”
左宗棠最后写道:“臣前闻英人有遣淑姓赴安集延之说,已驰告刘锦棠、张曜,嘱其善为看待。如论及回疆事,则以我奉令讨侵占疆宇之贼,以复我旧土为事,别事不敢干预,如欲议论别事,请赴肃州大营。臣于此次奉到谕旨,当加饬其体察情形,妥为办理,务期预为审酌,以顾大局。”
左宗棠洞悉其奸,一语道破英国人极力斡旋的玄机:“保护安集延”只是英国人的一种托词,实际是为了“图占我边方各城”,为了“欲于回疆撤一屏障”,达到“为印度增一屏障”的目的。
众所周知,印度当时是英国的属国。英国为印度“增一屏障”,说穿了,就是为自己“增一屏障”。英国的另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想抢在别国之前,开辟出一条从西北陆路直接进入大清国内地的通道。
左宗棠的折子不言自明:英国人的阴谋如果得逞,他就能从海、陆两地对大清国实行战略包围,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左宗棠将折子拜发的同时,又着文案将折子底稿誊抄两份交驿站发给刘锦棠、张曜阅看。
(第三节)
俄国人旧话重提
英国的斡旋以失败告终,俄国则耐心地等待着机会。
库车一战,从根本上动摇了伪汗国的军心,南疆全境收复指日可待了。
俄国不敢怠慢,俄驻华公使馆快速把一个原本就很荒谬的抗议书重新摆到了总理衙门的面前。
左宗棠在肃州钦差行辕鸣炮拜折的时候,老湘军马步各营仍在库尔勒城内外掘地寻粮。
董福祥、余虎恩二将所料不错,老湘各营在库尔勒城内掘出地窖藏粮五万斤,在城外正北方十里左右,经循鼠迹掘地,亦得粮二十余万斤。保证了全军上下三天的军食。
刘锦棠闻报大喜,传命将粮食集中到一起,便开始抓紧让军兵造饭。
饭毕,尽管后路粮车仍未到来,刘锦棠却不想再等下去了,决定连夜兵发库车,趁敌军立足未稳之际,出其不意对其攻击。
刘锦棠已经意识到,只要各城百姓不被掠走,官军无论粮车能否跟上,都可就地购粮应急;若百姓尽失,官军无粮可采,便只能靠随军粮车解决饭食。这样一来,不仅被动,也实在冒险。
至于循鼠迹掘地寻粮,实在是因为库尔勒当地百姓确在地窑藏有粮食,若无粮可藏,百姓手里的存粮尽被敌军掠走,又当如何呢?
刘锦棠以为,侥幸之事一次出现亦能二次重演,但很难保证次次胜算,决不能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