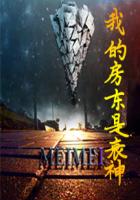父亲
父亲老了。
哥哥在信中说,父亲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他常坐在家门口我小时候亲手栽种的那棵石榴树下默默地抽着旱烟,或是从陈旧的箱子里找出这几年我给家里写的信,小心摊开,一遍一遍地看。见父亲呆久了,家里人劝他进屋去,父亲固执地不同,烟叶更是卷得快抽的凶,咳嗽也更厉害了。
我不禁落下泪来。
父亲,你不止一次叮嘱我,让我踏实做人,做学问。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您所期望的作家,只是我还没有完全辜负您。您的儿子要出书了,大学期间最后一个寒假他选择留在学校,呆在报社办公室里写他的大学和父母,校订他的书稿。这些年来,他忙于奔波求学,常年漂泊在外,除了每月写一封信,他再没能为家里做点什么。这些年来,他已将尊敬的父亲当成了知心的朋友,彼此倾诉一些如意或者不如意的事情。
人们都说母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父爱则是蒸馏水,我却不这样认为。其实,父爱是可以触摸的,如果说母爱是港口,那么父爱就是大海,而大海的呼吸是要通过巨浪和狂风用心去感受的。
我们每个月写一封信给对方,这个习惯从我念高中就养成了。您代表您和沉默劳作的母亲给儿子讲家里的事情,譬如小麦的长势,稻子的收成,还有您养的那几只兔子。您的信写在小堂妹的练习本上,黄黄的,皱皱的,有不少错别字。我却总能从哪些歪歪斜斜的字迹中读到城市里难以寻觅的温暖,读到故乡一年中渐渐变换的季节。您的问候总是伴着村里的月色和炊烟如期而至。信总是平静地叙述、殷切的希望,以及深深的自责,丝毫不提您借钱的艰难和辛酸。您说“现在的病情还可以”“妈妈好,只是太苦太累了,爷爷好,只是越来越孤独了,哥哥姐姐好,至少挣不了多少钱,晴晴好,会说话了会走路了……”。我用正楷字给您写信,详细汇报学习、生活和工作近况。我告诉您,我很忙但是很充实,我很穷但是很快乐。我说“请您和妈放心”,我会好自为之保重自己的,我不会贪污报社的公款,不会违法乱纪给学校添乱,不会眼高手低不向先生请教,我不会忘记应该记住的一切,我会努力做一个坚强勇敢真诚的男子汉。
父亲,因为你是伟大而坚韧的,母亲会将您看成大树,儿女会将您当作天空。父亲是一部书,但生活的重担和严酷的现实常常掩饰了父亲的情感,让父爱藏在深处,变得高远,年轻的儿女常常读不懂父亲这部书。父亲呵,我也一样。我读了17年书,却始终未能将您这部永远读不尽的书读透。
父亲只上了四年学。本来父亲是乐于读书的,后因祖母早逝,为了照顾年幼的弟妹,作为长子的父亲只好辍学了。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书读少了,父亲经常对我们说,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父亲希望能在他两个儿子身上实现读书的梦想。比我大四岁的哥哥极聪明,却不愿被拘束在学校里,而爱鼓捣一些小玩意,因此挨了父亲不少斥责。终于有一天,哥哥逃离了学校。老师追到家中,他竟不顾一切从后窗跳了出去,一连几天不见踪影,父亲只好作罢,叹着气说:“平娃子是真读不进书了,老师们都说管不住,要他站着,他偏坐着,要他跪着,他干脆躺着了。”
小时候,父亲喜欢用一只手托着小小的我走来走去。我站在父亲的手掌上,望着他呵呵地笑。据说,这样的孩子长大会有出息的。不到一岁就被送进一年级课堂,父亲看我果真读书专心,老师们也道悟性高,认为我颇有天赋,便下定决心让我读出一个模样来。
父亲在我九岁那年就发现了我的作文写得不错。在他看来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还记得,我的第一篇作文《放羊》给父亲看后,父亲竟然破例允许我和哥哥看了一晚电视,那时村里穷,方圆数里就族兄家里有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乡亲们茶余饭后讨论了好几年,而平时父亲是不让我们去添麻烦的。父亲仔细修改了我的作文,他甚至到羊群里数了数,将我写的十七只白羊改成了十八只白羊。次日,老师当着全班三十几位同学的面念了我的作文。“好儿子,你会成为作家的。”父亲笑眯眯地抱起我抚摸着我的头说。
父亲,我真的能成为作家吗?
我考上了大学,父亲送我,一路近千里,父亲从未睡过一个好觉。住旅社时,他安顿好后,便自己出去,回来踢了几个苹果给我吃。要他同吃,他舔了舔嘴唇说“吃过了”。然后默默地掏出他的烟袋。旅途的极度困顿让我很快入睡。被客车的隆隆声惊醒,却见父亲端坐于床位上,黑暗中有一点暗暗的火光抽的忽闪忽闪。父亲怕误了点,又担心数千元学费。
送父亲上车前,我们静静地在街上走。父亲的胶鞋和旧灰裤在街市上很惹眼,他却很自豪地走着—上了大学的儿子正穿着崭新的皮鞋和笔挺的衣裤,伴在他的身旁。走到舞阳坝,在一个摊位前,父亲拿起一根皮带。“买一根吧,爸。”我说。父亲红着脸,似乎做错了什么事。我赶忙讲好了价,付了钱。“您那根旧皮带可以扔了。”我记得父亲经常坐在油灯下缝补着那条伴了几十年的断皮带。父亲慌忙道:“不能扔,留着有时候到坡里去,还可以系。”上车的时候,父亲怕我不放心,回过头来倚在车窗上,晃晃手中的饮料瓶,说:“在这呢。”我知道那里面装的是隔夜的凉开水。
这样想着几年前的事,我的心里又酸酸的。父亲,儿子说过的话是算数的。他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好好生活,他没有也不会让您失望,现在,大学生活要结束了,他想跟您说说心里话,可是,从哪里开始说好呢?
做了一辈子木匠的父亲,您修了多少门窗,主持修了多少房子,可是您老没有赚到一分钱;勤苦劳作辛苦一辈子的父亲,您流了多少汗水花费了多少心血,可您从来不愿到医院为折磨您八九年之久使您丧失大半劳动力的病花一分钱。父亲,您抗争了一辈子,您在逆境中梦了一辈子。现在,您老了。您还在捧着儿子发表的作品用哼唱式似的品赏方式给他无比的鼓励和奖赏。您说您有罪,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职责,让母亲当牛做马在地里受苦,让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受苦。可是,父亲!这是您的过错吗?
父亲,您经常来信念叨让我多看看《杨家将》,让我记住杨家将。我怎么会忘记?那几册关于杨家将的线装书据祖父讲是早年先祖从江西带过来的。小时候,我出于好奇,经常瞒着您在祖父如雷的鼾声中偷偷出入他的房间,不止数十次地抚摸那些黄旧不堪,已被一种叫“灰鱼儿”的小虫子弄坏了不少的书册,纵然认不了几个字,却也能感觉到一些历史的神秘。
“教我启蒙识字的祖父念过私塾。他用唱诗般专注的神情和悠悠连绵的语调去读那些竖排的句子。祖父眯着眼睛,读得专心致志。当时我并不理解,现在想来,大概他捧的只是一种回忆,一种心境,读的只是一种情绪吧,读几段,就仰起头,见孙辈们团团围在身旁,便乐呵呵地接过已经点燃的烟锅吸上几口,再饶有兴趣地讲几段故事。这时候的祖父是最高兴的,冷不防还用粗糙的手掌拍拍正听愣了的孩子们。祖父讲诉的故事重复的内容还多,但总不乏听众。”
这是我童年的记忆。许多年过后,长大了的晴晴会不会这样写父亲您呢?同您一样,我也不能认定,我们这个家族与杨家将们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但仍然十分赞同长辈们写在脸上沟壑纵横那种飞扬的自豪。即使不是,也就不是罢。人活着,总要有一种向上的精神支撑复杂的生活。这种精神有时候本来就有,而大多只能靠想象和寻找。
你感到孤独。母亲要没日没夜地下地劳作,哥嫂也有自家的事情,与八旬的祖父也谈不了什么,您只有和您的宝贝孙女说话。可是侄女太小,还不到两岁,当然听不懂他祖父说了什么。不过您不管,您喜欢和小晴晴说话,说了半天,见躲在怀里的晴晴懂事地笑了,您也会两眼湿湿的,特别欣慰地跟着笑。
父亲,您真的老了吗?
母亲
每个人心中都藏有许多关于母亲的话题,可能这里面的故事太多,往往很少有人能满意地描述他的母亲,表达他们之间那刻骨铭心的挚爱深情。很早的时候,我就想为母亲写一篇文章,又担心笨拙的笔头写不出伟大的母爱的万分之一,写不出我对伟大的母亲最深的爱和最大的尊敬。我没有对母亲说过“我爱您”,这个世界上她是唯一一个我用全身心感恩并热爱着却不用表白的人。我坚信自己和母亲之间不需要任何言语和文字,多少年来我们就是这样用简单质朴的方式默默关爱,彼此挂牵。
母亲属于湖北五峰人氏。她十二岁参加生产队劳动,二十几岁嫁给了同样是贫民出身的父亲。近五十年的生活光景,母亲没有几天不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母亲心地极好,几乎身边所有的人都认为她和父亲是一对模范伉俪,因为他们都属于农村那种很能干的,并且少有争吵。我却深深地知道母亲在性急的父亲面前做出的迁就。她从来未曾对我们说过父亲半个不字。不甘被重病压垮的父亲有时候会表现得敏感多疑,而每当母亲无端受了委屈,他只是躲在一边使劲干活,边不停地念叨,“这……他爸的病哪门办呢?哪门办呢?”并不和父亲计较。
为了整个家庭,为了年近八旬的老人,病重的丈夫和读书用钱的孩子们,母亲终年生活在耕种背挑这种近乎原始的超越了女人性别和体能的劳作里。她言语不多,只知道起早贪黑没命地劳作。十三亩劣质沙田被她安排得满满的,收了油菜种花生,割了小麦种红薯,一年四季都有做不完的事。母亲还不嫌累,为了多收几担粮食,找几位本家叔叔讨了几片荒地,翻耕、锄地,几番折腾,又种上的苞谷或洋芋。农忙时节自不必说,即使是不可多得的农闲日,母亲也不肯在家闲着。她背了大竹篓,扛了锄头,到附近山头挖药材。丛林中荆棘遍布,野藤盘根,时有蛇虫出没。母亲天不亮就出门,饿了食红薯,渴了饮山泉,夜半回家额头或手臂常被野蜂蛰了肿得老高。而辛辛苦苦挖掘黄姜、采摘山倍挣得的一点钱她却不肯自己花,除了给父亲买药之外,就给家里带些油盐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