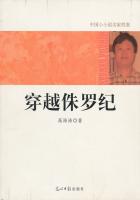许明在鱼儿她家一天的遭遇,让他一下子成了不明不白的人了。严格地说,许明是被鱼儿的两个哥哥一脚跺得对什么人都不敢相信了,包括他自己。他当时只想一点,离开这里!
许明走到了小镇上,搜遍了全身,幸好裤兜里还有二十元钱。他租了个机动三轮车,到了火车站。站上的人并不多,都是一些等夜车的人。这时,他已经开始有点清醒了,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如何能够坐上火车,可他身上没有一分钱了。
他犹豫一会儿,最终决定向别人讨钱。他先是向一位穿着体面的男人诉说自己是被人抢走了钱,但他得到的只是嘲笑,那人并没有给他一分钱。他再向一位很时尚的女性诉说同样的理由,那女的竟转身而去,根本就没有听完他的话。他觉得自己成了骗子,似乎在哪个火车站都出现过的骗子,就连他自己也仿佛在哪里见过。他本以为这些人会相信自己的,因为这些人更有眼光,会从他的言谈中辨别出他不是骗子,然而他彻底地失望了。
离他要坐的火车还有十几分钟时,许明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他走向那片坐在蛇皮袋上的民工。这些人到底是没有见过世面,对他的诉说极有热情,有人甚至下意识地向四周很警惕地瞅了一通,像是担心抢许明的那个歹人会不会突然出现。
许明现在只有骗人了,他把故事尽量说得刺激些,里面竟加上了一通打斗,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许明的身上明显有搏斗的痕迹。这些人到底是被许明给打动了,他们竟有人出钱,然后飞快地去买了张票,递到了许明手里。接着,许明竟被这其中的五六个人簇拥着进了检票口。许明悲壮地把脸上的泪抹进了嘴里,咸咸的苦涩。
许明躺在床上,把认识鱼儿以来的事一幕一幕地想过,他竟猛地坐起来,哈哈大笑着。笑声从这小屋里冲向昏暗的夜色里。你他妈这是干吗呀,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他妈干吗呀,你以为你是谁呀!止住笑的许明忽地又软在了床上,像一块破木板扑地倒了下来。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不知是醒还是梦,我们这个曾经是体体面面的宣传部通讯科长又接着反思了——
没有认识鱼儿前,自己一直都平平静静、慢条斯理地生活着,上班、喝茶、看报、点评时事、辅导儿子做作业、与妻子在一起吃饭做爱,一点也没有节外生枝的可能性。现在怎么了,怎么自从那天早上看到鱼儿后,一切说变就变了呢,变得这样超出他的想象。难道自己是真的像鱼儿两个哥哥说的那样,是图他妹妹的身体吗?没有呀,从来没有呀。那倒是为了什么呢?许明的思维又进入了一个难解的旋涡中。
人都是有欲望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欲望,他就不可能有生存下来的理由。世界也是有欲望的,没有欲望就不会这般变幻莫测。
许明想自己真的是对鱼儿有什么欲望吗?如果是真的像其他男人一样,想占有这个只有十七岁的少女,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不花上两张百元票子,去光明正大地占有呢?为什么在鱼儿要把她给自己时,自己竟没有一点那种感觉呢?许明想也许是自己真的太虚伪了吧。但不可能呀,要是有了那种欲望,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些破事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许明的思维又一次进行不下去了。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像妻子曾经骂的那样:你神经了!
自己到底是在做什么?是为了向社会证明什么吗,是在显示自己的责任感吗?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傻事呢?许明过去曾觉得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动物,现在他差不多认定自己是奇怪里的最奇怪的动物了。过去,他一直认为自己活得很清醒、很理性。他现在开始怀疑自己了,怀疑自己还是不是过去的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正常。
他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他必须结束这场噩梦。
已经睡了三天四夜的许明差不多就要虚脱了。他强迫着自己走回了父母那个家。在这中间,他似乎还到了那个曾经是他家的小院门口,甚至他还借着前面窗户的光线,看到了儿子写的那几个大字:许明是个大坏蛋!
一顿饱餐之后,天亮了。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还是那种温暖的红光,还是那样遍洒人间的无私与大方。许明重又迎着太阳光,走进了这个小城上班的人流里。当然,这次他的胳膊没有再夹着那个黑色真皮小包。因为,那个曾伴着许明上千个日子的小包,被鱼儿的两个哥哥给扔进那冒着臭气的猪圈里了。
机关里的人依然那样忙碌着,似乎没有人在意请了一周假的许明又回来了。
许明似乎又与从前的那个他重叠在了一起,严丝合缝的,看不出一点不一样来。
17
许明平静地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把鱼儿从许明的记忆里慢慢地淡去。
虽然有时鱼儿及因她而发生的事仍会时不时地跳出来,但许明却有点麻木了。其间,部长曾找许明谈过话,想让他主动找妻子复婚。部长并没有直说,可许明还是感觉到了这里面有妻子的意思。
许明现在不想想这事儿,他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他需要平静地反思这半年多来的事了,他的心确实很累,说不出的累与乏。有时他也觉得他似乎应该与妻子复婚的。因为这半年多,他就像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有些超出过去的直径在飞了。可他总认为他还没有脱离原来生活的圆心。这个圆心是什么呢?许明说不清,因为这圆心分明是一个混合体。
然而,发生过的事,再咋说也不可能说没有就没有了。许明有时也暗地里觉得,他与鱼儿可能还得有什么事要发生的。这种担心,就像在黑夜的远方草丛中,有一双发着绿光的蛇眼,让许明总是一想起来就一颤一颤的。
有些时候,许明心里还是苦恼的,他是为自己的行为会出现这种结果而苦恼。但这种苦恼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他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不明白。他对鱼儿的想法与做法,真的就与现在不融了吗?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许明有时真的不愿再想这些事。他变得更加沉默了。他从父母的家里搬出来,住进了鱼儿原来那间小屋。这屋子是交了一年租金的,与其让它空着,还不如把自己放进去呢。许明想,自己单住,心里或许会更好些。
让许明担心的事还是出现了。
一天,许明刚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部长就叫他去一下。部长很是和蔼地告诉许明,有一个人给部里写来了信,说自己的妹妹被许明骗了。许明立即愤怒了,压在心底的愤怒忽地冲了出来。部长见他激动得站了起来,就走过来把他压了回去:“组织是相信你的!你也不要说了,今后注意就行了。”
许明先是一愣,接着问:“你要我把这事全说出来?”部长再次笑着把他压在了沙发里:“你的事其实我们早知道一些了,我们是信任你的,以后别太理想化就是了。”
许明还要说什么,部长就说:“啥也别说了,安心工作,组织是相信你的!”
许明出了部长的门,心里难受极了,说不出有多难受。他突然觉得自己早就是一个脱光了衣服的人,众人早就在笑他了,只是他自己现在才知道而已。他不知道鱼儿哥哥的信里到底写了什么,到底写过几封信,他也不知道单位那些人心里都想些什么。他觉得背上一阵紧似一阵,像有一千根一万根针扎在上面一样。这些针就是众人的眼睛,而且都像是黑夜里草丛中放着绿光的蛇眼。
这时的许明几乎要崩溃了。整日脑子里晕晕的,人也瘦了一圈,就像被抽去了骨头的皮影人儿一样,虽然也活动着,可到底还是机械而呆板的。他真是有口说不清,屈辱和无处可诉的压抑,终于使许明病倒了。
他跟单位请了假,请了一个月的病假。但他没有去医院,因为他自己清楚他的病不是医院所能治的。
18
许明请假期间,洁来看过他一次。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声谢谢,就再也不想说什么了。洁呢,也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要他到医院去看看。仅仅是几分钟的时间,洁就与许明结束了会晤,然后就离开了许明住的小屋。
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她只是因过去的缘故才礼节性地来访。许明虽然心里是这样想的,但他还是有些感激的,他知道洁并没有把他从心里完全忘去。他还有可能再重新回到那个家吗?许明不知道,起码他觉得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
许明这一次去上班的时候,心里就轻松了许多。就像一个偷拿别人铅笔的孩子,在没被老师同学发现的时候,心里是最害怕与难受的。一旦这件事被大家都知道了,而且承认了错误,心里就轻松许多。有时许明也想,他之所以能有现在这样轻松的心情,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而且是公开地谈论过了一段时间。
他来到办公室,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别人不跟他说话,他也懒得开口。而大家仿佛什么都不知道一样,并没有什么人问他这件事,也没有人议论,大家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说说笑笑的。虽然还是那样轻飘飘的,但许明是适应的,机关的人不都是这样吗?这些年见谁实打实地说过多少话,还都不是虚头巴脑的。
转眼间就入冬了。
许明骑着车子来到市委大院门前,他下了车子,觉得额前的头发硬硬的。用手一抹,竟抹下一把白霜。这时,许明才感觉冬天来了,而且已入九了。
从春天见到鱼儿,许明就似乎没有怎么注意到时令的变化,是怎么从春天到夏天,夏天又怎么一转眼到了秋天,咋这么快就又到了冬天。许明真的没有怎么注意到。现在他真切地感觉到冬天来了,他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动弹,他想让自己回忆一下这从春到冬快一年的事儿。他就这样坐下来,一动不动的,接着,两百多个斑斑驳驳的日子,扑面而来。
在这之前的一些日子,许明总感觉到自己的脑子不好使了。有些事虽然影影绰绰地在他眼前,可总有点儿找不到根一样,就像天空中的云,飘忽不定,无根无据的。而今天却大不一样了,他一旦坐下来想自己与鱼儿的事,一件一件、枝枝叶叶、丝丝缕缕的都特别清晰。
时空的隧道又一次向许明打开,他在这突然而回的时空中,再次与鱼儿真真切切地相聚了。这时的许明没有前些日子的叹息了,他从鱼儿那清澈的眸子里,感觉到自己并没有什么错,甚至没有丝毫的后悔。这究竟是为什么?许明说不清,从春天一见到鱼儿时他就弄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