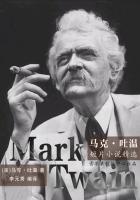00 鱼儿显然是被骗了,许明当时义愤填膺,呼地站了起来:“我要救你出去!”而鱼儿呢,却没有反应,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任许明在房间里像头狮子一样,来回地转着圈。鱼儿的两眼就像一口深井,无波无纹的那种。其实,她对许明的表现并没有感动,她认为他像一个孩子似的在那里说胡话,仿佛他就是解放劳苦大众的解放军一样。
许明是想立即把鱼儿带出去的。可鱼儿没有同意,这令许明很不解。他说:“鱼儿你不是在火坑里吗?干吗不出去呢?”
鱼儿却笑笑,然后靠在了他的身上:“你以为我们很苦吗?现在可不是万恶的旧社会呀,我们姐妹们认为这样很好的,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可做吗?何况我从不与男人做那事!”鱼儿调皮地问许明,眼里的水波一动一动的。
许明认为鱼儿是为现在的生活而满足,他彻底地恼怒了,大声对鱼儿喊:“堕落!”
鱼儿这时又恢复了第一次见他的样子,站起身子笑起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4
鱼儿这几天心情突然不好起来,她自己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就是见什么都烦的感觉。
过去她也常有心烦意乱的时候,这也就是过去这两年开始的事,是一种周期性的,与她身体的周期变化几乎同步。而这几天,她感觉不是过去的那种烦躁的味道了,而是全身都特别地懒,仿佛她成了一副囊,拎起来不能放的,一放就塌作一堆的那种疲软与无力。
原来她每天早上六点就起来的,她要看看小花园里的那几束花,无论睡得有多晚到这个时间她就一定得起来。而这几天,她都在九点后才起来,晚上睡得也早了,这两天都没有接待客人了,她总以身上来了为借口。其实,她虽然起得晚,可还是六点就醒了,这是一年多来形成的生物钟,一到这个时候就必须醒。醒了又不起,那干什么呢?那就只有想事儿。鱼儿这几天都在想许明,无论想什么,想到最后都得拐到许明的身上来,她的思绪就是挂在树上的苹果,许明就是地球,他的引力使这只苹果不能不落在他身上。
今天,鱼儿一醒来就想起了那枝玫瑰,这是她长到十六岁第一次有人给她送花,而且送的是玫瑰,更主要的是送花人竟是许明这个她从没有想过的男人。顺着这条思路,鱼儿在想,许明就像命中注定的一样走进了她的内心,她不明白许明是什么心理。她认为许明是一个谜,比以前老师给她出的任何一个题目都让她难以破解。
许明究竟要做什么呢?第一次见许明,鱼儿认为他与其他男人并没有两样,也只是个伪君子罢了。这样的男人她见得多了,都是喜欢自己年龄小,有不少人在她身上都想有一些变态的作为。而现在她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了,他并不动自己一手指,而且就像是一个老师,就像她的那个班主任一样。
他要做什么呢?他说要救自己。鱼儿想,我有什么可救的?我活得不是好好的吗?我不这样活又能做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我们都生活在痛苦之中吗?你错了,这种生活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就是最好的选择了。鱼儿想,家里现在是这个样子,父亲瘫在床上,又欠这么多钱,只有母亲一个人在撑着。尤其是她的两个哥哥,过去多好啊,现在娶了媳妇就完全变了人一样,不但不帮母亲,还想着法儿给瘫在床上的爹和受罪的娘吵架。每当这时,她都想起小时候娘教给她的那段歌谣:
灰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不要娘。
把娘送到高山上,他好在家把福享。
烙油饼,卷砂糖,媳妇媳妇你先尝。
吃得好,喝得好,哪想高山上苦命的娘。
高山上,风儿凉,冻病苦命遭罪的娘。
将你生,将你养,到老落得这下场。
……
在心里低吟着这段歌谣,鱼儿眼中不由自主地噙满了泪。
自己不退学又能怎么样呢?就是考上高中,家里能有钱供自己上吗?像自己这样的乡下女孩子,做这就不错了,有钱花有玩的。这样想着,鱼儿竟在心里笑了起来,她都要嘲笑许明了,都三十多的人了,脑子像灌了水一样啊。
像鱼儿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思想是不太固定的。她自己都感到心里的想法就像花丛中的蝴蝶,飘忽不定,她也不想让这只蝴蝶固定在一朵花上,也绝不可能的。有时给客人做按摩时,鱼儿脑子里经常会一片空白,什么想法都没有,就像一张白纸。
有时,她会突然想起学校来,想起与她同村的华子。她也想在学校里上学,尤其想像华子那样上完高中读大学,读完大学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这种事哪个女孩不想呢?可现在自己呢,却在这么个地方,而华子现在也许正在县里念高中,他是一定能考上县里的高中的。她从小就是喜欢华子的,他们从小一道儿去上学,一直到她退学那一天。
但现在如果华子知道自己在这么个地方,他会怎么看自己呢?正是为了这个原因,鱼儿坚决不与男人发生那事,亲亲摸摸什么事都行,就是不能让男人占有自己。为了保护自己,她心细得很,喝水吃饭都特别小心,生怕被别人用药给蒙了。同时,她不止一次扬言,只要谁逼她,她就死给谁看。
有时,当客人非要与她做那事时,她就说自己有肝炎病,家里两个哥哥和爹都是得这病死的。这样一来,到现在竟没有一个男人占过她。当然,最主要的是她觉得自己将来是属于心里的那个华子的。
现在,鱼儿心里想到了许明,她想许明是她这一年多见到的最规矩的一个男人了,说话像老师一样,一字一句的,带着笑,带着关心。她一下子感到自己太需要许明给她的那种感觉了,那话语、那眼神、那呼出的气息,都像一股微风吹拂在她的心坎上。不,应该是一双手抚摸在她心上,她感觉自己的每一根汗毛都在颤动。
有了这种感觉,鱼儿心里就像突然填满了委屈,委屈就像一眼泉水,从她的两眼里呼呼地向外涌。
5
许明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黑洞,一个无底的巨大的黑洞。这个黑洞就是他自己的想法,就是他必须把鱼儿救出来的想法。
这些天他一直在想,他必须把鱼儿从那个地方弄出来,正像花骨朵一样的鱼儿怎么能在那里度过一生呢?鱼儿虽然表面上并没有答应他,而且,鱼儿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在那里没有什么不好,可越是这样,许明就越感觉到鱼儿的内心并不喜欢那里,不喜欢她现在所做的事,只不过她现在没有更好的事去做,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做什么。
当然,许明也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像鱼儿这样的姑娘全世界多的是,别说一个许明,就是一千个一万个也无济于事的。但许明现在心里就只有鱼儿,他弄不清是被鱼儿的什么吸引住了,他决定在这个事上他一定要做出自己的努力,并且得有一些结果来。
怎么才能让鱼儿从那里出来呢?许明想关键是鱼儿自己不愿意出来,只有她自己觉悟了,她才能走出当前的处境。可鱼儿给许明的感觉是:我在这里挺好的!许明由此产生了恨铁不成钢的苦恼,他想,他只有采取非常的措施才能使鱼儿离开那里,因为他感觉鱼儿是绝不会自己主动醒悟的。
有了这个想法后,许明踌躇满志,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感在胸间回荡,而且一种大丈夫仗剑南山的英雄气概使他也比过去多了几分自豪感。他感觉自己过去只不过是个气球,而现在呢,他被这种想法膨胀了起来,不仅庞然威猛,而且飘飘欲飞,好不快哉。
其实,许明现在并没有具体的措施,他只不过刚有这种打算和想法。有时人的想法力量特大,它可以使人产生无穷的力量,无往而不胜,无所而不能。虽然,目前他并没有太明确的办法,但他是充满自信的,他想他一定能有办法使鱼儿离开那个地方。什么办法呢?他这些天来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思考,以致他的妻子洁竟有所觉察了。
这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反反复复的不能安宁,洁开始并没有吱声,第二天也没有吱声,而到了第三天,洁才说:“你把心里的事说出来吧!”
许明先是一惊,继而,很轻松地耸了耸肩膀:“我有啥事?我能有啥事呀?”
他笑了,洁也笑了:“你这些天心里有了女人!”
许明笑得更响了:“嗨,你不是说像我这样的人放在女人堆里都不会放出屁来的吗?”
妻子洁的脸突然一变:“你能拉出啥屎,我还不知道!”许明以为妻子洁真的知道了什么,还想分辩。可洁竟不再提这事,而且一连几天都不提这事了。这就使许明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必须加快步伐!
下班前的一瞬间,许明突然想出了一个让他自己都吃惊的办法,那就是报110。只要110接警了,鱼儿就会被抓,抓到公安局后,他就可以通过同学海峰把她弄出来。想到这里,他飞快地蹬着自行车回到家里。妻子洁已经做好了晚饭,许明很兴奋地吃着饭,吃得特别快,没有一点儿吃相,几乎是狼吞虎咽,而且嘴里还哼着什么曲子。妻子洁眼睛瞪得老大,有几次都停了下来,但许明并没有感觉到她的变化。
碗和筷子往桌上一撂,他就起身了,说是去办公室写篇稿子,也没有等洁的答话,就出了门。他骑车走在路上,心里想着如何向接警的人说这件事。他想了一套回话否定了,又想了一套方案也否定了,一直到他坐在办公室里,都没有想好。但这也并没有影响他立即拿起电话。可电话发出嘟嘟的响声时,他又犹豫了:在办公室里打电话不是暴露了自己吗!不能,绝不能。
许明想,只有打IC电话了。
现在这个时辰,街上的人已经不是太多了,IC电话旁也不是都有人的。可许明还是觉得自己现在去打电话好像有什么危险似的。他空着手在街上走着,眼却盯在沿街的一个一个IC电话上。他不仅瞅哪个电话旁没有人,更重要的是,他还想看看行走在街上的人有没有注意打电话的人。他就这样像一条觅食的游狗一样,很谨慎地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鼻子也哧着,不放过一切他不熟悉的味道。
都快十点了,街上的行人已经很少了,有的只是呼呼跑着的各种车辆,许明大牙一咬,攥了一下拳头,关节咯咯吱吱地响了一阵子,他想他现在必须去了!
他找到一个稍微隐蔽一些的IC卡电话亭,电话一拨就通了,许明顿时没有了刚才的紧张感,很流利地把自己的想法全告诉了接警的人。挂了电话,许明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像一块巨石被搬走了一样,全身都舒展了开来。
当他向四周看看,并没有见什么人从这里走过时,他竟无声地笑了,是那种胜利后由衷的暗喜。许明想,没有什么啊,做了又怎么样了呢?不还是一样吗?他对刚才两个多小时的踌躇感到不好意思,甚至是恼怒,他想我是在做光明正大的事,我怕什么呀我怕!回家的路上,许明依然走得很慢,他没有坐车,他是想慢慢地分享成功的快乐。
进到家里,他洗漱的动静很大,像一个取得重大胜利的将军,没有了什么顾忌。妻子洁也没有睡着,依她的经验,许明今天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好事,虽然许明平时什么事都不对她讲,可对于一个细心的妻子来说,丈夫的什么事能瞒得了她呢?洁也不问他,她不想知道具体是什么事,她没有必要知道,只要知道丈夫的心情就行了,她是懂得给丈夫空间的女人。
许明什么也没说,就贴着洁睡下了,但洁已从他的喘气声中、身上肌肉的触碰中感觉到了他要干什么。这是只有夫妻间才有的特殊语言,洁慢慢地开始做出反应了,也许你会认为洁为什么不很快做出反应呢,都快十一点了。可洁有她的经验,这样才能最好地调动丈夫呢。许明今天的精神比往日都要好,洁明显感觉到了,而且自己也不能像往常一样慢慢地动作,她要求自己必须对当前的战局作出调整。
这时,街上突然传来了瘆人的警笛声。许明突然从洁的两只胳膊中挣脱,直直地坐在了洁的右腿上……
6
许明拨通了电话,海峰在那边问是谁,许明停了几秒钟,还是把电话压上了。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开口,他想他只要一开口,海峰必然要问他与鱼儿是什么关系,甚至会认为他是嫖客。
绝对会认为他是嫖客,你许明怎么认识一个外地的三陪女呢?你不是嫖客又怎么认识的呢?一定是次数多了产生了感情吧,这是最合逻辑的事了。许明想,如果自己是海峰也会这样想的。但事已如此,也没有别的办法,鱼儿说不定还在拘留所里呢。许明想现在只有撕破脸皮跟海峰说了,无论他怎么想,无论他信不信。
第二次再拨通电话后,许明就说:“海峰,你现在忙不忙?”
海峰说:“你有啥事说吧,昨晚刚逮着十几只‘鸡’呢,正在一个一个地问着,想不想来听听?也可作为你的写作素材呀。”
许明在这端有几秒钟没有说话,海峰在那边显然是急了:“你今天怎么了,有屁就放呀,我还有事呢!”这时,许明才说:“我真的有事,我马上去找你,行不行?”
海峰说:“好,就知道你是想见识见识这些‘小鸡婆’,来吧,我在局里呢!”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可许明却没有放下话筒,耳边只有嗡嗡嗡的电流声。
许明在海峰办公室里,把要说的话一口气说完了。他也不看海峰的脸色与表情,就只顾自个儿说,真像竹筒里倒豆子,哗哗啦啦一下子就全倒出来了,他担心自己一停下来就不能再开口了。当他说完后,海峰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吃惊或嘲笑,只说那你替她交了罚款吧,减半,两千元,不过你得写个担保书。
许明望着海峰没有说话,他是在考虑怎么写担保书。海峰说带钱了吗?许明点了点头。这时,海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递给了许明。许明按着表上的内容一项一项地填写着,几乎没加考虑很快地填写着。
当填到“与被担保人是何关系”时,许明望着海峰:“这咋填?”海峰这时突然笑了:“你问我我问谁呀!”他显然认为许明与鱼儿就是“鸡”与“嫖客”的关系。
许明说:“你笑什么?你不相信我?”海峰笑得更响了,似乎是憋了很长时间的笑一下子爆发出来一样,而且再也抑制不住了,直笑得喘不出气来才算结束。笑过之后,海峰从许明手中夺过笔,飞快地在这一栏中写上了“亲戚”两字,然后说:“这按手印的事我不能代替了。”许明没吱声,他把右手拇指跷起来,在鲜红的印泥上很重地按了一下,然后又在那张表上很庄严地按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