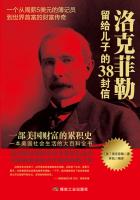他们说话走动的声音渐渐远去,偏离向村东头。我故意弄出些响声,还钻出来跳了几个蹦子,想引他们过来。可是没用,他们离得太远了。
“柴垛后面找。”“房顶上找一下。”“菜窖里看一下。”他们的叫喊声隐隐约约,我又藏进那丛干草中,掩好自己,心想他们在村东边找不到就会跑回来找。我很少被他们轻易找到过,我会藏得不出声息,我会把心跳声用手捂住。我能将不小心弄出的一点响声捉回来……
夜又黑了一些,他们站在院子里,好一阵一句话不说,像瞌睡了,都在打盹。又过了一阵有人开始往外走,其他人跟着往外走,院子里变空了,这时雨点落下来,有一两滴落进鼻孔,直直滴进嗓子里。
我一直藏到后半夜,整个村子都没有声音了。屏住气,我突然听到整个村子变成了一个东西。它猛地停住,慢慢蹲下身去,耳朵贴近地面。它开始倾听,它听见了什么,什么东西在朝村子一点一点地移动,声音很小、很远,它移到村子跟前还要好多年,所以村子一点不惊。它只是倾听。也从不把它听见的告诉村里的人和牲畜,它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起身离开。
或许等那个声音到达时,我、我们,还有这个村子,早已经远远离开这个地方,走得谁都找不到。不知村子是否真听到这些。不管它在听什么我都不想让它听见我。它不吭声,我也不出声。村子静得好像不存在。我也不存在。只剩下大片荒野,它也没有声音。
这样不知持续了多久,村子憋不住了。一头驴也叫起来,接着另一头驴、另外的好几头驴叫起来,听上去村子就像张着好几只嘴大叫的驴。
我松了口气,心想再相持一会儿,先暴露的肯定是我。因为天快要亮了,我已经听见阳光刷刷地穿过遥远大地的树叶和尘土,直端端地奔向这个村子。曙光一现,谁都会藏不住的。而最先藏不住的是我。我蹲在村东大渠边的一片枯草里,阳光肯定先照到我。
从那片藏身的枯草中站起的一瞬我觉得我已经长大,像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动物在一丛干草中寂寞地长大了,再没地方能藏住我。
门一关上,就永远关上了。通往消逝了的时间脉搏的另一个入口是不存在的。
灌木丛中的钻石
卡洛尔·娜普译/唐小蒂
我并不想迁往阿拉斯加,那是我丈夫特里的梦想。还是在做孩子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夏天。而对我来说,阿拉斯加只不过是一堂被我早已淡忘了的地理课。那是一块被人叫做希伍德冰箱的土地;在那儿,爱斯基摩人居住在圆顶茅屋里,猎狩北极熊那是我丝毫不感兴趣的远乡僻壤。
我和特里在华盛顿州的斯波肯过着惬意的郊外生活。然而有一天,他意外地得到了一份去阿拉斯加的工作。于是,我们乘上飞机去了北方,想去仔细瞧瞧。这冰箱突然间不再是笑谈了。我走下飞机,那冰箱的门一下子冲我敞开了。
接下来的三天可真够呛。我是心诚意笃地想喜欢上阿拉斯加,但是,春末对于我同阿拉斯加的初次见面来说可算是糟糕的时候了。一开始,虽时值五月,而湖面上却依然是冰雪皑皑,举目不见一片绿叶。如同泥土中的那种褐色,呈现着这个季节的色调,到处都是如此。还有大得出奇的蚊蝇,瘦削挺拔的云杉树,以及地上的麇鹿粪……一切都是真切的了。
房屋大都星星点点地随意散缀在树林中,而不是井然有序地排列成行,坐落在灌木的掩映之中。在这里你见不到草坪那类的东西。我发现乡村里的阿拉斯加人竟然用链锯在院子里割草。
决定了,我们将迁来阿拉斯加。我装作挺快活的样子,可在心里却情绪低落。阿拉斯加使我感到畏惧,她太辽阔、太荒凉,确切地说,它不在我所熟知的美国之中。回到家里,那几个星期就记忆模糊地全在腾空碗柜、出售车库和道别声中过去了。我不愿意看见我的家具被那些贪婪的生意人一抢而空,一件一件地被运走。最后那天,我在屋子四周转来转去,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摸着每一面熟悉的墙。
在所有这一切的不愉快之中,有一个特殊的时刻。那是在一个早晨,我独自坐在屋外。这时,我年轻的女儿布兰达,赤着双足,穿着睡衣走过来,同我坐在一起。我们默默地注视着阳光在草丛中的露珠上熠熠生辉。“瞧,布兰达,”我说着,又指了指,“那就是上帝的钻石。”
她朝那一片闪烁的草丛走了过去,小心翼翼地取下一滴露珠。
“啊,你给我摘下了一颗钻石!”我叫道。
她用指尖将它送到我跟前,然后我们一起把它举到阳光下。我们被一粒普通的水珠放射出的耀眼光芒给迷住了。
七月里出发的日子到了。在那些植物和箱子的空隙里,我们往旅行客车里塞进了四个孩子和一只迷惑的狗,开始了驶向阿拉斯加毕格湖的二千六百英里旅程。要不是终点错了,这倒是一次了不起的度假。可我们再不会回来了。
我们一直往北行驶,白昼逐渐地变长了,直到夜晚全部消失,而阿拉斯加绵延的山峦也越来越近了。第七天早上两点,我们十分疲惫地到达了毕格湖,遇上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一位老住户向我这样的新来者表示欢迎,他当初也不想来这里。
雨接连下了两天。第三天早晨,天空晴朗,气候温和。我独自坐在卧室里望着窗外的灌木丛。阳光勾勒出了秀美的白桦树干上树叶的图案。红松鼠在树丛中跳来跳去。这是一个闲散的日子,一切都适得其所,但对我却不然。
在内心里接受搬迁的事实是经历了一场斗争的。我对阿拉斯加抱有敌意,并且陷入了绝望之中。后来,在那近在咫尺的地方,我看见了绿叶上的一颗雨珠,它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勃勃生机!刚才还是一粒湿漉漉的水珠,转瞬之间就变成了一颗璀璨的珍珠。我的记忆中立刻闪现出一颗露珠在布兰达的手指上闪耀的情景。虽然它默默无言,但我明白这颗雨珠所允诺的是什么。
它似乎在说:瞧,卡洛尔,世上到处都有钻石啊!
于是,就从这一刻起,我开心地笑了,我感到解脱了,浑身又充满了活力。就是那样一颗普普通通的雨珠驱散了我心中巨大的恐惧。我又望了一眼,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使,它栖息在那片绿叶上,正冲着我眨眼呢。
如今,我们在阿拉斯加已经生活了两年。一个一个的日子如同充满了冒险的骑术比赛。我会在附近的河狸摆尾戏水时划着一只独木舟,或是望着落日的余晖沐浴着一群驯鹿,或是去注视荒野小径上的一只山羊,要不就是坐在蓝莹莹的冰川上,或是眺望着北极光在夜空中闪射着耀眼的光芒——这一度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从来没有梦见自己会发现一只黑熊趴在卧室的窗户上窥探,或是惊动一只在院子里吃东西的麋鹿。我永远不会想到我的洗涤槽里会装满了鲑鱼,或者是炉子上烘烤着塞满了野酸果的面包。我也没有想到过秋天里会有白桦树叶覆盖而成的黄色大海,或者牵引着雪橇的猎狗无声地从雪原上跑过,还有那一望无际、蜿蜒展现于眼前的雄伟山脉。在阿拉斯加,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是啊,我热爱阿拉斯加,我属于这里。只要我一睁开眼,我就会看见到处闪烁的钻石。
智慧的可靠标志就是能够在平凡中发现奇迹。
额外的恩赐
其博德·罗雷基
某个十月的夜晚,我黯然神伤地沿着滨海村庄的街道踯躅前行,去探望重病卧床的朋友。当时满月高悬,银光洒地,使我的心顿时安静下来。整个世界变得光辉灿烂,每株矮小的灌木和每块石头都有如脱胎换骨。一阵微风带着沼泽的气味吹过满溢的潮水。
原来我的朋友也在欣赏月夜之美。他望出窗外,可以看到迷人的夜色,月光泛在海潮上,又穿过树林掷下白色长矛。我在他旁边坐下,一只鸟开始在月下高歌。
许久以后,朋友对我说:“我原以为那个夜晚会是我最后的一夜。可是一听到那只鸟的歌声从窗外传来,我就知道我会复元。”
我认识一位老猎人,在世上虽是默默无闻,却是个忠实的朋友。他偶然会告诉我一些关于自己的事,通常都是很奇特的,就像下面这个故事:
“这是去年六月发生的事,”我的朋友告诉我,“比尔·摩尔多年来和我一直不和,我们最后一次相遇,打了个你死我活,幸而朋友把我们拉开了。
“那夜以后,我想这个仇是结定了。我知道他身上有枪,于是我也枪不离身。后来,六月某天,一个朋友告诉我,比尔说他计划干掉我。我决定先下手为强。那天傍晚,我向比尔家走去,准备了结此事。
“离他家大约一公里半,我看到路上有个人走过来。我退到路边,躲进月桂树后面。周围是灌木丛,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杀气腾腾紧握手枪。我举起左手拉开一条树枝,忽然看到枝上有一朵白花,一朵可爱的月桂花。
“你会以为我傻了,但我真的俯下去嗅那花的香味。我母亲最喜欢月桂花,我小时候,她叫我从沼泽地里挖出一棵月桂树栽种在自家院子里。她下葬时手里也拿着月桂花。我于是想起母亲希望我做个怎样的人。
“接着,我一抬头,赫然发现比尔已经走在我对面的路上。不过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我从灌木丛里跨出来,大声喊他。他看我的来势知道我是没有恶意的,不会出问题。而事实上的确没有问题,我们当时当地就把问题解决了。你听完了怎么想,是完全因为一朵小花吗?不过事实就是这样,像我所告诉你的。”
有一天,我走进树林,想忘掉失去挚爱之人的哀伤。不久,我听到一只莺儿啭鸣。它站在秃柏顶,俯瞰林间湖泊。乐声把我包围了。风过处,小溪潺潺,长草飕飕。抬眼四望,到处都是未经斧凿、与世隔绝的自然之美。
音乐和美景这些额外的恩赐,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我慢慢摆脱了锥心的哀痛,终于心平气和。
在树林里,我看到了生和死——在绿叶和枯叶里,在挺立的树木和倒下的树木里。如果你还提出为什么会死的问题,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就是答案。在树林里,在大自然赐给我们的那些东西之中,我醒悟了。
为了得到永恒的力量,我们必须依赖信仰:为了保持永生不灭的希望,必须信赖那些我们心灵所感应到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