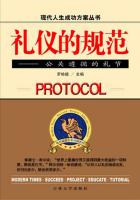尹仁街角巷道里穿梭了一夜,却没发现丝毫线索,还要躲藏随处都在的巡逻兵,眼见天快亮了,只能找个地方躲藏,突然灵机一闪,尹仁想到了王允府邸,在长安,第一个躲藏地点就是王允府了,若要汇合明显就是那里了。
若狼女没事,必定会去那里等他,若有事,也可让王允探听下消息。
当即向王允府潜去。
街很静,只有偶尔传来的巡逻脚步声和街边的狗吠。
尹仁一个人在街边跑动,跑的很快,但下脚很轻,不至于发出很大的声响。
黑暗中渐渐显出“居品楼阁”所占据的繁华的街头,酒楼就在十字街口,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酒楼是三层复式结构,在长安城内同类行业中,规模已算很大,可知老板沈重家资雄厚,酒楼的一楼喝酒吃饭之地,二三楼为住宿房间,楼后是个大院子,院子内有个二层小楼,小楼对面便是酒窖、厨房和下人居所连在一起。中间空地遍值花卉竹木,曲幽小径穿梭其间,环境优雅。
尹仁不觉放慢脚步,躲藏在一个杂物堆里,回想起晚上的情景,整理混乱的思绪。
晚上在酒楼里,突然很多官兵,显然有人发现了他们,并向董卓通报了行踪,正要出逃,便被黑衣人拖延,显然通风报信的人便在酒楼里,黑衣人也在酒楼里,而后尹仁和孙策分开之后,并未发现黑衣人跟踪,但会不会跟着孙策呢,何况孙策和仆人都受伤。尹仁暗怪自己大意,一直在担忧狼女的安慰,此时再次看到酒楼时才想起这孙策来。
正暗自责备,突然听的身后传来脚步声,尹仁心头一喜,或许狼女也会来此跟他汇合也不一定。
一个身影从黑暗中奔跑了过来,不是狼女,是个男子身形,也不像孙策和其他认识的人。未急细想,人影很快从尹仁前跑过,是个穿黑衣的人。
看他行动匆匆,不知有什么事情,尹仁忙坠着他。
那人的目的地正是居品楼阁,他在后门一靠,便有人给他开了门,那人朝后环视周围,发现无人,便转身进入。
那人转身之际,尹仁正要隐蔽,突然被一只手拉了过去,人靠在墙的犄角处。
尹仁一见那人芊细的身形,喜道:“狼姐,你过来我竟然未知。”若要是敌人,死了也不知道是谁杀的。
狼女轻声道:“你太专注于那人了。”瞧着那人进门,继续说道:“我一直找不到你们,突然发现这黑衣人鬼鬼祟祟,一路跟来,想不到发现了你。”
尹仁道:“我们跟去看看,看他搞什么名堂。”
两人悄悄的跳进墙内,四周一片黑暗,只有那二层小楼的楼下还亮着灯,尹仁和狼女猫着身体向窗边靠过去。
窗边值着几排文竹,尹仁和狼女借着文竹掩映,捅破窗纸,室内情况,一览无遗。
只见四人围坐一桌,三人穿着平常的衣物,只有一人身穿黑衣,想必就是刚刚进去的那人,还未及时脱下夜行衣。
那黑衣人已除下面罩,长的贼眉鼠眼,短小精干;黑衣人右边的人背对着尹仁和狼女,两人看不到样貌,黑衣人对面的人身体最为魁梧高大,粗眉大眼,方口阔鼻,摸样很是正派,最后那人面如冠玉,模样英俊。
那背对的那人品了口香茗,愤然向几人说道:“今晚忙碌了一晚,折损了好些兄弟,却一无所获,如何向师傅交代。”
狼女和尹仁不觉望了一眼,露出惊讶神色,那人竟然是沈重。尹仁发现了沈重掌心的老茧后,就知道沈重是会家子,只是沈重既然与朝廷勾结,欲对尹仁不利,为何还救他们?
沈重转向那贼眉鼠眼的人,问道:“张师弟也是追踪高手,寻着孙策方向,两人又是伤员,怎么还追不上他?”
原来那贼眉鼠眼的人姓张,被沈重一问,面色发红,惭愧道:“那孙策并非等闲之辈,在长安必有个落脚点,我追到西大街便失去了踪迹,找了半夜,也没半点发现。”
沈重也不好再说什么,无奈道:哎,你们本是来京助我完成大事,可如今,大事未成,却损兵折将。”说着摇头叹息。
尹仁不知道他说的大事指的是什么,仔细的听着,希望能在言语中透入。
那长相英俊的男子,说道:“事已至此,我们只能向师傅坦白,再想想有什么解决办法吧。”
那身材高大的人,也说道:“若今晚能除掉孙策,孙坚定然会愤而攻入长安,到时天下大乱,岂非大功一件,办不办那大事,不多一样嘛。可想不到啊。”说话如巨石摩擦,甚是难听。
听到此言,尹仁知道今晚的行动,并非是针对自己,而是针对孙坚,而他们的目的是要天下大乱,想要天下大乱的人很多,而他们到底谁人所派呢?而且到底什么样的大事,同样能使天下大乱?
沈重听得更加心烦,愤然道:“想不到,想不到尹仁和孙策如此厉害,想不到我们这些兄弟竟然如此不济,想不到,想不到的事情多了。”说着转身向那英俊的男子,说道:“明日,楚师弟去向师傅禀明情况,再做定夺。”
姓楚的点头,应道:“是。大师兄。”
其他几人都低头,闷而不响,显然十分尊重和惧怕沈重,想不到沈重除了是这个酒楼的老板外,还在这个组织中地位十分高的人,那姓楚的人称呼他为大师兄,他们都提到一个师傅,想必他们是师兄弟几人。
沈重一拍桌子,几人不明其义,纷纷抬头看他,只听他叹道:“机缘之下,竟让我救了尹仁,我沈重阅人无数,可断定此子必成大器,不可限量,本可籍此结交接纳,为我所用,可惜,今晚真是一败涂地。”
那身材高大的人安慰道:“大师兄放心,我们今晚蒙面行动,且本是借着朝廷之手,该不会怀疑到我们的,还以为我们是朝廷的人。”
姓张的人说道:“郭师弟说的也不无道理,师兄不必介怀。”
沈重沉思片刻,说道:“算了,想再多也无用,师傅或会来长安,等他来了再说吧。”
尹仁和狼女听到此处,知道不会再有什么有用的信息,便偷偷的出去。
及至王允府邸,天刚蒙蒙亮。
王允见到两人很是欢喜,但要去早朝,便让尹仁和狼女去休息。
尹仁和狼女各自洗了下澡,整理下崩裂的旧伤,涂上沈重给的龙膏粉,便去休息,都是辛苦了一晚,刚洗澡更觉全身舒坦,片刻已进入梦乡。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尹仁感觉似有人在边上,猛的睁开眼睛,只见王允正坐在一边,持卷阅书。
王允感觉到动静,抬头见尹仁醒了,忙露出微笑,道:“你醒了?”显然已等了很久了。
尹仁叫了声:“王伯伯。”便起床。
王允一直含着笑意,说道:“我一直很担心你们,现在也放心了。”
尹仁感动道:“累的伯伯担心了。我还担心董卓会对你不利呢。”
王允笑道:“我官至司徒,董卓也忌我三分,况且没有能说明你我的关系,也不能证明你们是躲藏我家的,在董卓眼里,一直以为我是向着他的。”
王允看了眼桌上的食物,说道:“过来坐吧,吃点东西。”
尹仁点头恩了一声,便过去开始吃起来。
王允看着尹仁吃的样子,呵呵一笑,说道:“哈哈,我想起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你那狼吞虎咽的样子。”
尹仁嘴里塞着食物,笑了一下。想起跟尹仁相遇不久,但对自己关怀备至,甚至冒着灭族危险保护着自己,尹仁失去亲人多年,已经感受不到这样慈父的关爱,不觉想起了父亲和舅舅,眼眶已微微泛红。
王允看到尹仁眼神不对,满是感动之色,立即明白尹仁的内心想法,知道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亲人,爱怜的说道:“慢慢吃。”不想气氛如此深沉,便转换话题,说道:“纪明已经被杀了。”
尹仁对纪明本就没好感,也不以为异,想起了文录,问道:“那文录呢?一起被抓的。”
王允道:“文录该还没被杀,文录是右营的人,吕布怕还有顾忌吧。纪明本是左营的人,叛变投靠了右营,若不杀他,难泄左营人愤。”
看了尹仁一眼后,继续道:“今日董卓满是愤怒之色,看吕布时眼神尤其不悦,纪明投靠了右营,吕布杀他,虽平了兵愤,但定引的右营人的不满了。况且又是如此节骨眼上,右营李傕等定然在董卓处落井下石。”
尹仁边吃东西边说道:“逼迫越紧越好。”
王允点点头,想起了廖化和水影月,问道:“水影月和廖化等人呢?你们这两天藏在长安哪里?”
尹仁想起她们,不禁食不下咽,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于是便说了离开王允府后的情形。
王允听着尹仁说完,说道:“你们竟然遇到了孙策。”
尹仁道:“王伯伯,也认识他呀?”
王允摇头说道:“哈哈,我怎么会认识他,只是听过他父亲孙坚,那贼子妄藏传国玉玺,却因此送了性命。”
尹仁一惊,忙道:“孙坚死了?给谁杀的?”
王允以为尹仁因为孙策才如此关心孙坚,却不知他还因为传国玉玺的关系,回答道:“今早刚接到的消息,孙坚三天前被刘表部下所杀,如今孙坚旧部在寻孙策,想不到孙策瞒着他们,竟然在长安密谋要刺杀董卓。听说那晚那几个刺客连董卓的面也没见到,实在是年轻气盛,不自量力。”
尹仁想起孙策,今日也该知道父亲被杀的消息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惋惜道:“听闻孙坚勇壮刚毅,英年早逝,确也可惜。”
王允却脸有不屑,大有死有余辜之意。私吞传国玉玺,就是死罪。
尹仁流露伤怀之色,想起传国玉玺的下落,道:“那传国玉玺呢?”
王允盯着尹仁似乎大有深意,想了想,便笑道:“传国玉玺上的大秘密,想必你们也知道吧。”当年张让深得汉灵帝的宠信,必然告知了传国玉玺的秘密,而张让知道了,尹易自然知晓。
尹仁知道不必隐瞒,说道:“尹仁有所耳闻,但只限于传说,不过想必也非空穴来风吧。”
王允说道:“宝藏确实是有,只是藏在何处,无人能知,秘密皆在于传国玉玺,如今有不臣之心者,欲得而图天下,真是可笑,难道一个宝藏能毁我大汉几百年的基业?”似也在提醒尹仁要忠于大汉。
尹仁道:“不过如今诸侯拥兵据地,若无人威摄天下,力挽狂澜,怕要重演周末诸侯并立的局面。”
王允愤然说道:“董卓本可力挽天下,奈何其狼瘴之性,终落的遗臭万年的下场。”说到动情之处,王允重重的捶在桌上,道:“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可恨,可恨哪!”说着咬牙切齿,气愤的眼眶泛泪。
尹仁明白王允说的是那些手有重兵的诸侯州牧,却只知道兼并撕杀。出言安慰道:“王伯伯不必悲伤,一切自有定数。”想要多说几句劝说安慰的话,但也不知道什么。
王允重重叹了口气,说道:“只是百姓。。。”已然哽咽的说不下去了。
尹仁看着这胡子斑白,两鬓染雪的老人,突然心中升起一股崇高的敬意,这不是个只会出言阿谀奉承,只会做表面文章的老人,而是实实在在的在心中想着百姓,记挂着百姓;会真真切切的为天下为人民考虑,会为劳苦人民的苦难而担忧而难过而内疚而心急,一个真正的鞠躬尽瘁的官员。
为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