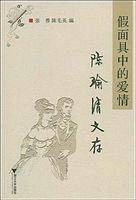在草原的牧民家里,都有钐镰,钐镰是他们在秋天用来收割大片牧草的主要劳动工具。在观察中我发现,他们听说我是城里人,就委托我为他们在汉人街购买那种苏联出产的钐镰,他们说苏联的钐镰比国产的质量要好得多,不容易卷口,使用更顺手。是不是在这样的边地,牧民也受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的影响?我一时找不到答案,也许他们压根就是从实用的层面上来考虑的。而我的理解是,钐镰就是特大号的镰刀,因为钐镰的刀杆长至少有两米,大多用笔直的松木干,中间绑着一个握手,拿在手里一掂,少说也有两三公斤沉。使用钐镰割草需要一定的技巧,抡起的镰刀舞出的弧线有两米多,随着镰刀呼呼的风响,一排齐腰的牧草倒地发出清脆的声音。那声音就像秋天宽阔的原野上一首美妙的音乐在奏鸣。
此刻,欣赏巴拉提的父亲抡起钐镰打草,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享受。别看他年龄快六十了,抡起钐镰来比我们这些小伙子有劲。只见他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左手握着钐镰把的一端,右手紧握钐镰把中间的横木,从右向左一扫,腰部灵活地一转,一个漂亮的孤线,“嚓”地一声,那些齐腰高的牧草就像设计好的股牌一般,轻快整齐地躺倒在地上。巴拉提的父亲总是一口气钐倒一大片。当我们有一次满心以为自己已经追上他的时候,却看见他坐在草丛中的一块石头上,正在用一块磨石,精心地磨着变钝了的镰刀刃。
巴拉提的父亲钐镰走过的地方,地上留下的草茬子又短又平,象铺着一块绒毯一样,再看我自己忙乎了半天留下的草茬,长短不齐,高低不平。老人指点我:“使用钐镰,左手的高低要平衡,不要高一下低一下,这样刀头才有准头;快到头的时候右手往下压着点,这样刀就不会飘,草茬才平。”我按照着老人的要领去做,草茬好看了些,可抡不了几下,右臂就酸疼得不行了。老人又指点我不要光用胳膊拉动刀杆,而要转动腰身带动胳膊一起用力,要用全身的力气把刀抡起来,这样才能有省劲、省力,打草的面积大,出草多。
老人说:“别看抡钐镰简单,里边的学问多着呐!”我认为老人讲的句句有理,只要认真领会照着去做,就会收益多多。
巴拉提的父亲挥舞着钐镰在草场上前行,就像一只雄鹰回旋在草海上。那些在钐镰下偃伏的草,铺开了一地诱人的金色的光焰。
而远处那些金色的草垛,就是草原深处站起的一座座丰收的里程碑,沿着牧民走过的道路,延伸到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