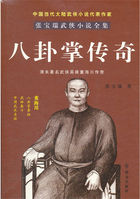这是个爽朗的秋日,温暖和煦得跟一年前他们定情时那天相仿,马丁把他写的《爱情诗集》读给露思听。像那次一样,他们也是骑车来到山间他们最喜爱的那座小山丘上。她不时发出欢呼,打断马丁的朗读,最后,他把末一页稿纸跟别的稿纸放在一起,等她发表意见。
她迟疑了一下,最后吞吞吐吐开了口,要把苛刻的想法用词语表达出来,她不禁感到为难。
“我觉得这些诗很美,美极了,可你不能把它们卖出去,不是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她说道,声音好像是在恳求。“你这样写作不切实际,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也许是出版市场的问题,结果你无法靠写作为生。亲爱的,请你别误解我的意思。你专门为我写了这些诗,让我真感到得意、骄傲、兴奋,要是没有这种感觉,我就算不上个真正的女人。可这些诗并不能为我们的婚姻铺平道路。你难道不明白吗,马丁?别把我看成个贪图金钱的人。让我焦虑的是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未来。我们公开彼此相爱已经有整整一年了,可我们结婚的日子仍然是那样渺茫。别把我这么谈论我们的婚姻看成过分露骨,因为它实在是个关系到我的心、我的一切的大事。既然你这么热衷于写作,为什么不考虑进报社工作呢?为什么不能成为个记者呢?至少可以暂时干一段呀?”
“那会破坏我的风格,”他回答时声音又低又单调。“你不知道我怎么为保持自己的风格而奋斗。”
“但是那些短篇小说呢?”她分辩道。“你把它们叫做糊口作品。你写了很多那种东西。你的风格给弄糟了吗?”
“不,那是两码事。那些短篇小说是在一天辛苦推敲,仔细研究之后,挤时间写的。然而一个记者的工作可是从早到晚一整天的苦营生,是他一天的头等大事。记者过的可是一种旋风般的生活,只有眼前而没有过去和将来,当然除了报导体裁之外根本没有文学风格可言。要是我现在撇开即将成形的风格去当个记者,那可简直是文学生命的自杀。实际上,每一个短篇小说,其中的每一个字眼,都与我自己的风格、我的自尊心和我对美的崇敬格格不入。跟你说吧,我对那种东西感到恶心。我是在犯罪。那些短篇小说卖不出去时,尽管我的衣服都进了当铺,我也暗自感到高兴。但是在写《爱情诗集》时,我感到的是欢乐!那是创作时感到的最崇高的喜悦!它是对一切牺牲的报偿。”
马丁并不知道,露思对这种“创作的喜悦”无法产生共鸣。她使用过这个词,而且他是从她的嘴里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她为了获得学士学位,在大学里从书本里学到过这个词,也研究过它;但是,她并没有独创性,也没有创造过,她那有教养的一切表现,无非是把别人的调子重弹一遍而已。
“难道那位编辑改动你的《大海抒情诗》毫无道理吗?”她问道。“要知道,一位编辑必然有当编辑的确定资格,否则他就当不成编辑。”
“这种说法是顽固的正统思想的翻版,”他压不住对编辑们的火气,开口说道。“但凡存在的东西,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最好的。只要一个东西能存在,就足以证明其存在的理由,请注意,这是指一般人不自觉地相信,不但现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存在的理由。他们会相信这种荒诞的东西当然是因为他们的无知,完全是威宁格尔所描绘的那种简单的思想方法。他们自以为有思想,然而这些实际上并没有思想的人却主宰着少数真正有思想的人。”
他停顿了一下,发现自己讲的东西露思根本不懂,不禁觉得难为情。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威宁格尔是谁,”她反驳道。“你讲的这些太笼统,我可听不懂。我说的是当编辑的资格问题……”
“让我告诉你吧,”他打断她说。“所有的编辑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主要的资格就是他们的失败经历。他们当不成作家。别以为他们不喜欢写作的乐趣,而喜欢编辑部的苦差事,喜欢做发行工作以及营业主任的奴隶。他们都试过写作,却失败了。这就是最严酷的矛盾所在。通往在文学上成名道路的每个入口都由这批失败者像看门狗一样把守着。那些编辑、副编辑、助理编辑,以及那些为杂志和书籍出版审稿的人们,大部分都想走写作道路,可全都是失败者。然而,审定有独创性的天才们写的稿子是否能发表的却是他们,他们是天底下最不适于做这份工作的人,他们失败的经历已经证明自己没有独创性,缺乏天赋的灵感,却坐在那里判断哪些能出版,哪些不能。除此之外,还有那帮评论家,也是同样的失败者。别以为他们没有做过写诗写小说的梦,他们做过,然而失败了。呕,一般的评论文章真比鱼肝油还让人恶心。你知道我对那些评论家和所谓的批评家是什么看法。伟大的批评家不是没有,但少得如划过夜空的流星。假如我当不成个作家,我准能当个合格的编辑,无论如何,干那个行当总可以混碗饭吃。”
露思的头脑很敏锐,当她从她爱人的论断中发现自相矛盾的地方时,就更加强了对他观点的反对意见。
“然而,马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假如真像你所说的那样,所有的门都关上了,那么伟大的作家怎么可能进去呢?”
“他们是靠做出普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才成功的,”他回答道。“他们的工作干得光彩夺目,把一切阻碍都烧成了灰烬。他们能创造奇迹,能战胜占绝对优势的对手。因为他们是英国作家卡莱尔笔下那些满身战伤却决不屈服的巨人。我就得这样干。非要干成不可能的事不可。”
“要是你失败了怎么办?你也得考虑我才成啊,马丁。”
“要是我失败了?”他打量着她,仿佛她说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接着,他的智慧又让他的眼睛变得炯炯有神。“要是我失败了,我就去做个编辑,你就会成为编辑太太。”
听了他这句笑话,她皱起了眉头,皱得那么可爱迷人,他忍不住把她搂在怀抱里亲吻她,直到把她亲得不再皱眉头。
“啊,够了,”她敦促道。她凭着意志的力量才让自己摆脱了他的魅力。“我跟父母谈过。以前我从没有那样跟父母顶过嘴。我硬逼着他们听我说,真是不孝。你知道,他们对你都表示不赞成;可我一遍又一遍向他们保证说,我对你的爱情忠贞不二,后来,父亲总算答应说,只要你愿意,可以马上进他的事务所工作。接着,他还主动提出说,一开始就可以付给你足够的薪水,好让我们结婚,并且找上一座小房子住。我认为他这么做实在太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马丁心中感到沉痛的失望,不由自主伸手去掏口袋里的烟草和卷烟纸(他现在并不随身携带了),嘴里还含糊地说着点什么,露思接着说道:
“跟你说实话吧,你听了可别生气,我告诉你是为了让你知道他对你的看法,他不赞成你那种过激的观点,而且他认为你懒惰。当然我知道你一点儿也不懒。我知道你工作得十分辛苦。”
但是到底有多辛苦,就连她也不清楚,马丁这么想着。
“那么,”他说道,“我的观点怎么样?你也觉得太过激吗?”
他盯住她的眼睛,等待她的回答。
“我觉得,嗯,你的观点让人听了感到不安。”她回答道。
他的问题得到了回答,结果他感到十分压抑,生活好像变成了一片灰蒙蒙的迷雾,使他忘记了她试探性地提出的要他去工作的建议。而她呢,既然已经壮着胆子提出建议,也就愿意等到下一次重新提出时再得到答复。
她并没有等待多久。马丁也向她提出一个问题。他想知道她对自己有多大信心,结果不出一个星期,两人的问题都有了答案。马丁把自己写的《太阳的耻辱》读给她听,使两个问题都得到了答案。
“你干吗不去当个记者?”等他读完,她问道。“你这么喜欢写作,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你可以在记者生涯中发迹成名的。了不起的特派记者多得是。他们的薪水高得很,而且他们的工作领域是整个世界。他们会被派到各种地方去,像史坦莱那样到非洲腹地去,或者去访问教皇,或者去神秘的西藏去探险。”
“这么说,你不喜欢我这篇文章吗?”他反问道。“你认为我在新闻界有希望,在文学界倒不行,对吗?”
“不,不,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听起来很不错。然而我恐怕读者无法理解它。至少我听不懂。听起来好极了,可我不懂。那些科学术语太深奥了。你属于极端派,亲爱的,你自己也知道的,你自以为浅显的东西,别人可能并不理解。”
“恐怕让你感到费解的是那些哲学术语吧。”他只能这么说。他刚刚读给她听的这篇作品表达的是他最成熟的思想,他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可她的意见仿佛向他浇了一瓢冷水。
“且不说文章写得有多糟,”他追问道,“难道你连一点儿好的地方都没有发现吗?我是说,在思想方面。”
她摇了摇头。
“没发现,它跟我读过的任何东西都不同。我读过梅特林克的作品,也理解他的……”
“他的神秘主义,你理解吗?”马丁脱口说道。
“是的,可你说你这篇作品是对他的攻击,这我可不懂。当然,说到独创性……”
他作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打断她的话,可他并没有说什么。忽然,他发现她在讲话,而且她已经讲了好一会儿了。
“不管怎么说,你一直以写作为乐,”她这么说道。“你玩得够长了。现在该认真对待生活了,是我们俩的生活啊,马丁。迄今为止你一直仅仅考虑你自己。”
“你想要我去工作?”他问道。
“是的。父亲提出……”
“我明白的,”他打断她说。“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否对我失去了信心?”
她默默握住他的手,目光中充满了朦胧。
“我对你的写作失去了信心,亲爱的。”她低声承认道。
“你读过我的很多东西,”他卤莽地继续说。“你觉得那些作品怎么样?完全没有希望吗?跟别人的作品比较起来怎么样?”
“但是人家的东西有人要,可你的……就没人要。”
“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觉得我根本不适于干文学这一行吗?”
“好吧,我回答你的问题,”她鼓起勇气说。“我认为你天生不是搞写作的。原谅我,亲爱的。你逼得我不得不这么说,你知道我比你更懂文学。”
“是的,你是文学学士,”他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你应当更懂。”
“但是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他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停顿的时间长得让两人都感到难受。“我知道自己的能力。谁也不如我对自己更加了解。我知道我会成功。我不会被压垮。我有写诗、写小说和写论文的激情。我不要求你对此有什么信心。不要求你对我和我的写作有信心。我对你的要求仅仅是爱情和你对我们爱情的信心。”
“一年前,我请求你等两年。现在还剩下一年。可我确实相信,而且我可以凭我的名誉和心灵来担保,不出一年,我准能成功。你还记得很久以前,你对我说过,要当个作家就得有个学徒期。啊,我现在已经出师了。我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尽量把它压缩到最短最短。有你在等待我,我从来没有放松过。你知道吗,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平静的睡眠’了。仿佛几百万年前,我知道什么叫做‘睡个够’什么叫做‘从梦乡中自然醒来’。现在我总是被闹钟吵醒。不论我早一点睡,还是迟一点睡,我都要把闹钟随之拨得早些或迟些;我每天最后一个清醒的行动就是拨闹钟和关灯。”
“当我感到困倦时,我就把手头费解的书换成一本内容轻松的。当我读这种书也打起磕睡来时,我就用拳头砸自己的脑袋,好把磕睡赶跑。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过一个怕睡觉的人。那个故事是基普林写的。那个人在身边安装了一个马刺,只要他一打磕睡,他赤裸的身体就会碰在那些铁刺上。我也这么做的。我看着时钟,不到午夜一两点钟或者三点钟就决不拿走马刺。这马刺每晚在规定时间之内能让我一直醒着。它已经陪伴了我好几个月啦。我为了拼命工作,每晚要是能睡上五个半钟头,就算是奢侈了。现在我每晚仅睡四个钟头。我磕睡得要命。有时,我睡得太少,感到头晕眼花,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的安息对我简直是个诱惑,在这种时候,我的脑子里常常想着拉菲罗的那几句诗:
静静大海深几寻,
芸芸众生睡何沉;
轻轻一步解千愁,
汩汩泡沫藏万恨。
“当然,这纯粹是一派胡言。是由于神经过于紧张,脑子过度劳累才引起的。然而,问题在于: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为了你。为了缩短我的学徒期。为了迫使成功早一天到来。现在,我的学徒期已经结束。我对自己的能力完全了解。我可以发誓说,我每个月学到的东西比一个大学生一年学到的都多。告诉你吧,我说的没错。要不是我这么想要你理解,我绝不会告诉你的。我绝对不是在吹牛。我是根据读过的书来衡量自己的。你的兄弟们跟今天的我和我在他们熟睡之际学到的知识相比之下,都是些无知的野蛮人。很久以前,我渴望成名。可现在我把名声看得很淡,我想得到的只有你。我想得到你的欲望比吃饭、穿衣以及获得名声都更加迫切。我梦想着把脑袋枕在你的胸脯上,美美睡它一个世纪。不出一年,这个梦想准能实现。”
他的力量像浪潮般一阵阵冲击着她,他的力量跟她的力量对抗愈猛烈,她就愈感觉到他的吸引力。她从来就能感觉到他汹涌澎湃的力量,现在这力量使他的声音热情奔放,使他的眼睛熠熠生辉,使他全身都放射出精力和智力的光彩。在这一瞬间,她发觉自己的信心龟裂了,透过裂缝,她瞥见了马丁·伊德光彩照人而又无懈可击的真实面貌;正如训兽师有时不免会怀疑自己的能力一样,这时她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力量,不知道是否能驾驭这个人的野性。
“还有一点,”他起劲地继续说道。“你爱我。可你为什么会爱上我呢?我内心中有一股力量,迫使我非写不可,而使你爱上我的不正是这股力量吗?你爱我是因为我与你熟悉的那些人,或者说你本可能爱上的人有些不同。我生来不是做文书工作的料,不会当会计,不善于为生意上的琐事争个高低,不配在法庭上喋喋不休地辩论。假如要我去做那种事,要我干那批人的工作,呼吸他们呼吸着的空气,形成他们已经形成的观点,你就毁了我这一点不同于别人的特性,毁了我,毁了你心爱的东西了。我的写作欲望是我最有力的东西。假如我不过是个平庸之徒,我也不会渴望写作,你也就不会渴望跟我结婚了。”
“可你忘记了一点,”她打断他。她灵敏的头脑里闪出个可类比的东西。“有些怪僻的发明家,不顾家人饿着肚子,一味追求发明诸如永动机之类的东西。他们的妻子无疑爱着他们,而且跟着他们受苦,为他们的动机而受苦,不过并不是为他们的永动机着迷,而是尽管他们着了迷,她们仍然爱着他们。”
“不错,”他回答道。“但是有些发明家并不是怪僻的,他们一边饿着肚子,一边拼命工作,盼望着发明些实用的东西;有时,他们能够成功,这是有据可查的。我当然不想做那种不可能的事……”
“你不是说过要‘做出不可能的事’吗?”她打断他说。
“那是打个比方。我想做到以前有人做到过的事:写作,靠写作生活。”
她的沉默鼓励他继续讲下去。
“难道你认为我的目标是个像永动机一样的幻想?”他追问道。她紧紧握着他的手,这就是他要找的答案,就像个母亲捏住孩子的手对孩子所受的委曲表示怜悯一样,她这时正是把他看作个受了委曲的孩子,这个走火入魔的男人竟然非要干成不可能的事。
在谈话结束前,她警告他说,她的父母都反对他这么做。
“可你爱着我,不是吗?”他问道。
“我爱你!我爱你!”她喊道。
“我爱的是你,不是他们,他们做的一切都不会伤害我。”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胜利。“我相信你的爱,不怕他们跟我作对。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能出岔子,只有爱情是可靠的。除非爱情本身就很虚弱,中途晕倒或者跌跌撞撞,否则它不会出岔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