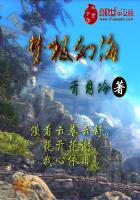那时候,我刚好从学校回到家里,两兄妹都闲着,怎么办呢,任何开心的事情都不能使我开心。家里的特困环境迫使我出去谋生。干什么呢,社会上的失学、失业的青年一大群,那时所谓出身好的也没有事做,何况我这个“黑五类”的子女!即便有天大的本事,就算他们点错了名,工作也不可能轮到我的头上来。心想只有去推板车罢了,过去年纪小,拉车人不雇我,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健康,一定会有人雇我吧!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身穿一套劳动服,脚穿一双破力士鞋,头戴一顶旧草帽,从家里走到一师范旁边一条叫由义巷子的巷口上,我突然停住了脚步,因为走出巷口,就是书院路大马路,马路上都是来来往往的搬运工人拉着木板车行驶。这时候,好像大家都在看着我,笑我,议论我,过去在学校里拔尖的出席全长沙市的“三丰收”学生,今天怎么会出来推板车呀!那时候推板车的都是男孩、妇女、老头或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力,根本没有年轻姑娘去干这种粗笨和低贱的苦力活。我街待业女青年共有40名,没有人去干这个活。我脸上感到一阵发热,心里火辣辣的,片刻,满脸通红,害起羞来,用草帽盖住自己那害羞的脸,不好意思地往回走了几步,我又停住脚,这时的思想斗争相当激烈,为生活所逼,哪能光顾自己的面子呢!就这样反复三次来回,最后,我才鼓足了勇气冲出了巷口,来到火车南站,很快就被一个拖煤到雨花亭长沙锅炉厂去的车主雇上了。
从火车南站到那里,全是上坡路,大约有三公里,推车的时候,我的力气很大,拉车人的背马上直了起来,可是我被累得汗流浃背,到达目的地时,喉管干得好像会裂开似的。车主给了我1角5分钱,这时我才知道价钱。往回走的路上,看见路边摆了许多茶摊,1分钱可以买1杯,我舍不得用这汗水换来的钱去买茶喝,直奔家里,到屋就抱起茶罐像牛喝水一样咕噜咕噜一下子将罐里的开水全部喝光了。
母亲见我满脸通红,全身汗湿,立即拿来扇子,帮我煽风,我高兴地将那一角五分钱交给了母亲,并对她说:“今天是个良好的开端,明天再去。”母亲接着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第二天,我又来到火车南站找车主。为了找到一个车主,至少要问几个拖车人,他要从头到脚地打量一遍,看你是否健康,有无力气,然后再告诉你去什么地方,问你要多少钱,由自己喊个价,他认为合适,这笔生意才算成功。昨天因为我是第一次,根本没有与他谈这些,他要我开个价,我说随他给钱,心想只要他同意雇我就已经满足了。要是我是个男孩子,昨天那么远的路程至少应给二角伍分钱。
我最害怕的事是跟车主讨价还价,他们都是大男人,我在他们面前,说不上两句话,脸就红了。
大弟那时候也长到快12岁了,后来每天我带着他,叫他出面谈生意,两个人推一部车,只要一个人的钱,这是个好办法,天天都有车主雇我们。
连续推了半个月的板车后,我慢慢地认识了很多人,交了一些朋友,有个姓王的搬运工人,每天固定雇我和弟弟推他的板车。他全月都包我们,不管一天推多少车,也不管天晴和落雨,除了两人午餐他包干外,每月给我们30元工资。第二人拖什么货,去什么地方,晚上由弟弟到他们常坐的茶馆里听消息。这样既保证了我每天的收入,又不担心找雇主的困难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一句形容行旅艰难的诗句,用来形容我和弟弟去干推板车的心情,倒有点相似。我的一家在生活道路上十分艰难的时候,我们这对无助的少年,勇敢地迈进社会,去干推车的苦活,能够增加收入,对父母来说也不无小补。
“推板车”究竟是一回什么事,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见过,当然感到陌生,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记上一笔,也算是历史吧!
一句话,推板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由于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谈、天天讲,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人妖颠倒,黑白混淆,国家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作为省会城市长沙,经济滞后,交通运输很不发达,谈不上现代化,短途运输全靠原始的人力搬运。当时,市内数以千计的搬运工人,全靠木板车和胶轮板车运货。工人的劳动所得,有55%被抽走,所剩无几,不得不靠超载重拖增加收入。当时规定一车的载重量不得超过500至600公斤,一般都拉上一吨以上货物。载重量超过一倍,付出的劳动力也必须相应增加。拉车走平路,一个人还可对付;遇上陡坡陡岭,搬运工人就死猴子了,何况城南一带没有平路,只能望岭兴叹。这时就必须有辅助劳动力帮助推车上坡。工人家里有子女或老婆的,就让他(她)们跟在车后跑;没有人跟车帮忙的,就只好临时雇人帮忙了。因此,推板车就是那种经济落后时代的产物。现在看来,推板车也的确是穷苦劳动者的劳动互助、经济互补的一种临时工种。几十年后的今天,由于邓小平拨乱反正,国家经济日渐发展,汽车运输逐渐代替了人力搬运,胶轮板车被淘汰了。“推板车”也变成了历史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