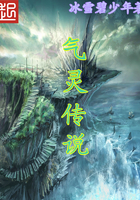1930年12月,驻扎富田的红二十军不满肃清“AB团”运动的扩大化,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把部队拉过赣江,进入永新、永阳一带。红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
毛泽东正掌握着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权和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的指挥权。
那些投机革命的,个人和家庭利益被触动的,无辜受害的,都把不满情绪对准了毛泽东。
同时,由于负责红二十军肃反的李韶九,在反“AB团”时的扩大化做法,也加剧了红军内部人人自危的情绪。
敌人想利用这种矛盾来拔掉他们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一起谋杀毛泽东的阴谋就在此时悄悄地紧张进行。
由赣西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的红二十军,富农子弟多,读过书的人也多,连以上干部差不多都涉嫌“AB团”而受肃反运动的冲击。
对于苏区的肃反扩大化,毛泽东虽然不无责任,但是下面的很多过火做法,他其实并不知情。然而红军中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认为,这一切全怪那个湖南人——毛泽东。如今,他大权在握,竟然派兵逮捕了赣西南特委的主要负责人,把他们关在富田镇的监狱里……
红二十军的军官们认为,毛泽东这是先把赣西南特委的领导搞掉,接着就会对红二十军的军官们下手。因此,一些人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杀到瑞金,拼个你死我活。
1930年12月8日的中午,红二十军中的一个营教导员接到一份没有署名的密令,命他当晚率部袭击富田,解救赣西南特委领导,并同时派人速奔瑞金刺杀毛泽东,上级将配合他们的行动。
这密令完全迎合了这个营教导员及其一伙的心绪,尽管没有署名,他们也知道是来自何处,所以乐意执行。
接到密令的营教导员,名叫赖柞焘,家有50亩田地,20间青瓦房,属名符其实的富农家庭。他从小读书,还到苏联留过学。从苏留学回来半年多就当上了营教导员,上级已透出信息,要提升他当团政委。
赖柞焘投身革命队伍,也是为了借助这一条船,达到实现他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彼岸。可是,一场清“AB团”的运动,搅了他的好梦。有人私下告诉他,已把他定为“AB团”骨干分子了,因此,不仅没有当成团政委,而且,要不是军部头头硬顶住,说不定他也成了黄泉路上的新鬼。为此,他心里长出了牙,恨不得活吞了毛泽东。苍蝇也要先找准烂疮才下咀。赖柞焘能接到这份密令,要他去执行那种“特殊使命”,也就十分自然了。
赖柞焘接到密令后,感到憋在胸中的怒气终于可以焚烧了。他激动,他高兴,立即马不停蹄地找来同伙们进行秘密的紧急传达布置,他充分发挥那沾过洋墨水的三寸不烂之舌,唾沫横飞地进行了振振有词的鼓动,并拍着胸脯发誓,要亲自率队打到富田镇劫狱。但是,赖柞焘一想毛泽东的足智多谋,想到毛泽东在苏区、在红军中的地位和威望,想到邓发领导下的保卫人员的利害,又让他那沸腾的血浆,一下降到了冰点。冷汗浸湿了内衣的寒意刺激他打了几个振幅很大的寒战,使他倒抽了几口冷气,心想,行刺毛泽东非同儿戏!
赖柞焘认为,选准直接执行任务的人最重要。于是,他立即把全营几百号人在心里过了一遍筛子——进行了逐个审查:张大个胆子大,心大粗;李精灵枪法好,胆子小;赵白脸是马尾巴穿豆腐,靠不住;禹二狗有家小,必然顾虑多……全营大多数人在他的“筛子”上一过,几乎都落选了。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想来想去,他想到自己的表弟。
他的表弟小名叫满古子。
这个满古子,家里也是富农,参军前在家里是教书先生。
满古子的父亲是个阴阳八卦先生,一个偶然机会他见到了毛泽东,按照阴阳八卦和面相一比一算,就断定毛泽东将来要坐天下。于是,认真地动员儿子去参军,跟着毛泽东打天下,将来好稳坐江山,满古子听了父亲的话,丢掉教书的饭碗,报名参加红军。
满古子读过书,机灵,但胆子较小。第一次打仗被吓得往后跑,连长用枪口抵住他的胸膛,要毙了他,他的表哥赖柞焘救了他一条小命。后来,仗打得多了,枪法也好,他的胆子也就渐渐地大了。赖柞焘见他为人机警,就把他调到侦察排当班长。如此安排,一是因为亲戚关系,关照他;二是随时都可以派上用场,对自己有用。
赖柞焘曾多次私下给满古子打过气许过愿:“满古子,争口气,好好干,我当上团政委,就提你当连长。”
满古子也多次拍着胸脯表示:“表哥,我保证听你的!你叫我往东,我决不往西,你叫我死,我决不活!”他知道表哥喜欢听话并忠于他的人,也明白“水帮船,船帮水,水涨船高”的道理。为他能出人头地,他当然乐意跟着自己的表哥干。
赖柞焘想到满古子后,很为自己的深谋远虑得意,并做了个右手握拳,力度适中地击在左手掌心里的动作。他脸露微笑,轻蔑地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呀!让满古子行刺毛泽东,无论怎样都是上策:成了,他们同归西天,互无怨言;若是满古子被捕,他可表白自己与此事无关,并来个大义灭亲,为自己晋升多铺几块砖;若是满古子因此先送了命,他则可继续混迹革命队伍中。
经过反复比较,再三权衡,赖柞焘认为满古子符合执行行刺最重要的三个条件是:首先是自己人,靠得住;其次是练过侦察打过仗,人机灵;第三有突击的特长——枪法好。行刺毛泽东的执行人选就这样敲定了。
接着,赖柞焘找来满古子,单独作了详详细细的交待。在精神上给他鼓了劲壮了胆,在物资上给了他最优厚的保证,在仕途上反反复复给他许了愿。最后,他给了满古子六个字:“不成功,便成仁!”
满古子受命后,心里象揣了个小兔子,蹦哒声清晰可闻。这是一项特殊任务,他既兴奋,又紧张,也害怕,即便有他的整个侦察班配合他,还是热汗冷汗交替着往外冒。但是想到表哥平时对他庇护,想到反富农触及到他家的利益,想到清“AB团”又会涉嫌自己……他从口里溅出几滴自我安慰的墨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经险中险,做不得人上人!”
时间紧迫,迟疑不得。满古子如今在侦察班讲话。他曾经教过书,却依然保留了纨绔子弟的劣迹,加上“特急使命”令他激动,尽管他装模作样,故作镇静,讲起话来还是离不开“脏”字。他佯咳几声,开口了:“妈那个×的,大家听着,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今天,我们执行的,是一次最特殊的重要任务,也许一辈子就碰上这么一次。因此,也最光荣……大家不准再打听了,这是我们军人,特别是我们侦察兵要做到的。”
满古子粗粗的喘了一口气,接着说:“妈那个×的,老子在前面打头阵,大家配合我。我的枪没响,大家就是死了,也不准开枪;我的枪响了,大家尽管打他个痛快。不准乱来,妈那个×的,哪个敢乱来,别怪老子不客气!”最后,他提高了调门,也把他表哥甩给他的六个字甩给大家:“今天晚上,妈那个×的,大家要来他个‘不成功,便成仁’。”
准备停当,满古子带着侦察班,从驻地东固村出发,急急赶到了目的地。在夜幕降临时分,他们化装混进了红都瑞金城,顺着脑瓜里记下的路线,寻找毛泽东的驻地,找到了预定的地点,埋伏好。
毛泽东住在一个财主的房子里,这是瑞金城最好的一座庭院,围墙不高。满古子用手势召来一个兵,两人一起顺围墙察看一圈后,指挥大家在前后门分兵埋伏好。
这是1930年12月8日的寒冬之夜,刺杀就要真正开始了。满古子脱下身上的蓝灰布棉袄,顺着纽扣对折起来,铺在围墙顶上,再把别在腹前的手枪往腰间挪了挪,顺手又紧了紧腰带。然后,他两手按着棉衣,双脚轻轻向上一纵,全身便撑在围墙顶上,接着悄然落到院内。
满古子迅速隐藏在树影里,细细观察:后窗有灯光,却没有身影。此时,他从受命后一直在强力压抑着的心脏,终于失去了控制,象被惊吓的兔子狂跳起来,口里断断续续地不由自主地轻轻念叨“妈那个×的,目标在吗?如果不在,今晚等于白干,若因此走漏风声,后果将不堪设想……”
“干掉毛泽东!”执行这种特殊任务,无论再胆大妄为的人,也会浑身发抖的,何况满古子是深知毛泽东神威的侦察兵呢?不过,他想到:反富农运动中,自己家里30亩地全被没收了;清“AB团”把表哥定为“AB团”骨干,肯定也会连上自己;自己丢掉教书的饭碗,提着脑袋来参军打伏,这么久了,不但没有得到封赏,反而连家里的田地也被革掉了,弄不好还会革掉自己的命。这些,都是毛泽东造成的。表哥说得对:“不将毛泽东干掉,就没有我们的出头之日。”
恐惧压下去了,仇恨鼓起来了。满古子在树影底下静静地稳了一阵神后,抽出枪,压上一梭子弹,再插到腰带上,瞪着两眼,四处观察。
初冬之夜,后院静悄悄的。
满古子窜出树影,潜身在屋檐下。他贴着墙根碎步移近窗前,紧紧靠着窗户,朝房间里看:一个印在墙上的巨大身影,震人心魄,微微有些摆动。他心中一阵狂喜:“没错,正是他——毛泽东!”
满古子猫下腰,快速从窗台下踅过去,从窗户的另一侧再观察房内,想看个一清二楚,以便做到万无一失。啊,她也在。年轻漂亮、在红军中很有名望的女英雄贺子珍。
她皮肤白嫩,身材苗条,却能征惯战,文武双全。有一次,她随朱德和毛泽东去侦察敌情时遭到伏击,随行的警卫慌了手脚,连忙撤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贺子珍却快跑几步纵身一跃,抽出双枪立在一座小桥上厉声喝道:“谁跑我毙了谁!你们在这顶住!我去引开敌人!”说着,转头飞身上马,甩开双枪边射击边冲向敌阵,把敌人吓呆了。贺子珍撂倒了几个白狗子,然后拨转马头朝斜刺里冲去,吸引敌人向她追击,从而使朱德和毛泽东安全脱了险。
此刻,这位威振敌胆的女英雄,正聚精会神地埋头在补毛泽东的大挎包。挎包上有一个破洞,贺子珍用旧布补好,再巧妙地用红丝线在补疤上镶一颗象征革命与希望的神圣标志——红五星。她一边缝一边看,脸上露出甜甜的微笑,还不时给毛泽东送去一个爱抚的眼波……真是一个心灵手巧的柔情女子呀!
满古子尽管重任在身,还是把贺子珍从头到脚细细地搜索了一遍,难以挪开那贪婪的眼光:“这个湖南蛮子真福气,好事全让他小子沾上了!”他极不情愿地从贺子珍身上抽回搀眼,把目光狠狠地对准了毛泽东。
此时的毛泽东,一年多以前骨瘦如柴,长发蓬乱的模样,已不存在,苍白的脸已经稍稍红润,并有了一点光泽;长发也二一添作五地由中间向两边整齐地梳理分开着。他,宽阔的额头,淡淡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目光,均匀升高的鼻梁,丰满红润的嘴唇,外圆内方的下巴中间略略偏左的那颗痣,“地阔方圆,两耳垂珠,明眸朗目,隆准生乐,日月争辉”的帝王之相。难怪满古子那摆卦摊的父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暗暗惊呼:“那姓毛的了不得,是真龙天子降世啦!”
可是,满古子胸中的邪火上窜。他拨出手枪,向早已观察好的制高点快步蛇行转移。此处,杂树丛生,密密麻麻,既能隐蔽自己,又能看清毛泽东,是最理想的射击点。
初冬的深夜,冷清清的。此时,人们早已钻进被窝,没有闲杂人员,没有流动的哨兵。虽有门岗在执勤,但只要他满古子的枪一响,早已埋伏好的弟兄们,是完全对付得了这几个门岗的。关键就看他这第一枪了。
眼睛瞪得大大的冬月,看到这一切,也惊得似乎气不敢出,步不敢迈了。
满古子的枪法是手屈一指的。表哥曾多次私下给他讲了在军队里要出人头地的秘诀:枪是战士的第二条命,谁枪法好谁就能吹牛皮称天下。所以,满古子到侦察排后,除了执行任务或偶尔去过过色瘾,其余时间几乎都用于手枪射击。因此,对香火、飞鸟、飘飞物,他能在奔跑或翻滚中抬手命中目标。他的勇气,80%也是来自他手中的枪。
满古子举起手枪,左眼微眯,指向那颗使敌人害怕的头颅。打手枪,平时他根本不瞄准,随手一挥,枪响中的。可是,今晚非同寻常,稍有偏差,后果不堪设想。可他越想打好,就越是紧张。狂跳的心总是镇静不下来,总感到枪柄冷冰冰地打滑,举枪的手颤抖不停。无奈,他只好放下枪,张开口轻轻地长长地尽力地做了几次深呼吸。
此时,满古子见贺子珍站起来,把修补好的大包,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拿起挎包,一边欣赏一边夸妻子心灵手巧:“子珍哟,你咯样能干,我都怕配不上你!”
“你又怄我。”贺子珍娇嗔地含羞一笑。她把毛泽东的“文房四宝”有秩序地放回挎包的各层里。
“嚯,我的文房四宝又回新家罗。”毛泽东高兴地说。
“是老家!”贺子珍纠正道:“这里原来就是人家的房间嘛!”
毛泽东笑开了:“房间?嗬嗬,真有味。”他一手叉腰,一手扶住贺子珍的肩膀说:“土地回老家,房子归原主。农民开荒没有田耕,泥水匠砌屋没有房住,土地革命不搞何事要得?”
毛泽东止住笑,抬手拍拍桌子上的一本小册子说:“你看,这是上个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苏维埃区域土地农民问题议决案草案》。连共产国际都肯定了‘坚决为着平分土地,首先就是保证贫农、雇农、革命战士的利益,而实行坚决不可调和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主要的农民群众反对破坏农民土地革命的富农。党在这些问题上的一切消极行为,必然是放弃无产阶级的独立地位,向富农投降’”。
满古子听到这里,心里更凉了:“呵,原来是共产国际指示要反富农的!就算杀了毛泽东,恐怕自己家里的土地还是要不回来。听说上海中央局有一班子28个半留苏布尔什维克,比毛泽东还要过激些。那班人正在苏联支持下夺李立三的权,并且很快就要到江西苏区来。等李立三一下台,赣西南特委和红二十军的大小干部大部分都要完蛋。”
满古子握枪的手越发瘫软无力了。他懊悔当初不该听老爸子的话,来当红军自找苦吃。即使在家教不成书,把地出租了,到白区找点事做,也比在这里被当作革命对象强。
正当满古子在沉吟自责时,忽然听到卫兵报告:“首长,有一位老人,非见您不可,说是有重要情况。”
“请他进来。”毛泽东给卫兵下令,起身踱步,消失在满古子的视线之外。
“完了!满古子左手在自己的大腿上击了一拳,”机会失去了!他凭着当侦察兵的经验,这种任务完不成,回去是交不了差的。没有别的路,只好耐着性子等下一个机会。只要目标再出现,他将甩手就是一枪,决不再犹豫。
不一会儿,窗户上人影晃动,他好欢喜:“机会来了。”
“老人家,里面请。”静静的夜里,毛泽东和蔼的声音也显得更加清晰。
“毛委员请……”
话音熟悉。这不是老爸在和毛泽东对话吗?唉!他怎会……我不该……唉!
因为这是一次最特殊的任务,稍有不慎,将有去无回。所以,满古子在行前专门去城郊沙洲见了摆卦摊的老爸子一面,表示最后别离。言谈中,他把这次特殊任务悄悄地全部告诉了老爸子。他老人家听了连连摇头跺脚:“杀不得呀!毛泽东是真龙天子,刀枪不入。你兔崽子会白送死。”老爸子把门闩起来,死活不让他走。
满古子拗不过,眉头一皱,来了一计,一边故意和老人家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很快就把父亲灌醉了。然后把老人家反锁在家里,急急忙忙赶进城和弟兄们会合。没料到,老爸子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赶来向毛泽东报信了。
“事不迟宜,赶快动手!”满古子催促着自己,双手举起手枪,瞄准窗口,紧张得眼冒金星。机会终于来了,毛泽东出现在满古子能够射击的范围内。可是,毛泽东是弯腰搀扶老人家进来的,老人却又偏偏走在靠窗的一边,成了毛泽东的保护墙。
真是急死人气死人。满古子的头上渗出了点点虚汗,他的牙齿咬得格格响,却不得不强压怒火又一次收回枪。
毛泽东坐在原来的凳子上,招呼夜访老人:“老人家,请坐。”
满古子一听,心里好生高兴:老爸比毛泽东矮,只要老爸子一坐下,毛泽东的头部就会暴露在枪口下。可要命的是,老爸子就是不肯坐下,反而尽量挺直腰板,急促地大声向毛泽东报告:“毛委员,有人要谋反……已有几千人打富田去了。”
毛泽东镇定自如,安坐不动,不紧不慢地说:“老人家,您坐下,慢慢说。”
“我不……不坐”老人根本不管儿子藏在杂树丛中恨得咬牙切齿,依然挺着胸脯木桩似的站着,声音也超常地又高又急:“毛委员您是真龙天子,您不能让别人夺您的江山……”老人家谈着谈着,算命卜卦的那一套也搬出来了。
毛泽东听了,不但没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幽默地说:“多谢仙人指点。”他略停一下,语调也变得庄重起来:“不过,请老人家理解、体谅,我们共产党人不信神仙不信皇帝,只信自己的骨头硬。”
“信不信由您!”老人家生起气来了,酒也清醒了几分:“我不是酒后胡言。毛委员,您还是赶快升帐点兵吧……”
“请老人家放心,我们的部队已经派出,现在快到富田镇了。叛变的人是成不了气候的!”
听到这里,满古子象全身掉在冰窟里,凉透了。看来,毛泽东确是真龙天子,料事如神,谁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他明白,老爸那些话是故意讲给儿子听的,自己今晚肯定是伤不到毛泽东的一根汗毛了。与其在这里白白等死,不如赶快离开这里,另谋他计?他终于放弃了一切努力,转身潜出杂树群,快速溜到墙根,纵身上墙,“嘭”的一声跳落院外。
“谁?站住!”邓发安置在毛泽东住处附近的暗哨听到响声后大喝一声,接着几个敏捷的身影顺着满古子的脚步声追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