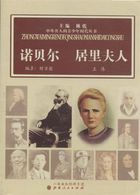“八一”起义的枪声,划破夜空,传遍神州大地。在张发奎军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听到起义的消息,高兴极了。可没料到,起义队伍没过多久就撤离了南昌,朝广东潮汕方向开去了。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听到南昌起义中自己的部属贺龙、叶挺的部队离他远去的消息后,非常愤怒。他马上召集二方面军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如何解决贺龙、叶挺率部离去的事。会上,气氛非常紧张,许多军官都主张派兵尾追,捉拿贺龙和叶挺。偏偏在这个时候,张发奎又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的命令,要张发奎立即追赶贺龙、叶挺部队,这无疑是给张发奎火上加油。他终于大发雷霆:“贺龙、叶挺这两个家伙,完全不顾公谊私情。你不仁我也不义,我就是要追着你们的屁股打!”他正要下达命令,这时,在他身旁一直沉默着的叶剑英参座说话了。
叶剑英向张发奎说:“总指挥,依我之见,我们还是不追贺龙、叶挺为好。”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投向叶剑英。他不慌不忙地讲出“力主不追”的道理来:“总指挥不是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总理的革命义旗吗?我看,目前正是好时机。你想想看,广东现在是李济深的地盘。现在,我们放贺龙、叶挺的部队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时,就会请我们到广州相助。这时我军就可名正言顺地以援军名义开进广州。这样比跟着贺龙、叶挺的屁股打,造成两败俱伤要好得多。如果我们现在派重兵尾追贺龙、叶挺,白白浪费兵力不说,也不一定就追得上他们,就算追上并捉住他们,而我们仍无立足的地盘,又怎么谈得上北伐统一呢?”
张发奎一听,觉得叶参座的话也很有道理,气消了许多。他原来奉命“东征讨蒋”也不是他本人愿意干的事,他一直想干的,就是重返广东,扩充实力。于是,他就采纳了叶参座的主张,放弃了尾追贺龙、叶挺的想法。为了避免别人说他通共,他便虚张声势地派小部队追了上去。
这样,南昌起义军就在没有多少追兵的情况下,顺利地朝南而去。中国共产党正是靠这些武装起义的“火种”,让它们熊熊燃烧,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势。
1927年8月3日至5日,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先后撤离南昌。陈赓调到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任营长。军长是贺龙,师长是周逸群。
陈赓跟部队一起向广东进发。山路崎岖、酷暑难当。第三师的新兵没有尝过这种滋味,一路走,一路把毯子、衣物甚至子弹丢得到处都是。
起义军手里拿的纸票子,老百姓不肯开门,沿途连一个人都看不到。有些司务长、副官及学生兵,腹内饥饿的时候就将老百姓的瓜果鸡鸭拿来充饥,因此更惹起老百姓的惶恐与讨厌,所以后来每到一个地方,简直是十室十空了……
这种现象过了两三天,贺龙异常愤怒,当场枪毙了一个捉鸡吃的司务长,并宣布如有发现无故鸣枪及乱入民室者,就地枪毙,于是军纪渐渐地好了,后来发了几块现洋,稳住了军心。
陈赓营里的士兵都是东江、湘南一带的农民子弟,士气高,战斗力强。他们颈上飘着红带子,背后挂着斗笠。他们拍打着磨得发亮的枪托,瞪着眼睛,等待着营长的命令。
8月24日,第三师一到会昌附近就和敌人接上了火。陈赓带领第一营,由正面发起攻击,一口气攻下三个山包。但是担任两翼攻击的部队走错了路,没有按时赶到,便使突击的陈赓营变成了孤军深入。敌钱大钧师的炮兵开始轰击,四个团的兵力朝阵地上压来。敌兵怪声嚎叫,子弹掀起青草和泥屑,在身边乱飞。双方交战的中下级军官,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许多还是儿时朋友。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浑名对骂。那边骂这边:“共党为什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面疯狂地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陈赓目击这种情形也为之心酸。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士兵往前冲锋。牺牲者的尸体布满了山坡,血流成河。从上午8时一直打到中午,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陈赓焦急地跺脚,咯吱吱地咬着牙齿,只好朝传令兵挥挥手:“通知全营,撤!”
撤退时,陈赓走在最后。他弯腰冲出树丛,开始奔跑。他心想,最好的办法是先照直朝前跑,等敌人调转枪口对准他的时候,再突然卧倒。他看不见后面,完全凭经验和运气。
他跑出十几步以后,就猛然闪向一边,再跑出五六步,又拐向右侧。这时候,连珠炮般的子弹开始在他四周噼噼啪啪地爆响,好像有人在贴着耳鼓击掌,他一边左右躲闪,一边拐着“之”字形奔跑,时而扑倒在地,时而打着滚,然后跳起来往前猛冲。
背后有挺机关枪急速地向他点射。他已经撤到那片开阔的杂草斜坡,身边一片平坦,根本无处藏身。现在他是破釜沉舟,只能一口气地飞奔,如果稍一停步,敌人就会调准机关枪的射程。
子弹打在他周围的石头上,迸着火花。他往左侧接连闪了两下,又迅速转向右侧;他猛地收住脚步,一转瞬又奔跑起来,挥动着手臂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就这样,那挺机关枪又被愚弄了,一梭子弹打到他前面了。他跳向一边,听见子弹爆响着掠过自己的左耳。他还没来得及庆幸,便觉得脚腕被什么绊了一下,膝盖处一软,一头栽倒。他的左腿脚腕和膝盖还在刺痛。有一种热烘烘的感觉。一股粘稠的细流渗了下来,湿漉漉的,流进了他的鞋子,流到土地上。他用手摸了一下左腿,满手都是血,连指甲缝都染红了。一股鱼和石灰的腥味。他想站起来,左腿轻飘飘的,使不上劲。完了,左腿两处中弹!
正是午后1时。他的四周全是尸体和明晃晃的光线。围攻的敌军还在嗷嗷叫着冲锋。他们的帽子、枪口和狰狞的面容在山野的岚气里飘浮。他的脑子里有种种念头和幻想在翻腾。追击的敌人愈来愈近!他忙脱掉身上的制服,免得敌人搜查口袋发洋财时被发觉还活着。他咬紧牙关,从山坡上滚下去,跌进一块深耕的田沟里。血立即把田沟里的水染成了红色。像波浪一样越来越向上升的刺心的疼痛,顺着脚腕一直升到大腿根。膝盖处的筋断了,脚腕骨被打折,不能行动。
“营长!营长!”
有人在摇晃他,凑近耳边喊。
陈赓睁眼一看,是卢冬生。
“营长,我扶你走!”
“不行!”陈赓推开他。“敌人上来了!我走不动,你快跑吧!”
“你不走,我也不走!”
“你快走!不走咱俩都完了!”
卢冬生去搀陈赓,被陈赓狠狠推了一把:“快走!”
敌人已经越过山头,朝山下袭来。漫山都是枪声和狂叫。卢冬生便躲进附近一堆草棵里。
陈赓握住了驳壳枪光滑的枪把,把枪口举到了胸口。死亡在诱惑。一勾扳机,痛苦将不再延续,被俘的一切麻烦事都可避免。也不会连累因为他而不肯离去的卢冬生……可我才24岁,24岁就革命到头了?太便宜他们了!十年奋斗难道就为了这么一颗子弹!同志还在,革命刚刚开始……让我再碰碰最后一次运气吧!
他丢开枪,用手把腿上流出的血涂抹得一身一脸,静静地躺着。
机关枪不作声了。一下子寂静得可怕。陈赓猜想,追击的敌人正沿着山坡朝自己逼近。他清楚地听见敌人边骂着边用枪枝翻动尸体,一声呻吟,就会招来一枪。尸体的恶臭和刺鼻的硝烟味一齐飘来。有颗补射的子弹打在岩石上,火花四处迸溅。他准备好,只要敌人有所察觉,就扑上去扼住对方的脖子,同归于尽……皮靴声愈来愈近,踏得草棵沙沙响。来了,来了!陈赓咬紧牙齿,屏住呼吸……走过来的是个小个子,抬起皮靴朝着陈赓腰上就是一脚。陈赓纹丝不动。小个子奚落笑骂一番,又去扳另一个尸体,蹲下身来翻尸体的衣袋,粗鲁地拽着死人的皮靴……随着脚步的起落,陈赓咬牙切齿地在心中咒骂:宰了这些狗杂种……宰了这些狗杂种……宰了这些狗杂种……
陈赓静静地躺着,感觉到眩晕就要袭来,就像汗和血溶进炙热的土地一样,神志也在一点一点消失。
来吧,让他们来吧!让他们来吧……
躺在那里过了两三个钟头,下午4时左右,山上突然人叫马嘶,一批人涌过来,到处搜索。陈赓腰上又挨了一枪托子。他睁开眼睛偷偷一看,见他们脖子上都挂有红带子,知道这是叶挺的部队,他振作精神,向一个士兵挥手打招呼:“我是自己人!”
搜索的士兵大惊失色:“你,你怎么这个样子?”
陈赓看了一下自己:满身血污,只穿着背心和短裤,苦笑了一下:“被敌人打伤了!”
“你不像自己人!”士兵一拉枪拴,枪口指着他。“谁证明你是自己人?”
“我,我证明!”躲在深草丛中的卢冬生跳起来,掸着满身的碎屑,指指陈赓说:“他是我们营长!”
“营长?我还是军长呢。走开吧!”
“你不信,找你们叶军长!我们是贺龙部队三师六团的。”
“军长已经两天没合眼了,哪有闲工夫看你们!走,跟我们回城!”
会昌城里,指挥部门前。哨兵拦住问:“什么事?”
“这两个人要见军长。”
“谁?干什么?”一个戴着红带子的军官用红肿的双眼打量了陈赓一番。“老天,这不是陈赓同志吗?”
闻声又从指挥部走出几个人。他们是周恩来、聂荣臻等。周恩来跑过来扶住陈赓,说道:
“我们差点把你写进阵亡将士名单!”
陈赓既没有敬礼,也没有点头致意。一下子,浑身一点力量都没有了。
“医生,你快去看看!我们营长腿肿得跟大象腿似的,都发黑了!”卢冬生跑进办公室,神色慌张地在傅连璋耳边说道。傅连璋卷起听诊器,跟着冬生朝病室里走。
福建汀州城内的福音医院,是座教会医院。战火一起,医院不大,起义军的300多名伤员进来,连走廊里都加了床。有些年轻伤员坐在地上。护理人员大多是志愿来的青年教员、学生。许多人一见血就发抖,一见脓就要呕吐,可他们还是抢着替伤员洗伤上药,喂水喂饭。炎热的天气,既潮湿,又闷热,傅连璋走得很急,流着大汗。床那边传来一阵含糊不清的话语,接着传来一阵呻吟。
他把陈赓腿上的绷带解开,绷带上满是脓血,伤口处像厚厚的嘴唇外翻着。周围的皮肉已经腐烂,膝盖骨像个倒扣的瓷碗,肿胀得皮肤泛出蓝幽幽的光亮。屋子里顿时弥漫着腐烂的恶臭。
年轻的院长在盥洗盆内使劲搓着双手,满头秀发不停地晃动着。院长似乎是在注视墙壁,实际上却正在思索着另外一件事情。他问卢冬生:“这个伤员是你负责的?”
“是……”
“怎么恶化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不上来治?”
卢冬生淳朴诚实地脸抽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屋子里鸦雀无声。
“你们给我打什么针?是不是瞌睡虫的血?我怎么睡不醒?”
太阳很强,从百叶窗照进来的阳光在陈赓脸上映下道道条纹,把陈赓那张清秀、疲倦而又坚韧的面孔衬得格外清晰。他醒了。
护士示意他不要讲话。傅连璋用听诊器敲打着掌心,把解开的钮扣扣上,不一会儿又解开。
“我的腿怎么没感觉了,是不是好了?”陈赓说着,就要去摸腿。
“别动!”傅连璋在又窄又硬的床边坐了一阵,终于拿定主意,站了起来:“准备准备,截肢。”
“截肢?”陈赓惊得面如土色。他捂住膝盖,大声说道:“我死里逃生,难道是为了到这里来锯腿?没有腿,我拿什么走路?我还怎么带兵打仗!”
“现在要紧的是保住性命!”
“你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保守疗法当然有。要把烂肉和新生的息肉一刀刀剜掉,那个滋味不比截肢好受。”
“死我都挺过来了,还怕疼!医生,我求求您,只要能保住这条腿,我,我陈赓年年给你做寿……”
傅连璋终于被说动了。他吩咐护士拿来夹板和消毒水。他望着陈赓因流血过多而变得蜡黄的脸,不禁犹豫起来。
“做吧,医生。”陈赓安慰起傅连璋。“打惠州的时候,我自己还从腿上抠出子弹呢。你大胆做吧,我要是叫一声就不是人……”
傅连璋走到病人跟前尽量轻地揭着粘着血肉的绷带。他用手术刀刮着烂肉,一股股脓血往外涌着。傅连璋用棉纱蘸了一些消毒水,往肉芽上扑了扑。陈赓的腿一下抽起来。傅连璋急忙看了一眼陈赓,在胸前画着十字。
陈赓正在和护理他的谭惠英护士交谈:“我们冲进小银行的时候,行长拿出几只金铸的小乌龟,叫我们高抬贵手。他以为我们是抢钱的土匪……”
他的话音开始发飘了。舌头不听使唤,上下牙开始打颤……
“小谭,给我条毛巾!”
他把毛巾咬在嘴里。脑袋可不能发昏,千万不能昏过去!要让医生觉得你没事……别喊!
“咝……”
别出声!你要保住腿就别喊!
“咝……”
别出声!听见没有?你为什么想哭,你为什么流泪了?
“哎哟……”
你干嘛像个猪似的嚎叫?想叫傅医生看你的笑话吗?再坚持一会儿,一会儿,你那块腐烂的地方就会刮掉。别发抖,控制住自己!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千万别尿裤子……糟糕,尿了……
一种想摆脱疼痛的愿望像闪电一般闪了一下。不,只要不是锯腿,即便是疼痛,即便是折磨,都要顶住!他的身子又颤动了一下,碰到了硬板床,就再也不动了。
傅连璋解下口罩,呼出一口大气。他摸摸陈赓湿漉漉的额头,看着他那憔悴的面容和腮边留下冷汗,问道:“痛不痛?”
陈赓微笑着摇摇头。
“不对。我知道你刚才一定痛得厉害。但我佩服你,小伙子!”他看到卢冬生手里的毛巾,上面留下了陈赓咬破的洞。
“我是一个基督教徒。你是教义里讲的英雄子孙。可惜我还不是彼得或约翰。假使他们拉拉你的右手,就可以使你的脚和踝子骨健壮……”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医生。”陈赓微笑着说。饱尝疼痛之后,他正在深深地、艰难地呼吸着。“到我们队伍里来吧,我们多需要你,你肯定比约翰和彼得强!”
傅连璋警觉地瞥了陈赓一眼:
“我不像你们那样年轻。你好好养伤吧。”
接连几天,傅连璋都来看伤情。每天用“由素”替陈赓消毒,用夹板固定。同时把新鲜牛奶让给他喝,增强他的抵抗力。陈赓时常讲起义的故事给大家听。有时讲得入神,不禁眉飞色舞。有时也会感慨近于沉默,喃喃道:看来,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竟使许多老战友对杀起来。钱部那些黄埔同学,在战场上作战的那股坚决精神,是中反革命的毒太深了,加上国共之间无法破除成见,我们如果要获得胜利,专凭硬拼还是不够的。护士们忘了手里的工作,重伤员也忘了疼痛。屋子里一时静寂无声,沉浸在对这个伟大事件的思念中。
傅连璋的心也被他的革命激情所打动。但他有点拿不定主意……
那时,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正患重病,也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边的一座楼上,傅连璋也经常去替他医治。他烧得很厉害,加上年纪大了些,身体也显得虚弱。他那坚定乐观的心情,却使你看不出他像一个重病的老人。他病好些,就找些话和傅连璋聊聊。问他多大年纪了?做医生几年了?从他的谈话中,傅连璋知道他已经50岁了,那年刚刚参加了共产党。
傅连璋大吃一惊。相信,还是不相信?
徐特立哈哈大笑起来。
“50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人生五十始,我起码还能有三四十年能为党工作呢!”他几乎是突如其来而又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刚满33岁,对吧?”
傅连璋点点头。
不久,陈赓拖着没有痊愈的伤腿,徐特立撑着才退烧的身体,都走了。
后来,傅连璋摆脱了种种束缚,跑到瑞金,投奔了红军。陈赓的腿也和傅连璋的名字一起保存下来了。傅连璋的名字一直印在他的脑子里。他记得傅连璋的生日正好是中秋节。所以每逢中秋节都要登门祝寿。如不在一地,就写信祝贺。直到1961年3月,在他垂危之际,仍记得中秋节的事。叮嘱家人:“每到中秋节,不要忘了向傅连璋同志祝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