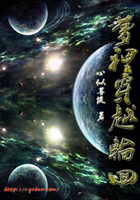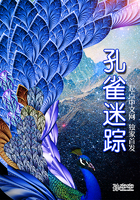1933年4月15、16、17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三次公开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为应付这次审讯,陈独秀早在2月20日,就奋笔疾书写好《辩诉状》,但无钱付印,原来,他在上海被捕时身无分文,就连衣服也未带。
公开审讯消息传出之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镇江、无锡、苏州、上海等地的旁听者纷纷专程来南京,只能容纳二百来人的法庭旁听席,拥挤不堪,而且是一次甚于一次。据当时《申报》报道:“惟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有立于坐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有立于室外者”,寂静肃穆。当陈独秀等被押上法庭被告席时,全场起立,众目投去,鸦雀无声。陈独秀镇静自若,目光环顾庭堂,不过脸庞消瘦,几多惆怅。
当检察官朱隽起诉指控陈独秀与中共一样,“主张打倒国民党政府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时,陈独秀早年的诤友、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站起来,出庭为其辩护。他认为,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陈独秀当初与国民党“合作”,在国民党中担任职务,且在“汪陈宣言”中苦口相劝“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陈独秀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主张“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章士钊言辞有据,有力地批驳了检察官起诉陈独秀所谓叛国,危害民国是“湛然无据”,法庭应“谕知无罪”,“省释无辜”。
陈独秀听了章士钊为他的辩护,拍案而起,即刻声明:
“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他个人之意见,至于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他的话音刚落,旁听席上众人发出赞声:
“革命家!革命家!”
好心的章士钊,被陈独秀的这个意外声明,弄得十分尴尬。陈独秀习惯地摸了摸胡髭,举目向庭堂而视,用洒脱、宏亮的声音,发表洋洋数千言自撰《辩诉状》: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走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
他在自撰《辩诉状》中,极尽驾驭文字之能事,慷慨激昂,义正辞严,把自己变成了原告,把法庭当作战场,一下子使国民党对他的审判,变成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揭发和指控,证明犯有“危害民国”和“叛国”罪的不是他陈独秀,而正是国民党政府自己。他说:
“予生平言论行事,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开罪国民党已耳……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入热河,而国民党军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也,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
这时,旁听席上发出一阵笑声,大家交头接耳,赞许陈独秀的辩诉言之有理,审判长胡善称怕惹起麻烦,便站起来说:
“大家肃静!旁听者不得喧哗,被告陈独秀不得有鼓动言辞。”为表白自己,他又画蛇添足地说:
“大家要万众一心,上下一致,精诚团结。”
接着,陈独秀幽默地说:
“不要我讲话,我就不讲了,何必还要什么辩诉程序呢?”
胡善称忙解释说:
“不是不要你讲话,要你言辞检点一点,你讲吧。”
陈独秀接上说:
“刚才你说团结,这是个好听的名词,不过我觉得骑马者要和马讲团结,马是不会赞成的,它会说你在我身上,你相当舒适,我要被你鞭打还要跑,跑得满身大汗,你还嫌慢,这种团结,我敬谢不起。”
旁听席上,又爆发出哄堂大笑。
陈独秀态度安闲,顾盼自若,又说道:
“好,闲话休提,书归正传,我遵命讲我的辩诉了。”又引起旁听席上一阵笑声。
最后,陈独秀大声疾呼,宣布道:
“今者国民政府因予始终尽粹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之外,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若当院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以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在拘押期间之经济和健康上的损失!”
旁听者纷纷议论,气氛热烈:
“这不但表示陈氏政治风骨嶙峋,亦为法庭审判史上的新纪录。”
陈独秀、章士钊的两辩诉状,轰动全国,各大报纸都希望登载,但国民党以“不许为共产党张目”而禁止之,只有天津的地方报纸《益世报》和上海《申报》冲破封锁,分别登载了全文和摘要。以后,上海泸江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还将它选作法学系教材,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陈独秀判刑后,亚东图书馆从章士钊那儿拿来所有材料,出了一本《陈案书状汇录》,印了1千本,汪孟邹从上海来探望时带给了他,听说此事,陈独秀十分高兴,不停地翻阅着汪孟邹带给他的小册子。
陈、章的辩诉,纵有万分理由,也改变不了国民党的既定政策。法院秉承当局的旨意,宣判陈独秀、彭述之各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15年,其他被捕者各判5年、2年不等。
当宣判完毕,陈独秀当场起立,愤然大声抗议:
“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裁决不公我要上诉!”
消息传到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第77期报道说:
“二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讨饶……所以保住了生命,而且很快要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得以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哩!”
陈独秀对法庭判决极其不服,提出上诉,并于6月15日写了言辞有力的《上诉状》。官司悠悠,三冬九秋,时隔年余,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才终审判决陈、彭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