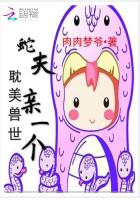1942年2月的一个夜晚,一辆黑色的小卧车开进愚园路地丰路口的一条宽敞的弄堂里。这条弄堂里一共只有5幢洋房,4号就住着李士群。
这是“七十六号!”打手吴四宝孝敬给李士群的住宅,西式洋房,中式客堂,上下三屋,屋前还有一个漂亮的大花园。吴四宝巧取豪夺,“买”下了2号、4号两幢洋房,一幢留作自用,一幢送给了李士群。
汽车在4号门口停了下来,轻轻按了两声喇叭,铁门悄然无声地打开了。汽车驰进花园,停在洋房前,车上一前一后跳下两个人来,前者身材硕壮,后者气宇轩昂,他们便是袁殊和潘汉年。潘汉年在袁殊陪同下走进客厅,李士群急步迎上前去,他望着潘汉年这张似曾相识的脸,跨前一步,刚要伸手,又觉得有些不妥,于是手就尴尬地停在了半空……
潘汉年看了看李士群那张似笑非常的面孔,淡然一笑,便主动伸出手去,握住了李士群在半空的那只手,轻声说:“李先生,久违了……”
李士群用力捏住潘汉年的手使劲摇了摇,说:“潘先生,久违了,怕有十多年了吧……”
1931年4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党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党中央急调一批忠贞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担任党中央的保卫工作,以便切断顾顺章原有的关系网,潘汉年就在此刻从左联调到中央特科,担任过李士群的领导。1932年李士群叛变投敌,以后又企图反正,这前前后后的一笔糊涂帐,潘汉年却记得清清楚楚,这一晃倒也真的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
两个人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叶吉卿端这端那,亲自前来张罗,同时将站在一边的胡均鹤介绍了潘汉年。说来胡均鹤也是熟人,30年代初他曾经做过共青团中央的书记,后来叛变做了特务。他说话不多,老是阴沉着脸,当潘汉年把手伸给他的时候,才勉强在脸上挤出了点笑容。
潘汉年轻轻地呷了口咖啡,两眼炯炯有神地注视着李士群,意味深长地说:“李先生,是有十几年没见面了,想不到我们还会再见面吧!”
李士群恢复了自信,他举着刀叉将一块蛋糕塞进口里,咽了下去后说:“潘先生,你也晓得我现在在政府里的位置可以讲是不算低了,这一次请你来主要是想叙叙旧情……”
“是吗?”潘汉年微微一笑:“李先生,南京、上海都是中国人的土地,中国人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有些人认贼作父,引狼入室,非要借日本人的势力来欺压自己的同胞,这样的官做得再大,又有什么滋味?再讲,李先生,你这个‘部长’做得也很不自由,你的一举一动哪一样不要经过你的后台老板晴气庆胤的同意?就连七十六号里不是还有个涩谷准尉吗?如果你真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的话,就应该经常想一想这些事情!”
李士群被潘汉年的这一番话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很不是个滋味,过了好一会儿,才喃喃地讲:“你的这番道理我不是不晓得,你们共产党不要我,国民党也不要我,我是在走投无路时才投靠日本人的。我也晓得汉奸这碗饭不好吃,全上海哪一个老百姓不是指着鼻子在骂我李某人?唉!”
“李先生,那你应该拿出中国人的样子来。”潘汉年又说。
“潘先生,你叫我怎么办?”李士群抬起头来,两眼通红,赌气地说:“难道你要我真刀真枪去和日本人拼?”
“不,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潘汉年淡淡一笑:“这么多年了,你好激动的老脾气怎么还是改不了!真如你自己所说的,你现在官做的不算小,你立功赎罪的机会会很多。你现在的这个位置很重要,你可以为老百姓做的事也很多。”
“这……潘先生,我听你的……”李士群又说。
潘汉年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哈哈大笑:“李先生,你是个明白人,你心里清楚得很,现在你怎么会听我的呢?我只希望你今后做事情,能拿出一个中国人的样子……”
李士群和叶吉卿毕恭毕敬地将潘汉年和袁殊送到洋房门口,在握手话别时,仿佛不经意地指了指胡均鹤,说:“这是我的助手,今后与潘先生的联系,由他全权负责。”
潘汉年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胡均鹤,这才跳上汽车。汽车拐出花园,疾驰而去,不一会儿便消失在浓浓地夜雾之中……
一列从上海到南京的火车,喘着粗气,吐着浓烟,徐徐从上海火车北站开车。车很挤,车厢里坐满了上海到南京沿线的各式人等。但是同一列车上,二等车厢里却显得空空荡荡,整整一节车厢里只坐了不到一半的人。这里坐的都是一些身份特殊的人,没有一个特务会自讨苦吃,跑到这儿来盘查。但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恰恰在这节车厢里,坐着他们日夜想捉的中共江苏省委近一半的领导:刘晓、潘汉年、王尧山……
列车徐徐地在镇江停站住了,潘汉年提着一个小皮箱率先走出车厢,王尧山和他的夫人紧随其后也跳下车来。站台上正站着两个人,高的一个一身西装,矮的一个身着长衫,这两人一见潘汉年一行,便径直迎上前来,王尧山一见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那着西装的正是中央通报过的大叛徒原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均鹤。
胡均鹤走到潘汉年跟前,与潘汉年握手寒喧,同时便将这一行人带到了镇江最大的饭店金山饭店住了下来。胡均鹤前脚刚走,王尧山便急步上前,一把拉住潘汉年问:“小开,这……”
潘汉年抻开手掌,意味深长地望了王尧山一眼,然后一下子将巴掌翻了过来。王尧山一见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就在此刻,李士群也带了伪“江苏省民政厅长”张北生、“建设厅长”陈光、“财政厅长”唐惠民、“保安司令”唐生明、“教育厅长”袁殊,以及已经投靠了李士群的原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澍一行人,浩浩荡荡离开苏州,到镇江来“视察”。
中午,火车抵达镇江,李士群一行人在镇江吃了顿午饭,然后坐上汽车直驰江边码头,早已有一艘小火轮升火等在那儿。他们跳上小火轮,小火轮便载着他们渡过长江,到了对岸的扬州。当天晚上,扬州的地方士绅包了一家饭馆大摆筵席,招待李士群。席间大家高谈风花雪风,风流轶事,酒过三巡,又不知从哪里招来了一些妖艳的美女前来劝酒,于是这一帮狐群狗党越发喝得起劲,大吵大闹,酒席上一片乌烟瘴气,谁也不曾注意到李士群早已“不胜酒力”,喝得酩酊大醉由卫士们搀扶出去“休息”了。
夜深人静,就在扬州市郊的一所深宅大院里,李士群悄悄地露面了,与他碰头的是刚刚从江对岸镇江坐小驳船摆渡过来的潘汉年。
“潘先生,这一路上过来可发生过什么麻烦?”李士群问。
“没什么麻烦,一切都很顺利。”潘汉年回答。
“是吗?”李士群高兴地扬了扬头,颇有些夸张地说:“这一次我请贵方的几位老板到苏北去避一避风头,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日本人几次三番催促我要捉共产党,我手底下的人很杂,万一有个失手,倒显得我没有诚意了。”
“这没什么,”潘汉年淡淡一笑,故意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本来我们就想到苏北去转一转。但是我倒希望李先生明白,不要看日本人目前非常猖獗,但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了,太平洋战争不过才打了一年,日本人却已捉襟见肘,落入了泥淖之中。李先生要审时度势,认清大局……”
“谢谢潘先生的教诲,”李士群谦恭地说道,不知怎地,无论他掌握了多少人的生杀大权,在潘汉年这位过去的老上级面前,他始终感到抬不起头来。他想了一想,从兜里掏出两张薄薄的纸片递给了潘汉年:“这是日本小林将军和我刚刚商定的‘清乡’计划,或许对贵方有些用处……”
潘汉年接过这两张薄纸片,凑在灯下细细地看了看,又还给李士群,说:“李先生,多谢了。听说,晴气庆胤调到了华北方面军,再有影佐祯昭也马上要调回日本,去担任东北军炮兵司令,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啊?”
李士群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暗暗吃惊,他想:日本高级军官的调动是一件非常机密的事情,自己也是这两天才从日军驻苏州的师团长小林中将处听到这个消息,潘汉年怎么这么快就晓得了?但是表面上他却不露声色地回答说:“我也听说了……”
潘汉年似乎并不在意李士群的装模作样,他沉思了好一会儿,忧心忡忡地讲:“李先生,晴气、影佐接二连三地调防,这对你来讲可不是什么好的兆头,你不要锋芒太露了,你可要小心呵……”
李士群心里一沉,但依然不露声色地讲:“这我心中有数,我已经作了准备……”
第二天,李士群照样带着他的那群幕僚在扬州“巡视”,而潘汉年一行却在胡均鹤的护送下坐了去仪征的机帆船……这一切似乎都显得天衣无缝,正可谓只有天知地知神知鬼知,但是潘汉年和李士群都没有想到,有一双眼睛已经牢牢地盯住了他们。他就是被李士群带在身边,地位尴尬,生杀大权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陈恭澍……
这神秘的镇江之行,给李士群带来了杀身之祸,而在十年之后又铸成了潘汉年千古奇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