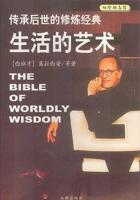但是年少的我,却是另一种意识状态,丝毫体会不到生活的艰辛和生命的意义。
那时的我,还在读小学,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对于节日特别敏感。因为在每一个特殊的节日里,都能够收到许多的礼物,并且父母的礼物是不可缺少的。
我从小就是个任性的孩子,对于玩具,表现得十分热衷。在商店里,但凡遇见心仪的玩意,就总能够找到机会,从父母那里获得。我总是志在必得,想尽办法向他们索取。很多次,为了得到一件爱不释手的宝贝,我总是不合时宜地叫嚣,逼迫着父母给予满足——我没用错词,当时确实很无赖。百般无奈之下,他们也只得妥协,即便是在捉襟见肘的境地。在当时的学校里,盛行着一股过生日的热潮。有即将生日的小朋友,提前就会通知要好的玩伴,让父母准备一场盛宴。谁家的排场大,谁收到的礼物多,便是其他小朋友羡慕的对象。于是,生日晚会成为检验一个孩子幸福指数的参考依据。这便顺理成章地滋长了年少的孩子们的虚荣心,谁都不愿在小伙伴面前丢脸。
但是那时,我的父母忙于工作,早出晚归,生活尚且只在温饱线上徘徊,而且又赶上国企大裁员,面临着下岗的危机,连生存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这一切并非我所能关注的问题,其实我好像也不太想关注这些,为了满足自己小小的虚荣心,我通常都要为父母制定宴请的标准。在家里办酒席,难免有些寒酸,那么酒店便成了理想的选择。于是,为了筹备这场我的盛宴,父母要提前很久就开始节衣缩食。
我清楚地记得,十二岁那年,在我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父母依旧一筹莫展。母亲试图与我商量,先降低标准于家中庆祝,待到发工资时再给我补上。但我毫不含糊,“邀请函”早已发出,怎能失信于人呢?
父母拿我没有办法,不得不趁着夜色辗转亲朋那里筹集资金。那一夜,他们回来得很晚,而我早已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便又匆忙离开了家。但凡有点接触的,几乎都借了一遍,你家五十,他家七十,他家一百。最后终于为我换来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和穿在我身上用来炫耀的新衣。
那个时候,对于穷困的现状,我尚且无力感知。或许是因为父母总能够将最好的东西留给我。
就在我依旧沉浸于生日的热闹氛围里,为小伙伴们羡慕的眼神沾沾自喜的时候,便迎来了房东太太的上门催租。她穿着睡衣,抽着香烟,和《功夫》里的包租婆一样,身上的胭脂水粉与香烟的味道掺杂在一起。此时,父亲碍于情面,躲在卧室里不作声;母亲硬着头皮凑到跟前客气,央求着她暂缓几日,却只换得房东太太的一阵奚落——我看你们这一家人就是“穷烧”!“穷烧”,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它意味着富人眼里的穷人摆阔,不自量力。
正是这句话,像是针芒,刺痛了一家人的心,没有流血,就是疼。这句话让本分的母亲几乎落泪,让要强的父亲无地自容,更让躲在房间里装作写作业,实则竖起耳朵的我感觉耻辱。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将两个月的生活费和房租,都用来置办那次排场大的生日宴席,换来我在小伙伴跟前的那份微不足道的风光与虚荣。
以至于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甘心吃着馒头,就着咸菜,节衣缩食好长一段时间,才勉强凑够了欠下的租金,稍稍拾起一点穷人的尊严,但却又要为下一个季度的租金发愁。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庆祝过生日,即便是后来条件有所改善,丝毫不必再为一顿酒席劳心费神。但是那些过往的岁月中,那个原本并不重要的日子,却像是一把枷锁,拴在父母已满负重量的脊梁上;又像是紧箍咒,箍紧着我蠢蠢欲动的心。
以至于在今后每一个虚荣跳出来作祟的时刻,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都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我的脸上,让我学会告诫自己:莫逞强,一切表面的风光,都是虚无,都是负累,都将让你为之付出沉痛的代价。只有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并且尽善尽美,才会得到自己应有的掌声。
真正的面子,不是你挖空心思做了什么,实现到某种程度,才让人感觉惊异佩服;而是你不必做什么,不必刻意地表现什么,就能够让人竖起大拇指!
这是一种特有的人格魅力,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每个努力实现自我价值,保持积极向前的人,每个今天都比昨天有进步,明天且又循序渐进有所期待的人,才是最值得你立为人生标杆的人。
同时,你不必没有原则地去羡慕那些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物质富有者,并将自己置于称重的天平上,因差距而感觉自卑,因命运不公而怨天尤人。你该明白,别人现在所拥有的,无非只是祖宗积德,也同样会有坐吃山空的那一天。在没有这个幸运的条件之前,你还有自己脚下的路。
你该相信,只有把目光对准地平线的人,才能找到自己正确的道路。即便你的现在,离成功还差一步,还有一段艰难的旅程要走,但是你的人生正是因为在不断地琢磨,才变得更加圆满、晶莹与剔透。
爷爷离开的时候,是个秋冷雁高的季节。
25
这一生有很多的遗憾
但好在还有更多的希望和爱
这一生有很多次失去
但总有一次拥有
值得倾注一世
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
我在三百公里外的地方,坐在办公室里改稿子。那篇稿子是许多年前,我写来悼念外公的。没想到,在怀念怅惘之际,再次收到爷爷病故的噩耗。十多年过去了,时光总有一些惊人的相似,让人无暇思考,却又要为之惊叹。生活总是这样,一切来得没有征兆,既能够让你喜出望外,心花怒放,又能令你防不胜防,失措惊慌。
我顾不得思索,潜意识里蹦出“回家”两个字。我给父亲语无伦次地打过三通电话,第一通电话,父亲哭,我也哭,两个人没说一个字。第二通,父亲哭,我咬紧嘴唇沉默。第三通,父亲用沙哑的嗓音向我陈述:孩子,你爷爷走了。我说:爸,你在家等我。电话临挂断时,我补充安慰:爸,你要好好的……我记不清我是以多快的速度切断电脑电源,收拾行囊,然后奔跑。我看了一下时间,十六时零三分。最后一趟北去的火车已然开出半小时。我在城南,汽车站在城北,我央求出租司机加速,好心的师傅也算体谅,一路油门。
我明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父亲需要我,我体谅得到他内心的缺憾和悲痛。好在赶上了最早的一班回家的大巴。我找到最后一排靠近车窗的位置,并下意识地箍紧窗帘,躲在角落里。
一路上,我不停地流眼泪,却又突然特别想看看窗外。然后我拉开窗帘,视线有些模糊,但这些曾经于我看来一闪而过的风景,却被打上了时光的烙印。像是冥冥之中,自有的安排。你该相信,每个出现在你身边的人和事,都有其特殊的使命。有些人,在你的世界里华丽地转了一圈,只为与你相遇,但未能找到与你共有的交集,不得已地被替换下场。有些事,在你尚未取舍之前,便早有了定论,之所以要安排到你身边,那都是出于命运的谋略计策,是用来教会你成长,驱使着你在千锤百炼中蚌病生珠,淬火成钢。所以,我愿意清楚地记得这一天的每一个细节,然后打包装进回忆里。这一日,阴天,6℃~10℃。
四小时的车程,父亲给我打过五次电话,用最耐心的口吻,话音已落,但却久久不肯撂下电话。
此时的父亲,啰唆得像位失忆的老人,又如懵懂的孩子。我能够想象得到,他是如何压抑着情感,跟我做镇定自若的交流。我甚至能从那每一声言语停顿的间隙里,感觉到他呼吸的局促,以及内心充斥的不安。其实我也很想哭来着,只是我觉得父亲需要我比他更坚强一点,我想安慰他。
到达北方小城已是晚上九点,老天爷也好像能读懂人的心思一样,应景地下起滂沱大雨。
爷爷常居在离城百公里远的农村,我还有一段坎坷的道路要一个人走,我跨上父亲事先为我准备好的车子,在一阵手忙脚乱中,忘记了松开手刹,直至车轮被迫逼停。
这又是一段漫长的旅途,往日漫不经心地走过,尚不觉得遥远,唯有那一夜,只盼天涯化作咫尺。我甚至能感觉到,车轮在泥水里打着滑,水花溅满了车身。我也不好说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其实大脑有点空白。
回到乡下已是翌日的凌晨,没有一盏街灯是亮着的。大老远,我便听到父亲的咳嗽,在格外寂静的深夜里,像是破旧的钟。父亲看着我走近,如释重负般深呼出一口气。
我不禁稍稍安心了点:“爸,我回来了,你放心,我陪你一起挺住!”说着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充满了能量。
那一刻使我明白,原来一个人强大的标志,就是学会保护另一个人。我是他血脉延续的薪火,在时间的流逝中,我已长成了一棵挺拔的大树,能够为他遮挡这一程风雨,能够伴他一同上阵,抵御岁月的侵蚀。如同在我的年少时代,他曾带给过我的那些内心安定和富足。
我沉默着,给爷爷的遗体磕了三个响头。
想想去年,爷爷的身体还算硬朗,我买来新车,准备接他去城市享享清福,或是驾车陪着他到处走走。路线都已规划好,但还是没能够实现。再想想每次回乡探望,心里总想着要在有生之年,给他多照几张相片,留作永久的记忆。但却总因为时间匆忙,忘记带上相机。同样的事情还有许多,虽然对于我的空头许诺,爷爷总是会心微笑,表示理解,但正是这些琐碎的小事,最后成为我一生的遗憾,让我只能深陷在自责中。
人总是这样,对于眼前触摸到的东西,保持着长期疏离的习惯。直到有朝一日,换了一个时空,看不到,够不着,便会走进内心的冰窖里,成为永久的裂痕。我们都是野心家,只顾着开拓新的领地,遇见新的见闻,认识新的人,攫取更多的财富,获得更高的名望,并且对此不遗余力,当作人生的战利品,以及供你余生用来回忆的展览。
但是造物者恩赐给你所支配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你的人生像是一条有规格的道路,你所揽获的东西,精神的、肉体的、物质的,都如同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箱子。你在这条道路上,一边行走一边收获,收获的就摆放在路边,然后继续向前进。收获得越多,堆砌得也就越多。直到最后走完全程,你再想回过头来收拾,却发现,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就连下脚的空隙也都没有了。那些箱子也被你堆叠得乱七八糟,使你根本无法折返,无法走近,无法用来感受。这样的行走,即便获得得再多,你的生命依旧空无一物。
同时,那些收获,像是攥在手心里的水,还没等到你试图撒手,便早已从你的手缝里溜走,从此不再属于你。由来已久的情感,长期拥有的物件,朝夕相伴的朋友,每一个你所认定会亘古不变的东西,一旦投递到了时空里,就只剩下一份回忆。
生命太拥挤,让我们只顾得寻找,不记得珍惜。人生就像掰玉米,我们常常顾此失彼,掰得越多丢得也就越多。与其回头晚矣,不如珍惜当下,把每一个捧在手心的当作最好的那一颗,慢慢地,你会发现,手心粒粒饱满,盛满阳光。
有人说
生命有了裂缝
阳光才能照进来
有人说
每一次告别
天上有颗星
就会熄灭
26
我好久都没有流泪
想必那样太矫情
我好久都不曾怀旧
想必那样太琐碎
但是同时
我也好久都不再像是从前的自己
我不知
我的初心
弄丢去了哪里?
除了眼泪和记忆
还有谁能帮我找回?
总有阳光温暖卑微的你
父母离婚那年,我母亲离开了这座城市,父亲因为经济问题被卷入了一场官司的风暴。于是,我无家可归,无人可依。迫于无奈,好心的长辈将我送到农村的爷爷家。我不得不与那座记忆分明的城池做短暂性的告别。
我没有来得及跟校园里的小伙伴说声再见,没有带走一件心爱的玩具,便急匆匆地攀上了开往乡下的汽车。谁都不曾知道,那个原本活泼可爱的小男孩,为何突然间从大家的视线里消失;谁都不曾注意,坐在汽车的后座上,他一边流泪,一边于心中默祷着告别。
很多人喜欢躲在角落里,自言自语。那是他与命运的交涉,同自己孤单灵魂的对白。那是在暗处蠢蠢欲动地为自己蓄光,更是自我精神意识的支撑。正如在一个密闭的容器里,它有自己应有的容积,一旦逾越了警戒线,便只能试图寻求释放的突破口。这个口子愈是狭窄,就愈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所以,你要允许自己的神经质,学会找准情感流泻的突破口;即便是在无人倾诉的时候,自问自答也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途径,不至于让扭曲的心灵凹凸变形。
在农村,没有照明的路灯,没有方便的自来水,没有水冲的马桶,更没有人陪我玩耍,和我对话,我消极抵触的情绪便暗自生长。
属于我的精神乐园,是一片打谷场的空地。有一条蜿蜒的小溪,在麦田之间萦绕。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都能与之辉映。春暖花开之际,我时常蹲坐在溪边,看初生的小蝌蚪在水族乐园里自由地嬉戏。
有一堆堆摞得很高的麦秆垛,是各家生火做饭的燃料。中心的麦秆被首先掏空,便可以成为小朋友们温暖的窝棚,在阴雨的天气里,可供躲避风雨。每每下午放学,不想回家的时候,我都会手捧着心爱的连环画册,对准阳光的方向,津津有味地坐在下面阅读。那片空旷的打谷场,在庄稼收成的时节显得格外热闹。你能够看见忙碌的庄稼人,拉着耕牛,牵引着柱状体的石碾,在收割的麦穗上来回地轧过,粒粒饱满的麦粒便能脱壳而出,给人以丰收的喜悦和生活的美好。但是平常,这里鲜有人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