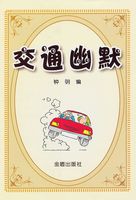侄女要临产了,她母亲不在北京,我自然而然地担当起了母亲的角色。她已经开始有阵痛了,我陪伴着她在妇产医院的走廊里漫步溜达着。护士笑眯眯地走近,侄女询问:“我什么时候能生啊?”护士回答:“每次见到你,都是谈笑风生,还早着呢。真到了快要生的时候,就不是你眼下这样子了。”
护士天天干这个,见得多了,自然经验丰富。我们继续来回溜达。侄女告诉我:今天那个漂亮护士说,我怀的肯定是个女孩。还说,没见过我这样的,不仅脸面光滑白净,肚子也出奇地光滑细腻,洁净地连一道妊辰纹没有,一点黄褐斑没有。我说,距离谜底揭晓的时刻最多还有一天。
次日,我又熬好了红枣小米粥,拎着包子走进妇产医院。侄女和昨晚判若两人,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被阵痛折磨得相当痛苦。我攥着她的手,阵痛袭来,平时总是一副温柔爱笑的侄女,此时皱着眉头说,给点力行吗?于是,我双手攥紧她的拳,她用力推我,我使劲推她。她就是借助这种方式来对抗阵痛的。侄女不是个娇气的孩子,但她还是扭曲着身子对我说,姑姑,太难受了,打一针止疼针吧,我想无痛分娩。我劝她,要挺住,打针对你和孩子都不利。越是疼痛难忍,说明越是接近生了。她很明白事理,懂得孰重孰轻。听着临床产妇的痛苦呻吟,她一声不叫,只在阵痛来临时说个“疼”字,便咬紧牙关,使劲推着我的手。偶尔,她还自言自语地小声念叨着:宝宝加油,宝宝快出来。
晚上,侄女由她丈夫陪伴着,从病房送进产房。我和爱人以及侄女婆婆一家,在产房外焦急地等待着。
莫非赶上孩子出生的峰值了,整个夜晚,不断有孕妇被推进产房,大夫护士不停地忙碌着。产房外的凳子上,坐满了等待迎接孩子出世的家属。侄女还没有生,我爱人坐末班车回家了,侄女的公公荣老爷子年龄比较大,也让他回家了。我和侄女的婆婆、大姑姐,继续在外候着。每当产房的门打开一次,每当报告谁谁生了一个男孩或女孩,大家都会跟着高兴激动一阵子。产妇和孩子被推出产房的时候,我们总会站起来,用祝福的目光走近看看,为陌生人的母子平安或母女平安感到一阵欣慰。已经半夜了,我们一直处在兴奋和焦急中。为他人孩子的到来而兴奋,为自家孩子还未出生而焦急。
过了许久,产房的门又一次打开了,侄女婿出现在门口,向我们报告:生了,男孩,51公分,7斤8两,母子平安!
咣当,一颗悬在半天空焦躁不安的心落回到了实处。侄女的大姑姐立刻给家中拨通电话,告诉她70多岁的老爸,他有了一个近8斤重的大孙子。我打电话告知爱人,让他踏实睡觉吧。又急急给弟弟弟媳发短信,让他们放心。一个小生命的诞生,牵动着多少亲人的心啊。
十月怀胎,非男即女,非女即男。然而,这永远是一个津津乐道猜测的谜语,也是一道怎么猜都搞不准确的谜语。孕妇猜、准爸爸猜、家人猜、外人猜,直到住进医院,年轻漂亮的护士也还在继续猜测。这个谜底,在接生护士托起婴儿的小屁股,举到妈妈面前的那一刻,终于宣告揭晓了。
从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们三个人同时“噌”地一下站起来,涌到了产房门口。我们眼巴巴等着,像夹道欢迎什么大人物似的,迎接着荣家大孙子的出现,迎接着受尽痛苦折磨当上妈妈的侄女。不知又等了多久,在深夜三点多钟的时候,门开了,床缓缓推出。笑眯眯的侄女身旁躺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儿。他双目圆睁,好奇地看着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我高兴地说,都深更半夜了,这小玩意儿睁着大眼,倍儿精神。其实,精神的何止这个小玩意儿,我们每个人都如同喝了兴奋剂似的,毫无困意。
此时,我想起了作家毕淑敏在《性别按钮》里说的话:“当降生终于开始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男性……无论社会怎样进步,中国人还是喜欢男孩。尤其在产房里的时候,生了男孩的妈妈眉飞色舞,生了女孩的妈妈低眉顺眼……为了能让自己的妈妈理直气壮,为了能让望眼欲穿的爷爷奶奶喜笑颜开,我只好义无反顾地选择男性。这可绝不是向世俗的偏见低头,而只是想在出生的这一瞬间,带给我的亲人更多的快乐。”
毕淑敏文中提到的带给亲人的快乐,我享受到了。在产房外听到母子平安的喜讯,那种高兴激动劲儿是难以言表的,比起当年我生儿子时的感觉,还要激动许多倍。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是庄严而神圣的,创造生命的过程是女性的一项充满艰险的劳动。在看到一个个产妇被阵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们每个做亲人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期盼新生命快快降临。只要大人孩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比什么都好。生,意味着大千世界又增加了一个万物之灵,不付出艰苦的代价看来是不行的。不管是英雄还是狗熊,不管是巨龙伟人还是平民百姓,不管是古代的孔夫子,还是当代的什么星,都是在妈妈的痛苦中诞生的,都是母亲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生命。
经历了几次产房外的等待,让我越发深深感受到了创造新生命的艰辛。生孩子,简直是女人一生中最大的劫难。放眼看看身边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就会觉得,女性,真的很伟大。
写于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