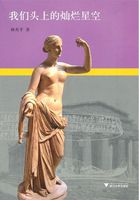就性别行业或工种参与率来说,壮族妇女也不比男性逊色。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证过的,壮族妇女在采集和渔猎时代不仅是野生果实、植物根茎、浅水螺蛳的采集者,也是原始农业的主要发明者;她们还参与某些狩猎活动,特别是当人们学会将动物赶到崖洞或院子圈养的时候,她们就开始成为家庭饲养业的主力。在农业时代,两性行业参与的基本情况是:男子在农耕中占有一定优势,并在陶瓷制造和铜铁冶炼活动中占据主要地位;而纺织是最能表现妇女主体作用的经济活动;在商业活动中,妇女在“赶圩”中占有一定优势,而男子在“商贸”中居于主导。如此看来,壮族妇女在劳动行业或工种上比男性更胜一筹。这一点,我们除了可以从上述《岭表记蛮》和《粤江流域人民史》的有关描述中得到说明外,还可以从《思恩县志》得到直接论证。这本民国时期的县志对壮族妇女所作的评价,在我们迄今所见到史料中是最为全面和最为难得的。它说:壮族“女子颇具特性,不饮酒,不吸烟,不赌博,德性纯粹超过男子之上,其才力亦不让于男子。凡农事工作,男子所能者女子尽能之,且襁负其子作工于烈日苦雨中,较男子为劳。其刺绣纺织裁缝井臼炊爨为女子分内职业者,均克尽厥职。思恩土锦即女子着名手工之一。兼能营商交易,每圩场赶圩之人,男女各半,外来人骤然见之,颇诧异,不知皆为生活问题所驱使也。”这种情况在现今的壮族社会里也还有所表现。据有关部门1958年的调查,西林县那劳区维新乡有如下的分工习惯:男子负责犁田、耙田、挖甘蔗地、打鱼、砍伐木柴、起田坎、放田水等,女子负责挑水、舂米、喂猪、找猪菜、洗衣物、插秧、纺织、做饭、搬柴等,男女共同完成挖地、收谷、剪谷穗等。“这些劳动一般成年人都可以胜任,十四岁以上到年老不能劳动为止都可以做这些工作。壮年一般都做较重的活,如挖地和砍伐木柴等,妇女不能砍,待日久柴干后搬回。老年男人在家做零碎工,或者看牛等。老年妇女一般都从事纺线、喂猪和煮饭、带小该等家务劳动。”[42]随着时代的发展,壮族妇女的劳动行业参与情况正在发生着更为可喜的变化。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资料显示:从1990年至1995年,女性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女性从事脑力劳动(指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三种职业)的比重由4.02%上升到4.30%。这些,对过去性别隔离严重、女性就业集中于体力行业或岗位的情况是一种改变,对女性发挥自身优势与男性开展平等竞争是一种促进。
当然,与女性较高的社会劳动参与率相比,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男女合理的分工协作更有助于消融职业的性别隔阂,从而更能体现和促进性别平等。而从壮族妇女的“忙里忙外”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这样的现象。其中,在历史文献和传说中描述得较多的是男女“共事耕种”。历史研究表明,壮族先民很早就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长期以来稻作农业就是其主要的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相比稻作农业环节多、程序杂,在正常情况下光靠男人或光靠女人都难以进行,必须是较好的分工协作才能顺利完成。刘新翰在《澄江劝农口号》中就有了对“男女共耕”的描述:“叱牛分秧去复回,绿蓑青笠绕江炜。长官亦是农家子,一见良苗开口笑。”据钟文典教授的考证,“男女皆力田”是从各府州县志中经常看到的描述。而经诗《赎谷魂经》也有一段关于男女“协力共耕”的叙述:主家经布洛陀、姆洛甲的指点,从斑鸠嘴里抢得谷种,“拿去育做本,拿去浸做种。申日拿去播,撒在大田里,播在大田中。七月禾含胎,收时很饱满,粒大如柚子,挑一穗不起;夫妻相埋怨,夫妻俩拌嘴;用木锤来敲,用棍棒来打,谷粒裂唰唰,谷粒碎喇喇;撒在大田里,播在大田中。”这仅是把“仙米”变成普通稻种,正常的水稻生产过程是:“二三月交春,大家都早起;初春杜鹃啼,仲春知了鸣;杜鹃叫犁田,知了催播种,蝶舞伴运肥。天上雷声响,雨水落下来,下三天不停,下七天不断;父疏渠灌田,子挖渠引水,水口响哗哗,水进田盈盈。要母牛去犁,要公牛去耙。拿粳穗来踩,拿糯穗来搓;谷种浸三天,四天捞起来;申日拿去播,申日拿去撒。谷种落地生,谷种落地长,秧苗高得快,二十五天拔,二十六天插,妇女扯作束,男人整成把,田中秧如绣,峒中秧似花。三周长成苗,五周可耘田,初耘又复耘。七月禾含胎,八月割谷子。”以上关于水稻生产环节和过程的描述,即使用从现代眼光来看也是较为全面的;其中有一对夫妻因共同抬不起一穗稻子而互相埋怨、拌嘴的情节,颇具夸张和诙谐色彩;而关于交春大家早起、杜鹃叫知了鸣、男女在稻田上共同“描绘图画”的写真,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和谐联想与审美感觉。而唐代之后的壮族春堂舞在表现插秧、车水、打谷时,也经常有“男女间立”等场景的描写。[43]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广西西林县那老区维新乡即使在解放前夕,“男工和女工基本上能做到相互协作的作用,例如男工犁、耙田,女的则扯秧、插秧,男的砍伐木柴,女的取柴。”[44]
男女“共事商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壮族先民也突破小农经济的“樊篱”,尤其是摈弃“不问商贾”的观念。经诗《赎猪魂经》描述到:九头婆造猪成功,王用笼子去要回家,“猪十天十变,猪五天五样。妇女都来看,妇女来问价,猪值十两银。猪生第一窝,得钱买鱼塘;猪生第二窝,得钱买田地;猪生第三窝,有钱养妻儿;猪生第四窝,有钱铸手镯;猪生第五窝,有银来花销;猪生第六窝,有钱去还债;猪生第七窝,有钱做斋事;猪生第八窝,当官去凌云;猪生第九窝,有钱来放债;猪生第十窝,王家旺似火。”显然,经诗对于生产方式的发展是持肯定态度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在性别上的“观照”。首先,经诗已经常出现“布板”(Bouxbuenq,即商人)的概念。《赎水牛魂黄牛魂和马魂经》描述到:王家里的牛死光,用人去犁地,累得全身痛;后来经过“布板”的介绍,到专门的“外阂”(Vaizhaih,即牛圩)才买来所需的水牛。而《序歌(一)》关于大哥“到上边贩马”、二哥“到下边贩牛”的叙述,表明当时“布板”也是一种不错的职业。其次,经诗也有两性“共知商贾”的初步定位。在《赎水牛魂黄牛魂和马魂经》中,买来水牛不仅有“王”的功劳,实际上他在赶赴牛圩前是“妻帮煮早饭”的;而在《赎猪魂经》中,主家卖猪得钱、家旺似火也不仅是男人出的力,妇女也是参与其中的,即她们不仅关注猪的喂养,而且关注猪的价钱和销路。经诗对两性“共知商贾”的定位与史料和现实的情况是相吻合的。《梧州府志》记载:妇人“入市与男子贸易”;《岭外代答》记载:“妇人则黑里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虚市,负贩逐利,率妇人也。”民国时期的《思恩县志》对此的评价是为最高:思恩女子“兼能营商交易,每圩场赶圩之人,男女各半,外来人骤然见之,颇诧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壮族男女一定会有更多的展示“共事商贾”的机遇。
二、壮族妇女的社会劳动影响力与性别平等
社会劳动影响力也叫做社会劳动的参与水平。它既包括男女所从事的职业或工种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地位,也包括男女在同一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还包括男女的劳动生产率及对社会的贡献等。如果结合社会劳动的参与率,并且暂时撇开社会劳动的回报问题,可以说壮族妇女在“忙里忙外”中表现出较强的社会劳动影响力。下面将从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就历史而言,壮族妇女所从事的职业或工种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述,在采集和渔猎时代,壮族妇女不仅是采集者,也是原始农业的主要发明者,她们还是原始饲养业的主力。因此,壮族地区经历过较长母系社会的说法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而不是波伏娃所说的“女人那个黄金时代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神话。”[45]在农业时代,两性行业参与的基本情况及其原因是:在农耕中男女的作用有些差别,但男子所占优势不大,并且是文化因素而不是技术因素造成的;在陶瓷制造和铜铁冶炼活动中男子占据着主要地位,女性话语缺失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选择、自然分工引起的;而纺织是最能表现妇女主体作用的经济活动,男子在此的角色扮演不很突出,这当然有“心灵手巧”等自然因素的作用,但角色期待等社会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否认;在商业活动中,妇女对“赶圩”情有独钟,而男子对“商贸”更驾轻就熟,这是壮族“男主外女主内”的具体表现。从男女所从事的职业或工种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地位来说:壮族是一个以稻作文化为主导的民族,因而农耕活动自然是经济基础的“基础”,而壮族妇女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就是她们给很多人形成“地位较高”印象的原因;青铜冶炼和铁器铸造从主要方面来说是源于农耕的需要,又是社会整合力量的象征,因此女性话语在这个领域中的缺失既是男子主导农业经济活动的一种体现,也是女子在社会整合力量上缺少“刚性”的一种写照;从“男耕女织”二分的社会劳动组织来说,并且从“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理以及人们对“温饱”的高度重视来说,纺织活动对社会发展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因此壮族妇女在此领域的独挡一面,就成为她们与男子寻求相对平等和平衡的最为重要的资源;在壮族的农业社会中,商贸活动不过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并且男女在各自的战线上都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对双方把握社会整合力量的原有格局影响不大。
壮族女性在对社会贡献方面也有与男子“争功”的资格。《宋书·传论》有言:“一夫躬稼,则余粮委宝。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我国男女两性共同推动家庭和睦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肯定。但是,如果用它来描述壮族男女两性的关系,恐怕还是有些低估了妇女的贡献了。远古“母权”盛行的时代姑且不论,就是在“父权”达到颠峰的近现代,壮族妇女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也是超出“男耕女织”范畴的。比如,程大璋在《桂平县志》卷29《纪政·食货中·民业》记载:19世纪末年之前的桂平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及其贡献是这种小农经济的重要力量源泉。她们“中馈饷耕,采樵汲水,陆居者更力作田亩,每日黄昏,则纫麻出棉(以车绞棉条或纱出棉),夜分乃息。农事既毕,机声轧轧,与小儿啼笑之声相杂。大家闺阁,勤于针黹,物不外求”。吕浚堃的《陆川县志》卷4《舆地类三·风俗》记载:“农家之妇女,当耕耘收获时,日则作田功,夜则纺绩……自老至少,绩纺不稍息。”1889年,马丞瑶以广西布政使授任巡抚后,大力提倡种桑养蚕,并在《广西劝民种桑养蚕歌》中指出:“男三棵,女四棵,急早种桑秧。非止老人可衣帛,贸易利无疆。缫出一把丝,换得两月粮;织成十匹绸,起得三间房。”(《马中丞遗集·杂着》)在他的大力提倡和认真推行下,广西的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等得到迅速发展,不仅桂东南如此,壮族聚居的柳州、南宁、百色等地界也取得较好成效,“从而推动了农副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46]据李伯重先生的估算,农家生产一匹布的价值,在清代中期平均等于1.65斗米,这样一个农妇仅从事纺织的日收入就约等于~个农夫日收入的80%。[47]如果考虑在价格上丝绸非一般布匹所比,加上壮族妇女除了“夜则纺绩”之外还“日则作田功”,那么可以说她们对当时家庭、对社会的贡献是不可小视的。依据这样的思考方法,我们还应该从更远久一点的时代来估算壮族妇女在纺织业上的努力以及通过纺织对家庭、社会的贡献。比如,北宋时,广南西路年贡布17.4791万匹,在全国仅次于成都府路及京东路,占第三。《明史·食货志·赋役》说:永乐年间(1403-1424),“以绢、漆、苏木、纸扇、沉速香安、息储、香代租赋”。“农桑丝遍天下,惟不及川、广、云、贵”。到明清之际,除壮锦成为高档供品外,“还有壮布、娘子布、勾芒布、红蕉布、弱锡布、火浣布、桐花布、桃花布、越布等,种类甚多,各呈异彩。产量既增,额贡也大,且常以布类代租。”[48]可见,刘锡蕃说壮族妇女是“立家庭同为经济重要之人物,有时并能赡养男子”,是有其充分根据的。
壮族地区还有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养不起丈夫,枉做一世女人”。联系上述观点来考察,这句很有豪气的话可以说是对妇女较高地位的一种彰显和宣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壮族妇女的社会劳动影响力也在增强。比如,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更多的壮族妇女由昔日默默无闻的家庭劳动力,正在转换为生产的组织者、管理者、决策者。据对邕宁县、百色市400个壮族妇女的问卷调查,成为家庭经济的组织者、管理者、决策者有320人,占问卷人数的80%。与此同时,更多的壮族妇女正在向着当家人、决策者的角色转换。据南宁地区1993年统计,有110多万妇女积极参加水稻高产竞赛活功,种植高产田97.1万亩,占全地区水稻高产田总面积的90.18%;种植玉米高产田27.3万亩,占全地区玉米高产田总面积的56%;改造中低产田面积33.1万亩,平均亩产352.8万斤,比历年增产33.6万斤;种植甘蔗78.79万亩,为农业生产的稳产、高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另外,据对300户壮族家庭的问卷调查,由夫妇双方共同商量决定家庭大事、共同掌握财权的有270户,占90%多。甚至有些妇女的经济收入超过男人,妇女在家庭中说话很顶用。[49]
三、壮族妇女的社会劳动回报率与性别平等
社会劳动回报率是指通过劳动所能得到的经济收入和经济实惠。由于经济收入是一个实证性、统计性的概念,所以人们习惯于从更简单的“经济实惠”来讨论问题。本书在涉及到社会劳动回报率问题时,也主要是从经济实惠来分析,尤其是从财产权、继承权、同工同酬等具有直观性的方面,来探讨壮族妇女社会劳动回报率与性别平等的问题。应该说,相对于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及较强的社会劳动影响力,壮族妇女是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劳动回报率的,即壮族妇女在经济活动中付出多、回报少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与周边汉族相比,壮族妇女的社会劳动回报率也蕴含有较多经济平等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