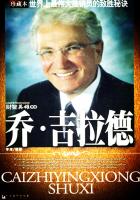“驾、驾——”
一身戎装的袁绍在雪地里纵马驰骋。
胯下之马通身殷红,只在额前有块长条形的白色印记,鬃毛齐整,马尾高翘,肌肉丰隆,两耳挺立,中间饰一铜铃,好一匹天下少有的骏马!
袁绍已经在这片一马平川之地跑了近半个时辰,跟随的人已累得几乎无法勒紧缰绳,但他似乎还意犹未尽。
他现年四十二岁,老话说,四十不惑,此刻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清楚自己的目标,那就是沮授向他建言的:以冀州为根据地,先取并州,再讨青州黑山贼,然后回师北征,平幽州公孙瓒,以四州之地收英雄,集大军,尊皇攘夷,号令天下。
每每想到这个宏伟的计划,袁绍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人人口中称道的“四世三公”,袁绍并不看重,他要为袁氏家族创造新的历史。
他“吁”了几声,马蹄慢慢停歇下来,他挥挥鞭子,从身后跑来一人。
“告诉颜良,军士的训练千万不能松懈,募兵的事也要抓紧。”
“遵命!”那人双腿一夹马肚,急奔而去。
“仲简(淳于琼表字)!”袁绍大声喊道。
“主公!”一个人也大声回道。
“公则(郭图表字)还没来消息吗?”
“禀报主公,还没有。”
“咱们这次举两万铁骑、三万步军攻伐并州,完全能一战而下,但公则劝我少点杀戮,说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如冀州故事。果能如此,那是最好,不过仲简啊,我这心里头没有底。”袁绍用鞭子拍拍自己的胸口,依旧用高亢的声音说着,“那个周襄虽是上党郡的富老,与并州牧张扬也是姻亲,但张扬这个老滑头,苦心经营数十年,会乖乖把并州让给我吗?”
“主公,咱的意思,费那些劳什子干吗,手起刀落,干脆利索。占冀州时,弟兄们就没见血,都憋着一股火呢!”
袁绍沉吟片刻。
“且看公则如何施展吧,开春前若没个眉目,咱就挥师西进!”
“诺!”
“走,回去!”
袁绍回到府邸,迎候他的是最宠爱的张氏,张氏帮他卸下甲胄,又是倒水,又是擦汗,还没等袁绍坐下,又吩咐下人赶紧备饭。
袁绍将玲珑婀娜的张氏搂在怀中,一边吃酒,一边痴痴地凝视这个女人。每次见她,袁绍的心头总是会泛起一丝疑问:都看一年多了,为什么还看不够呢?大概这就是这个女人的魔力吧。
想罢,袁绍突然冁然而笑,放下酒杯,把手伸进张氏的怀里,张氏娇羞地低下头去,轻声说道:
“将军,中午妾身的姨娘来了。”
“哦,有什么事情吗?”
“妾身姨娘家的大闺女,也就是妾身表妹,名唤甄洛,今年也到了婚配的年纪,妾身姨娘来,是想让妾身帮着看看,咱们邺城中有没有合适的。”
“这有什么难的!你看看咱邺城里的官家子弟,有中意的,你就定下。”
“妾身虽不会识字断文,但也知道这婚配之事,乃是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决不能草率。再则,妾身姨娘的夫家乃世家名门,那些个普通的官宦人家,怎么能配上我那表妹。”
“说得也对。”袁绍用满是胡须的下颌摩挲着张氏细嫩的脸皮,笑道,“你心上是不是有主意了?”
“妾身斗胆,三公子袁尚年已二十,却还没有立正室,三公子孔武伟岸,仪表不凡,而我那表妹生得娇脆欲滴,正好相配。”
“这个嘛……”袁绍眯了会儿眼睛,将手从张氏的怀中抽出,凝视着还在冒着热气的酒爵。
张氏的姨父一族,自先祖甄邯以来,世代担任二千石的高官,到了甄逸这一代,虽然远离了官场,但在冀州依然有着无可取代的巨大影响力,与之结为亲家,巩固在冀州的统治,倒也不失为妙方。袁绍对这门婚事没什么意见,唯一让他心起波澜的是,这件事原该由他提出,现在却似乎在被张氏牵着鼻子走。
他若有所思地拿起酒杯,一饮而尽,而后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张氏。
“报——”
一个侍卫跑进大堂,跪在地上,双手呈上一封帛书。
袁绍接过帛书,细细一看,脸上面无表情。
“老弟,看来冀州那一套在张扬那个老狐狸身上不灵了。”郭图耷拉着脑袋,紧皱眉头,“一个不为钱财所动,也不为美色所惑的男人,我不知道他还会有什么弱点,看来是我低估了他,把事情想得简单了。”
“良田千顷,永不征赋,安乐公不做,非得占着提心吊胆的州牧不放,这个张扬,难道是觉得咱们给的条件还不够高?”
还没入幕,周齐却早已把自己当成袁绍的人了。
“要是主公怪罪下来,那可是会被砍头的。”
“我有个主意,不知可行不可行?”
“你且说来听听。”
“宛城一带有支白雀军,洛阳大败后一直躲在鸡宁山上。”
“这事我听说过。”郭图又叫了壶酒。
“所谓擒贼先擒王,别驾是否能遣一人进山,以金银引诱,让他们出一彪人马,无须太多,百人即可,然后扮作百姓进城,为免张扬怀疑,可分批而进,先在各处潜伏下来,然后寻一良机,宰了张扬,群龙无首,并州便为主公所有。”
“这个计策不错,但我担心,一是鸡宁山虽小,但咱们不知白雀军具体所在,不好寻找,即使找到了,是否能为我所用,也不好说;二是并州虽弱,但也有万把人马,一旦反扑,光凭你我二人,难以应付。”
“白雀军的事交给我吧,我想既然他们占山为王,定有喽啰巡山,找到他们应该不算难事,别驾可通报主公,让他陈兵于中山,一旦得手,即刻入城。并州虽有万把人马,但张扬所在的西河城不过三千余人,且驻扎分散,短时间内不可能集合,等主公大军一到,并州再有反复,也掀不起什么风浪,而且,我们也可顺手收拾白雀军,为地方除去一患,为主公赢得人心,岂不一箭双雕。”
郭图思量了一会儿,开怀一笑,拍了拍食案,说道:
“甚好!甚好!就按你说的去办,这事如若告成,我替你向主公请功,主公定会高看你。”
周齐心中暗自得意,这郭图号称“袁门五智”之一,其实也不过如此,还不是得靠我!要是得了头功,那些什么高谋、什么神将,都得拜服,取而代之指日可待,就连袁绍也得敬我几分,言听计从。为了这个,此去鸡宁山即便凶险,这个险也值得冒它一回。
暮色苍茫,他原本想先回陆浑告知胡昭一声,又一想还是先找白雀军为要,便打马南下,歇歇停停,到鸡宁山已是三天后的中午。
鸡宁山比起陆浑山矮了半截,但奇松挺拔,怪石嶙峋,曲径通幽之美景,比起后者更胜一筹,悬崖峭壁,危峰兀立,层峦叠嶂,也毫不逊色,甚至更为险峻。
周齐牵着马上了一条平窄的山道,走几步眼前便散出白色的光芒,那是前阵下的雪还没完全融化。树木虽然秃了,但身在山中,还是会不时被什么尖刺划到衣服,磕磕绊绊走了两刻多钟,总算到了一处开阔地,耳畔传来潺潺流水声。他寻声来到山涧,蹲下身,以手掬水,喝了几口,吃了点身上带的干粮,开始在山上转悠,可直到天色擦黑,也没见个人影。
周齐见天色不等人,而且自己又饿又累,便找了个背风处,折了些断枝残叶,筑起火堆,吞掉剩下的两块胡饼后,拨弄着火堆里的木柴,让火烧得更旺些。他本想就这样挺到天亮,怕可能会有野兽出没,但熬了一个多时辰,就不知不觉间眯上了眼睛。
“那小子醒了!”
“睡得可够死的,这种不长眼的玩意儿,跑到咱山上来,不是送死嘛!”
“也怪咱大帅心善,留着他的性命,我看,把他跟那马一起炖了,还省了咱弟兄的心,大冬天的还得看着这小子,你说冤不冤!”
周齐隐隐听到有人在说话,还不时爆出肆无忌惮的笑声。他缓缓地睁开眼,发现自己被反手绑着躺在草堆上。稍一动,一阵针刺的痛感霎时间传遍全身,忍不住“哎哟”一声,惊动了看守的人。
“小子,睡够啦!”
其中一人冷冷瞥了他一眼,灌下碗里剩余的酒,踉踉跄跄来到周齐面前,一抬腿,在他肚子上狠狠踹了一脚,周齐疼得窝成团,紧咬下唇,大冷天额头竟然淌下汗珠。
那人见状,在他脸上啐了口唾沫,随即从地上一把将他抓起,在他身上挥了几拳,直打得他眼肿皮破,嘴唇冒血。
那人似乎打累了,坐回原处,又跟同伴吃酒划拳,也不管周齐的死活。
过了一会儿,两人吃饱喝足,晃晃悠悠地起身,刚走到门口,一人又转身回去瞧了瞧周齐。
“走啦,走啦,我看都死了,还瞧个鸟!”另一人不耐烦地嚷道。
周齐微张着嘴,像是用力将嘴里含着的话往外抛似的说道:
“我要见你们首领!”
“什么!见咱大帅?你活腻歪啦?”
“我是给你们大帅送钱来的。”
“什么,送钱!”那人起先没注意,稍一回过味来,立刻直眉怒目,双手拽着周齐的衣襟,抽了他一耳光,嘴上骂道,“娘的,送钱!你以为老子是三岁小娃,随你骗!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东西!娘的!”
“哎,这事要是真的,那咱俩不是耽误了大帅发财的机会吗?”
“你倒是信了!”那人白了同伴一眼,“天下哪有这好事,竟有人主动送钱来的?我看哪,这小子说不定是官家的奸细,早结早了。”
说着,就要抽出刀来。
“大帅让留着,你反把他杀了,死了他不要紧,把自己命搭上不值当。咱俩还是先通报大帅,让大帅自己拿主意。”
抽刀那人两眼一翻,觉得同伴说得在理,便收住手,泄恨似的又在周齐身上唾了一口。
没多大工夫,周齐听到外头传来嘈杂的声音,由远至近,周齐觉得耳根有点疼。
“就是这小子?”圆脸用脚尖拨弄了几下周齐,见他还睁着眼,笑道,“小子,钱哪?听说你要送钱给咱?老子活了大半辈子,头一遭遇到这种稀奇事,陈先生,你听说过吗?”
一旁的陈群笼着双手,笑而不答,圆脸也不介意,只顾自己笑着,但在听完周齐此行的目的后,他不再笑了,取而代之的是微锁的眉头。
他有点心动,这的确是一桩好买卖,对方出钱,咱们出力,结伙卖命,为的无非就是这档子事。让他犹豫的是,对方利用完自己后,会不会把弟兄们一锅端了,人心险恶,他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依照陈群的意见行事后,他现在手底下又有了近七千人马,身为大帅,这些爷儿们的命虽说都是他的,但也不能糊里糊涂地给弄没了!
回到道观,他征求陈群的意见。
陈群心中早有了主意,这是一次极好的脱身机会,虽然他瞧不上袁绍,但总比跟着与土匪无异的白雀军强,别看现在他们对自己客客气气的,哪天保不齐就会下杀手。贼人素无常性,多待一天,就多一分危险。
“他们现在是有求于大帅,袁绍这样一门大户,也不会在乎那点钱财,我看,这事可以做,大帅不必多疑。”
“咱要是帮了袁绍,西凉的事又怎么交代?”
“大帅借助西凉的势力,无非是为了替死在洛阳的弟兄们报仇,这事可急可缓,等得了钱财,再招兵买马,不靠西凉,大帅也可报洛阳之仇。”
圆脸眨眨眼,挠挠耳朵,一屁股坐在地上。
“咱就怕着了道!”
陈群心想,只有你着了他们的道,我这才能出你这贼道。
“大帅,杀杀打打,提着脑袋过日子,这其中的心酸苦痛,你是最了解的,今天还在一块儿喝酒的弟兄,明天可能就死了,你说难受不难受!”
“那是,那是,先生说得对!有好日子过,谁还干这拿命换命的营生!”
“在山上是以命换命,下了山也是以命换命,同样都是以命换命,所得却相差万分,你说哪个更划算!”
“先生,你别说了。”圆脸像是被谁刺了一下,急忙从地上跳起,“干!干它一票!”
第二天一早,圆脸清点人马,照着周齐的部署,开始行动。周齐虽然受了侮辱,身上多处挂了伤,但他还是很高兴,换作谁都会如此。
陈群看在眼里,嘴角一抽动,从腰间解下玉环放到周齐手中。
“你这是干吗?”
周齐要把玉环还给陈群,陈群急忙拽住他的手,摇摇头,示意他不要声张。
“这是送给你的,我只求你一件事。”
“哦?”周齐疑惑地看着陈群,一只手却已将玉环塞进了怀里。
“进城后,请让我与公则相见。”
“你们相识?”
“同乡而已。”
周齐见他一身士人打扮,器宇轩昂,谈吐淡定,料想可能是这帮贼人掠去的读书人,又称与郭图是同乡,都说颍川多奇士,还真不能小瞧了他,也许以后还用得上,于是他突然热情起来,说一定办妥。陈群也不多说什么,只是拱拱手,以示谢意。
陈群与二十来个白雀军夹在百姓当中进西河时,守门的兵士除了念叨几句“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外,也只是进行了例行检查,并没有想象中那般严密。
城内人来人往,热闹拥挤,一派繁荣景象。
过不了多久,这里又会是另一番天地吧。陈群环视四周,多少有些伤感,他决不是那种容易触景生情之辈,只是当他想到,眼前这些贩夫走卒,妇孺老小,说不定什么时候便会丧命于刀下,他就难以自禁。
“怎么了?”周齐问道。
“没事,想起了一个朋友。”
“跟我走吧!”
“那些人你都安排好了?”
“郭别驾派人接应,一部分各自找客栈住去,一部分去了城西郊刘老爷家,他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富户,充看门护院的家丁,不会招旁人怀疑,还有五人随我一起扮作郭别驾的随从。”
“你办事有些章法。”
“哪里,还有得学。”周齐客气地回道,“郭别驾的意思是,等人齐了,他择日以献礼为名去见张扬,张府对面是家酒肆,后院出门是条胡同,周围没有住家,只有一座破庙。郭别驾都打点好了,到时在酒肆和庙里埋下人马,为防意外,郭别驾还买通了张府管家做内应,他答应到时撤去府内的护卫,那时张扬身边只有手无缚鸡之力的婢女和老仆。剩下的白雀军则去解决城门的守卫,以烟火为号,而后主公率五万大军杀到,大功告成!”
西凉冀城,征西将军府内,灯火闪耀,亮如白昼。
一身便装的马腾斜靠榻上,瞥了眼立在身旁的大儿子马超,马超的身后依次站着一脸肃然的二弟马休、三弟马铁、堂弟马岱,右边马扎上坐着的是马腾的结义兄弟,镇西将军韩遂。
马腾见人都到齐了,坐起身,说道:
“袁绍夺了并州,灭了白雀,这样一来,袁绍的势力又扩张了不少,而我们想要联合白雀,再攻长安的计划也泡汤了。接下来怎么办,大伙儿合计合计。”
“父帅,既然袁绍势大,咱们就跟他联合灭了李傕!”
“你没看到白雀军的下场吗?”韩遂双手搭在膝上,道,“这年头,谁都不能相信,还得靠咱自己。西凉大马,横行天下,只因一次失利就畏首畏尾,未免太小瞧了自己。”
韩遂说这句话时虽然冲着马超,但显然,他是讲给马腾听的。在他看来,自从年初失利后,他的这位盟兄就显得格外谨慎,可别忘了,西凉还有二十多万兵马!
马腾听得出韩遂话里的意思,只是笑笑,站起身。
“这样吧,咱先看看袁绍的动静,再作计较。”
等韩遂走后,他叫住马超。
“超儿,你往后要多留心点你韩叔的事。”
马超不太明白父亲的话,但也没多问,点点头,深深施礼,骑马走了。
马超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于眼前,长长地叹口气,心中想道:超儿啊,以后的路,全得靠你自己走了。
年届五十的马腾,戎马半生,身子骨虽依旧硬朗,脸上还是掩不住岁月的刀劈斧凿。也不知为什么,自从年初在长安败于李傕之后,对杀伐之事越发觉得倦怠,一匹狼失去了孤傲的眼神,不再以获取猎物为乐,说明它老了。马腾已做好打算,等灭掉李傕一伙,就表奏朝廷,让马超继承他的官爵。
这晚,他又一次失眠了。
与马腾同样无法入眠的还有远在两千多里外的周齐。
原本他打算今天离开陆浑山,他以为这是理所应当之事,不承想竟遭到对方拒绝。
“并州初得,主公诸事繁忙,你的事等等再说。”
“别驾是想背弃诺言吗?”
“你莫多想。”郭图的脸上浮着惯有的笑容,他让周齐坐下,“少安毋躁,少安毋躁。这次并州能顺利到手,你的功劳最大,但主公除了下令赏赐你五百金外,并无其他表态。我看既然主公无意,你入幕后,也得不到重用,这不是与你最初的设想相悖吗?我劝你还是忍耐些时日,等时机成熟我再为你引荐也不迟,你现在正当年轻,时间对你来说,不是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