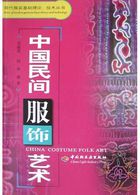渡江时间“学问”多
瑶岗的4月,蒙蒙细雨一连下了几天,周围的树林、村庄始终裹在浓浓的雨雾里,地面也成了一片汪洋。
邓小平立在窗前,望着院子里淅淅沥沥、没完没了的淫雨,心急如焚。他不时地在屋子里踱着步,额头上沁出了一,丢细细的汗珠。
几天来,北平谈判的前景时明时暗,中央的电报也一个接一个。这几天,他一方面密切注视着北平的谈判,一方面又关心着部队的渡江准备工作,他的心一直绷得紧紧的。
4月10日,军委来电说:“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
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渡江时机,这正是邓小平、陈毅着重要掌握好的主要环节之一。他们立即搜集各方意见。并亲自作调查。各路大军上报的意见都相当严峻:
二野:长江水势4月末5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三野:4月下旬起开始雨季,江水日涨,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江中行驶困难,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粮草困难。
总前委本身调查的结果是: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
于是,总前委建议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
中央军委在坚持政治斗争必需,又充分考虑到渡江的客观情况下,于4月11日电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并对这一点再次“请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张震即日电告自己的意见。”
军委的电报传到了陈毅、邓小平手里,传到了粟裕、张震手里,传到了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手里,也传到了谭震林的手里,但是由于他们不在一处,所以无法对此进行讨论。
粟、张在江苏泰州以南白马庙三野指挥所,负责指挥东集团。
刘、张、李在安徽舒城二野指挥所,负责指挥西集团。
谭震林在安徽庐江第7兵团指挥所,负责指挥中集团。
陈、邓坐镇合肥郊外总前委。
邓小平拿着电报,对陈毅说:“陈老总,你看我们如何答复中央?”
两人商议的结论是:“如在22日前渡江,尚无大问题,如再推迟一一礼拜到29日,则困难不少”;“从军事上说,以22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即使政治上必须,也以不要推迟到29日以后为好。”
向上面的回复就这样决定了,可怎么向下传达呢?怎么告诉部队推迟渡江的原因?军委在电文中曾提到:“你们下达推迟渡江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邓小平、陈毅对此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他们以总前委名义给两个野战军和各兵团党委作了指示。完全不回避“为了谈判”,而是正面说清楚渡江与谈判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他俩的办事风格。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一二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任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对方不执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的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错误,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凭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这份电文是4月12日下达并报军委的。军委于4月14日复示说: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甚好。请二野、三野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军委还告诉陈、邓对和谈的一些看法,电报中说:“我们现在要李、何、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五人来北平共商。如彼等不来,则由张治中派人回南京征求意见。如南京根本拒绝,不愿签字,则争取张治中代表团签字,然后由我军渡江,威迫南京批准。如果南京因受美蒋胁迫不敢批准,并逃往桂林,则将协定公布,号召一切国民党主和派分子(单南京立法院即有一百多个立法委员认为无论如何要和,并谓非共军渡江不能解决问题)拥护协定的执行。万一连张治中也不敢签字,则其曲在彼,我方可将协定草案公布,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对我军南进甚为有利。
而我军损失,不过推迟七天或十天,至多十二天的时间。”
从上述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和谈与推迟渡江可能的有利与不利影响,考虑得十分周到和细密。
4月16日,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和第三、第二野战军领导:
“你们的立足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与此同时,电报中分析了和谈签字时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又一次涉及面临某种假定情况时的渡江时间问题,“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政府愿意于4月20日签字,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22日改至25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25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如何?请考虑复电,并将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见告为盼。”
这时,恰巧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和两位兵团司令王建安与宋时轮来到总前委。陈毅、邓小平倾听他们的想法。
第7兵团司令王建安抢先发表看法:“继续推迟比较困难,部队已经做好了20日渡江的一切准备,现在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如果推迟几天,我担心会松了劲,短时间难以恢复。”
“我们不必对国民党一再让步,打给他们看看。只要我们一渡江,他们也许才会答应签字。”宋时轮在一旁语气坚定地说。
谭震林也不同意继续推迟渡江的时间,他说:“大兵团作战,最怕犹豫不决,兵法说,‘一鼓作气,再而衰’,只要国民党20日不签字,我们立即发起进攻。”
邓小平和陈毅二人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须的情况下,不能推迟渡江的时间。延长一天时间渡江,困难就增加一分,影响士气,特别是有可能会暴露渡江的地点。
在这期间,总前委办公室单独增设了一台“克劳特”无线电接收机。这是淮海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
为了侦察国民党军队的动态,邓小平指示通信参谋开通接收机,全波段侦听敌人的电台、广播。负责侦听工作的两名报务员日夜轮流,仔细监听,认真记录下国民党电台发出的每一个信息,然后,直接交邓小平、陈毅审阅。4月17日,邓小平从报务员的电台记录中发现了一条极有价值的信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成立由汤恩伯兼主任的政务委员会。
邓小平急忙叫道:“陈司令员,看来蒋介石是不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了!”
陈毅看罢电台记录,赞同地说:“唔,你说得对头。这叫狗改不了吃屎!我看,渡江不必再等下去喽!”
总前委仔细研究以后。当日给军委发报:
我们一致认为确定(21)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而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做最后抵抗,此种征候已日益明显。今天南京广播,汤恩伯总部之下组织京沪杭政务委员会,汤兼主任,谷正纲、邓文仪等为常委,即其具体步骤之一。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我们渡江成功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须的条件,务请不再推迟至25日。
2个小时后。军委复电:我们铣辰(16日9时)电问你们是否可以由22日改为25日渡江,是假定南京同意签字,并且假定20日确实签了字而要求我方给几天部署时间而说的,并非一定要改至25日。南京是否同意于20日签字,决定于美国及蒋介石的态度,因此把握不大。南京方面认为我军渡江有很大困难,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够大举渡江。我们估计他们20日以前可能不理我们,要看一下我军能否于20日以后真能渡江。假如我军真能于22日渡江成功,则协定仍有可能于二十三、四、五等日签订。故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22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
中集团一马当先
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在总前委谈完意见回到前线,又一次检查督促部队的渡江准备工作。
4月17日晚,宋时轮在无为东南神塘河召集军、师干部开会。
27军军长聂凤智说:“据渡江先遣大队的侦察报告,当面敌人第88军正与第20军换防,这几天特别混乱。是我们渡江的有利时机。”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曾要求各部队,在大规模渡江前,要先饥夺取江北各桥头堡及各江心洲据点。25军军长成钧说:“司令员,我们现在是先于20日攻打黑沙洲,然后22日再发起总攻,这样做不好。分两步渡江会失去突然性,敌人会做好准备。”
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建议:“干脆就在20号晚上,攻打黑沙洲的同时。将大部队同时渡江,打他个措手不及。”
宋时轮听大家说的有理,就说:“我给郭政委打个电话,请他立即报告总前委。如果上级同意,我们就这样干。”
总前委接到报告后,立即向中央军委请示。
4月18日9时,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军委的电报特别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4月20日,中集团。
渡江战役进入倒计时。已是傍晚的指挥所里,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久久地立在窗前,两眼注视着窗外,正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
再过几个小时,中集团渡江总攻的时间就要到了。这是整个渡江战役的第一枪。中集团渡江作战的位置在裕溪口至姚沟段和姚沟至枞阳段。中集团渡江作战如能成功,就可以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拦腰切断,策应东、西两个突击集团的强渡。同时,还可以控制宁芜铁路,使人民解放军挥师东进,直捣国民党反动派老巢——南京。很显然,中集团能否一举突破敌人的长江防线,对整个渡江作战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他是中集团的第一号指挥员,总前委和中央军委把渡江战役这最关键的“第一枪”交给了他,怎能不让他怦然心动?时针在表盘上一分一秒地划过,“嗒嗒”的钟表声如同一把钢锤,有力地敲击在他的心口上,此时此刻,谭震林的心情就如同已处于起跑线上的百米赛跑的运动员——发令枪马上就要打响了。
担任中集团第一梯队渡江任务的是第25军(芜湖一三山街段)、第27军(荻港一姚沟段)、第24军(铜陵段)、第21军(贵池段)。
中集团渡江对岸的繁昌、铜陵这一段的地形比较复杂。国民党军队利用优越的地势,在悬崖峭壁上挖掘地堡,居高临下,虎视江心。有的在江堤腰上的大缝处开设枪眼,横瞰江面。在黑沙洲东北部的险要处,还设置了一个平射炮连。
险要的地形对解放军登陆虽然带来困难,然而时机的选择却非常有利。此时此刻,敌第88军正在交防,敌第20军正在接防。敌换防没有完成,江防任务不明确,在一些地段上一时出现空白。这对解放军顺利登陆是极好机会。
中集团的突击开始了。
夜幕中的江面上,上千只木船竞渡。炮弹爆炸掀起的根根水住,在敌人探照灯的光柱闪动之下,跌落下来,像一朵朵巨大的水花。从江北看去,每只船后都挂着一盏红色指示灯,如火光点点。整个渡江场面宏伟壮观,激动人心。
由于天黑,船多人多,为了便于指挥,当天晚上突击队出发的信号十分简单:就是紧跟着“头船”行动。“济南第一团”一个战斗小组的战士,夜幕下俯在船上隐隐约约地看到处于战斗位置的“头船”开始挪动,便误以为是出发的信号,于是慌忙大声叫道:“头船出发了!”说罢,便挥起铁锹,用力划起船来,船像离弦之箭,“嗖”地一声跃出待命的行列。第三战斗小组、第四战斗小组……紧随其后,飞快地向江中驶去,大家都想争得“渡江第一船。”
而今,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保存了一条当年渡江用的船。人们说它是“渡江第一船”,驾驶这条船的船工名叫张孝华。
张孝华是一位阶级仇恨很深的贫苦船民。他从12岁起,就跟父亲上船开始水上生活。在长江上下行船20余年,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渡江时,张孝华被编在第一突击队第一组第一只船上,担任组长。他这个小组的另两只船,一个船工叫张孝寿,是他的同族兄弟,另一个船工叫沈先发。张孝寿和沈先发的船,在张孝华的左右两侧,连长在张孝华的船上,是突击队的指挥员。指导员在沈先发的船上,作为连长的后盾,紧随一侧。
4月20日晚上,渡江命令下达后,张孝华战斗小组的船,如同利箭,在隆隆炮声中成直线直刺江心,猛扑对岸。张孝华在船尾,稳稳当当地握着舵,同时保护着三方不见亮,一方闪红光的信号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