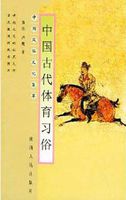北京是感性的,倘若要去一个地方,不是凭地址路名,而是以环境特征为指示:过了街口,朝北走,再过一个巷口,巷口有棵树等等。这富有人情味,有点诗情画意,使你觉得,这街,这巷,与你都有些渊源似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凭亲闻历见认路的,他们也特别感性,他们感受和记忆的能力特别强,可说是过目不忘。但是,如果要他们带你去一个新地方,麻烦可就来了,他们拉着你一路一问地找过去,还要走些岔道。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则有着概括推理的能力,他们凭着一个路名,便可送你到要去的地方。他们认路的方法很简单,先问横马路,再弄清直马路,两路相交成一个坐标。这是数学化的头脑,挺管用。北京是文学化的城市,天安门广场是城市的主题,围绕它展开城市的情节,宫殿、城楼、庙宇、湖泊,是情节的波澜,那些深街窄巷则是细枝末节。但这文学也是帝王将相的文学,它义正辞严,大道直向,富丽堂皇。上海这城市却是数学化的,以坐标和数字编码组成,无论是多么矮小破陋的房屋都有编码,严丝密缝的。上海是一个千位数,街道是百位数,弄堂是十位数,房屋是个位数,倘若是那种有着支弄的弄堂,便要加上小数点了。于是在这个城市生活,就变得有些抽象化了,不是贴肤的那种,而是依着理念的那种,就好像标在地图上的一个存在。
北京是智慧的,上海却是凭公式计算的。因此北京是深奥难懂,有灵感和学问的;上海则简单易解,可以以理类推。北京是美,上海是实用。如今,北京的幽雅却也是拆散了重来,高的京剧零散成一把两把胡琴,在花园的旮旯里吱吱呀呀地拉。清脆的北京话里夹杂进没有来历的流行语,好像要来同上海合流。高架桥、超高楼、大商场,是拿来主义的,虽有些贴不上,却也摩登,也还是个美;上海则是俗的,是埋头做生计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这生计越做越精致,竟也做出一份幽雅,这幽雅是精工车床上车出来的,可以复制的,是商品化的。如今这商品源源不断地打向北京,有看一举攻城之战势。
二、杨东平:两地人互看
几乎绝大多数上海人对北京人无可评价——由于缺乏实际的接触、具体的感受。“到北京去”在十来年前,还属于少数先进人物的光荣和骄傲。近年来,到北京出差、旅游的上海人增多,但对北京的共识也只是枯燥的几条:一是风景名胜比上海多;二是新建筑多,高楼多,其后跟一句牢骚“怪不得上海没钱盖房子”;三是购物、坐车不方便,商品品种少,价格贵;四是气候干燥、刮风,不适应。
一位上海人说,到大名鼎鼎的王府井,没想到走了几十分钟,就逛到头了。他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问别人“北京究竟有几个王府井?”关于服务态度,上海人说,上海的售货员至多不理你,自顾自聊天。北京的售货员还要训你:“你嚷嚷什么!”上海的儿童在北京则经常会有意外的惊喜——他们在大街上看到了拉车的活生生的骡、马,往往怀疑它们是从动物园跑出来的。
对于每个从北京来的人,上海人都会问:“上海好还是北京好?”在北京则很少遇到这种提问,因为对北京人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中国还有比北京更好的地方吗?其实,上海人的询问也没有城市优越感,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验证这一优越感;此外,则是潜意识中对京城模糊的崇敬和神秘感。
比较而言,北京人对上海人的感觉要多得多。几乎每个北京人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对上海人的印象,自然,好评不多。北京的女性尤其热衷于对上海男性的声讨,而且众口一词,仿佛个个苦大仇深。上海自然有对北人的轻蔑,例如称北方人为“北佬”,但通常,北京人被单列在这种称呼之外;而北京人并没有对南人共同的蔑称,而是将上海人单列——当他们说“他是上海人”时,口气中已经包含了轻蔑,有些像西方人说“犹太人”那样。以致于在京城的上海人不轻易暴露籍贯是比较明智的;但在江南,上海人的籍贯却具有自我提携的功用。直到80年代初,南京、杭州、无锡等地的时髦青年仍以会说上海话、打扮像上海人为荣(而他们在上海的同类,则以打扮成“华侨”为荣);至今上海的征婚广告上,“沪籍”仍是可开列的条件。电视剧《渴望》中那个自私委琐的男主角被取名“沪生”,引起了敏感的上海舆论的不满,却满足了北京人的集体认同,他们觉得:上海人就是这样的。因此,北京人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便是“你不像个上海人”。
但是,在北京人的内心,仍有对上海人、对南方传统的尊重。因而,谈及上海同行的工作质量和工作精神,北京人往往自认弗如。而声讨完上海人的北京姑娘,有时会出其不意地流露:“我妈妈(或外婆)也是南方人”;或者“我有个阿姨在上海”,“小时候在上海住过”等等。北京的孩子到了上海往往备受宠爱,人们惊讶于他们一口纯正的“国语”。如果他转学到上海则会经常地被教师提问,并让他朗读课文。
上海人和北京人交往中的“文化冲突”,相互间的成见和抵触之深,也许超过了我们的预料。
余秋雨撰文剖析了“上海人的尴尬”“全中国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上海人。这种无法自拔的尴尬境地,也许是近代史开始以来就存在的。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漠、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市侩气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的确,北京人对上海人的看法,是代表了“北方人”和“外地人”的普遍看法。
北京人津津乐道于上海人的洋相笑话,包括半两粮票的小点心;一次买一只苹果边走边吃。还传说上海人到北京吃涮羊肉(他们往往念成“刷羊肉”),10个人要了2斤,北京人说:“趁早别现眼了,还吃涮羊肉呢!”此外,他们又反感上海人关于自己特别“秀气”的声明:上海人老是说:“我只吃一眼眼”,实际比谁吃得都不少。经常参加会议、吃会议餐的人反映,上海代表在饭桌上的表现往往较差,他们不顾别人地抢食最好的菜(如大虾),一副“不吃白不吃”的架式;而轮到拍集体照时,他们又当仁不让地占据最“风光”、最显眼的位置。
北方人传播的一个关于上海人的经典笑话,说一个上海儿童去商店买针,针的价格是2分钱3根,小孩付1分钱,给了他1根针,他却不走,对售货员说:“你还得找我两张草纸。”另一则不是笑话,说上海人待人真热情,快到吃饭的时候,他告诉你附近有一家价格便宜又实惠的饭馆。
当北京人无意触犯了上海人某些“不成文”的规矩时,就会出现不快。例如,前些年的结婚宴席上,最后上的“四大件”(全鸡、全鸭、全鱼、蹄膀),客人往往是不触动的,留待主人用钢精锅装回家去慢慢享用。一位北京朋友抱怨,上海人家里,一条鱼要吃四顿:切成两段,每次只吃其中一段的一面。而他“破坏”了留待下餐的另一段鱼。他说:“从此在上海人家里做客,我不吃鱼”。
当上海人把自己的规则带到北京时,同样会发生难堪。
一位上海女学生参加一群北京青年的郊游,事后,她将所吃的面包、汽水、冰棒等的钱如数交付,使北京女友大为恼火。这种上海人的“经济自觉”正是北京人所嘲笑的“小家子气”。另一位毕业分配到京的上海姑娘,邻居怜其孤单,时常请她吃饺子等。后来,北京的主妇发现了“规律”每次请她吃过饭之后,她总要回赠一些豆腐干、香肠之类的“小礼品”。主妇不禁大怒:“我是可怜你,你倒和我算起账来。要仔细算账,你一袋豆腐干够吗?”上海人的乖巧知礼,在这里被视为小心眼和冒犯。
随着交往的增加,大多数上海人都会感到北方人更易于相处,没有那么多鸡鸡狗狗、不上台面的小心眼、小动作;而北方人也会感到,上海人并非如表面表现得那么不可交。
一位东北籍朋友谈起上大学时的一位上海同学。他衣冠整洁,独往独来,从不与同学一起看电影、吃饭,以免无谓地请客花钱;他从不言人恶,不涉是非,也不露个人隐私,与所有同学都是“淡如水”的等距离外交,绝无北方哥们结团抱伙、烟酒不分家的作风。起初,这种与众不同很令人反感,但时间长了,别人却感到与他交往比较轻松和安全。另一件表明其性格的小事是:他看书如遇不认识的字,绝不会嚷,或向别人求教,而是自查字典,这既避免了“露丑”,而且从字典查出的结果更准确、更权威。
一位北京教师后来认识到,上海人的精明和算计作为一种习惯,不独自己享用,有时也施于人。他在上海乘车问路,答者详细地告诉他,所去之处介于A、B两站之间,在A站和B站下车均可,但到A站5角,到B站1元,所以还是到A站下车为好。这位教师深受感动。
对于许多当年的知青,“五湖四海”的集体生活无疑是各地人习性、各种城市人格的大交流、大碰撞和大展示。
一位当年在东北兵团的北京朋友说,上海人最令人“腻味”之处,是他们互相用上海话交谈,这等于是公开宣称自己与众不同,用语言与其他人隔离。上海人固然精明,但是精到明处,也许不可交朋友,但却可以共事。他们有时要小心眼,晚上工,早下工,贪个小便宜,但并不坑人。上海知青搞政治小动作、玩小阴谋的并不多,北京人中反而较多。哈尔滨人最野,打架厉害;但形象最次的是天津人,他们最会斗心眼,打小报告。上海知青大多没什么背景,但他们自我料理能力强,干净,办事有规律、有准备。很多人靠一技之长(例如会修收音机、会写美术字等)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调到较好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