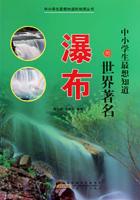起风了,那串风铃丁零丁零响了起来。铃声响在秋天午后纯净的阳光里,听上去,有一种深入人心的温馨和单纯……
最最没耐心的是铜锣。
自上回被青榴追打知道了她的厉害后,铜锣就没敢再欺负她。但他心里一直窝着火,特别是那天在吊桥上被我们晃得跌跌撞撞,更是愤愤不平,一直都在伺机报复青榴。光天化日他不敢了,况且青榴在晚会上唱歌之后,人气渐长,有不少同学喜欢围着她转,好像对她的兔子嘴巴也视而不见了。
可是,从青榴戴着大口罩走进教室的那一刻起,铜锣心里就升起了一片希望,这希望像野草般一天天地疯长,铜锣被它们缠住了,无法脱身。
后来他才知道,被“野草”缠住的还有陶丽丽。
陶丽丽是语文课代表,这天收作文本收到铜锣时,铜锣朝她翻翻眼说:“没做,忘了。”
“忘了好啊,明天交两篇。”陶丽丽板着脸说。
铜锣求饶:“我中午补,下午给你,行行好。”铜锣最怕写作文了。
“不行,写了就现在交,没写就罚一篇。”陶丽丽一点都不肯通融。
这时,青榴走进了教室,仍旧戴着大白口罩。不知为什么,这一刻陶丽丽看着那大白口罩觉得格外扎眼,就没好气地说:“不罚也可以,除非你把兔婆婆的口罩摘下来!”
“说话算数?”铜锣兴奋地瞪着陶丽丽。
陶丽丽用力点点头,眼睛闪闪发光。
这其实是铜锣每时每刻都想做的事,他太想知道口罩捂着的是怎么样一张嘴了。看来,陶丽丽也想知道,也许比他想得还更厉害。现在,他做这件事是一举两得的,他太愿意、也太值得去做了。
他朝青榴走去。
青榴对铜锣的阴谋一无所知。
青榴走向自己的座位,她看见我已经来了,正用眼睛和我打招呼。我想提醒她,已经来不及了。
铜锣与青榴擦肩而过时,青榴好像瞥见了铜锣眼睛里隐藏的一丝坏笑,下意识地警觉起来。可已经晚了,铜锣突然一伸手,将青榴的口罩扯了去,青榴“哇”地惨叫一声,赶忙用手捂住嘴,蹲在了地上。
青榴的惨叫震耳欲聋,所有人都惊呆了,包括铜锣和陶丽丽。
与此同时,肖老师出现在教室门口。
听见叫声,看见深埋着头蹲在地上的青榴和仍抓着青榴口罩的铜锣,肖老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她奔过去,想把青榴拉起来,但青榴一个劲地往下缩。肖老师对大家说:“你们都站到教室后面去。”
看看身边没人了,肖老师才附在青榴的耳旁轻柔地说:“身边没人了,让我看看好吗?一定非常好,相信我。”
青榴慢慢地抬起了头,可一只手仍旧捂着嘴。
肖老师将自己的手盖在青榴的手上,然后,将它一点点移开。
青榴还在反抗,但反抗得不坚决,犹犹豫豫的……终于,青榴的脸完整地展露在了肖老师面前。肖老师瞪大眼睛,十分惊讶地望着她……
我紧张地盯着肖老师,不知她那样的表情意味着什么。
青榴好像也没有读懂肖老师的表情,她的背僵直着,一动也不动。
肖老师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了,她猛地扳过青榴的身子,让她面向大家,欢欣地嚷道:“看看,大家看看!”
青榴本能地想逃,可肖老师死死地抓住了她的肩。
教室后面挤满了人,不光是本班的同学,还有别班跑来看热闹的同学。但大家都像刚才铜锣扯掉青榴的口罩时一样呆呆地望着她。
终于,我忍不住了,朝青榴跑了过去,一把抱住了她,然后,使劲地晃她,边晃边兴奋地叫道:“太好了,青榴,你不知道你现在有多漂亮!”
“真、真的?”青榴看着我,又看看肖老师和其他同学,迟疑地伸出手去,小心翼翼地触碰自己的嘴巴,就像触碰一朵刚刚绽开的花儿。
“给你这个。”有人递过来一面小圆镜。
青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不及待地需要这个以前她避之不及的东西。她一把夺过镜子,照着,望着她的唇——完完整整的唇,只在上嘴唇中间有一道宽宽的但并不显眼也并不难看的疤痕。
青榴看见了一如她所期待的、在她看来是非常完美的唇……可是,如果笑起来,笑起来会是什么样子?于是,她笑了一下——先是微微一笑,然后把嘴一点点咧开,笑得更灿烂一些,露出整齐的贝牙。真好看,可以这样笑了。如果把嘴张得更大一些,笑出声来呢?
青榴本想试一试,可还没等她笑出来,就发现镜子里的人哭了——镜子里的人笑逐颜开同时又泪流满面。
“看你看你,哭什么嘛哭什么嘛!”我兴高采烈地嚷着,用手去替青榴擦泪;青榴也伸过手来替我擦,我才感觉到自己脸上也是湿漉漉的……
我第一次明白了,流泪并不只是代表伤心,高兴极了也会流泪——现在我就高兴极了,为青榴。
其实,不仅仅是我、肖老师,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为青榴高兴,包括陶丽丽。我注意到,那面小镜子是她递过来的——除了她,班上有谁会随身带面小镜子呢?而且,她也早已完完全全忘了是她鼓动铜锣揭的口罩。
不过也许铜锣除外,他愣愣地看了一阵,嘟哝了一句:“又哭又笑,王婆拉尿。”就走开去了。
我一个人来到藏书楼的后墙,将那块松掉的木板抽掉,钻了进去。
我照例在那排书架前流连了一番,在淡淡的灰尘味中随意地翻了几本书,然后径直来到了最上一层的阁楼。我是第一次一个人来,但一点也不害怕。既然知道了唱歌的是青榴,就没有什么好怕了,只是青榴永远也不会来这里唱歌了。
没有必要哦。
现在她可以在任何场合唱,在音乐课上唱,在课间休息时唱,在晚会的大礼堂唱,在上学和回家的路上唱,做饭洗碗的时候唱,甚至,上厕所的时候都可以哼哼。当然,青榴最风光的是去县里的广播电台唱。
“六一”节,广播电台要做一期少儿节目,要学校推荐几个同学去录歌。肖老师是学校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她推荐了青榴、陶丽丽,还有其他班的几个同学,结果,青榴被选中了。“六一”节那天的下午六点半,所有听众都听到了青榴那欢快而甜美的歌声。
云婆婆没有听广播的习惯,家里没有收音机,我就让云婆婆问别人借了一个来听。青榴唱歌的时候,我把音量开到最大,搬了张凳子坐在门口听。从门前走过的人,只要我认得,就十分神气地对人家说:“知道是谁唱的吗?青榴,我的同学。”
云婆婆见了就嗔道:“看你疯的,又不是你唱的!”
“青榴唱的又怎样?我不该高兴呀?”我顶她。
云婆婆白了我一眼,不理我了,但我明明白白地看见,她的嘴角是含着笑意的。
我是真的很高兴,替青榴。虽然,我们在一起玩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青榴参加了学校的文艺队,放学后常常要排节目。课间的时候,青榴也不再是孤寂的了,好些同学会过来和她说话,夸她歌唱得好,人也越来越漂亮了。
青榴确实是越来越漂亮了,上嘴唇的那道疤在渐渐地变细,变淡,唇形越来越完好。原来,她对人总是提防着,抗拒着,排斥着,可那只是一张假面具,那张假面具在铜锣扯掉口罩的那一刻就被彻底粉碎了,快乐的、漂亮的才是真正的青榴。
我当然愿意看到青榴这样,可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落寞。当青榴身边围了好多人而她们说的话题我又不感兴趣时,我就会走开,走到石桥上,趴在护栏边看池塘里的红鲤鱼。
陶丽丽从桥上走过看见了我,奚落道:“她风光了,不跟你玩了吧。”
我瞪着她,不知如何反驳。
陶丽丽嘻嘻一笑,走过去了。没走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你可以和我玩哪。”
我扭过头去,不理她。
那天,陶丽丽拿镜子给青榴看时,我其实有点喜欢她了,可我一直都是一个嘴讷的人,不知如何表达,也不会主动去和她亲近。但今天陶丽丽这样的腔调又让我很不舒服。
我闷闷地走回教室,正好上课铃响了,青榴身边的人都散去了。在老师进来之前,我突然有些冲动地对青榴说:“放学后我们去藏书楼玩,好不好?”
“好啊。”青榴爽快地答应了。
我舒了口气,然后专心致志地听课。
可是,等到放了学,我只是去办公室交了一下本子,回来就不见了青榴。以为青榴去厕所了,等等不见来;又以为她去排练了,可到礼堂一看也没有人——今天不要排练,要不青榴会告诉我的。
青榴……她忘了?
想到这一点,我有点难过,有点委屈。为了让自己不那么难过,不那么委屈,我决定一人去藏书楼。
好久没来了,阁楼上的香案和长凳都落了厚厚一层灰。我撕了几张草稿纸,将长凳擦干净,灰尘腾起来了,从窗口射进来的一束阳光顿时喧嚣起来,像飞翔着无数的小星星。有时,又是一阵一阵的,烟雾一样往上涌。我坐在干净的长凳上看着,觉得这样也不错。
好久没有安安静静地一个人玩了。以前,在我叫沙吉以前,我多半是一个人玩。后来,我被寄养了,我有了水,水给了我一段难忘的日子,真的很难忘——就在这一刻,我又觉得额头在隐隐作痛了……
不知水去了哪里?他还好吗?会想我吗?
水走了之后我又有了青榴,有着兔子嘴巴的青榴躲在这里轻轻地唱歌,唱给我听,也唱给自己听。现在青榴不是兔子嘴巴了,不用躲在这里唱歌了,但是也可以一起来玩玩呀,她怎么就忘了呢?
这时,一只鸟儿飞了过来,雪白的,却让太阳染成了金色,精美得如玛瑙雕琢的一样。它唧唧唧脆生生地叫了两声,头歪来歪去打量了我一阵,就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起风了,那串风铃丁零丁零响了起来。铃声响在秋天午后纯净的阳光里,听上去,有一种深入人心的温馨和单纯……
听了一会儿风铃声我就下楼了。
今天下午老师们有活动,少上了一节课,时间还早,我不想这么早回家,就在曲里八拐的巷子里逛着。小城的小街小巷很多,珠丝一样横七竖八地纠缠在一起,而我就像一只被它网住的小虫,在里面没头没脑地瞎转,出不来,也不愿出来。
转到一户人家的大门外,我停住了。
这户人家不同于其他的民居,门楼要高大一些,青砖黑瓦,大门两旁各有一扇雕花的木格窗,窗子用白石灰镶了一道边,显得醒目又古朴。双扇木门大开着,我探头进去,里面是一个四合院,有一棵玉兰树,旁边是一口巨大的缸。三面都是厢房,木格窗下摆了一些开得欣欣向荣的花儿。
我走进去一点,看见有人在里面打理,把一些很旧的桌子呀椅子呀洗脸架呀什么的抬进去,商量着怎么摆放。还有一个人在粉刷墙壁。
没有人在意我,我悄悄地走进一间没人的厢房,看见窗前有一张宽大的样式老旧的桌子和一把藤椅。一时兴起,就在那张桌子前坐了下来。
我人太小,桌子又太高,我只能将下巴搁在桌面上。午后沉静的阳光落在上面,我能看清桌面上木纹的走向和散布着的细细密密的虫眼。一抬眼,透过窗子,看见院子里的玉兰树叶在风中微微颤抖着。
有脚步声传来,我赶紧站了起来,这才发现墙上有一幅照片。
照片上的人瘦瘦的,干干净净、斯斯文文,说不上有多帅,但看着让人觉得亲近。特别是他的眼睛,我一直一直盯着他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也一直一直盯着我看,并有浅浅的、暖暖的笑意从他的眼里溢出来……
“知道他是谁吗?”
身后响起一个声音,回头一看,是一个面容和善的老头。我摇摇头。
“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写过好多书,他小时候就住在这里。”老头告诉我。
“那他又要回来了吗?”我指指桌子说。
“不,他不在了,”老头摇摇头说,“他回不来了,这里整理好是要让人参观的。”说完又和气地赶我走:“放了学就快回家吧。”
走出大门时我想,住过的房子还供人参观,那他一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就对他有了一种遥远的、模糊的敬仰。
后来,我对这个了不起的人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就在心里封存了一个了不起的秘密——小时候,一个秋天的午后,我在他用过的桌子前坐过呢!
我又转了几条巷子,糊里糊涂地竟又回到了校门口。
“小姑娘,你好。”
我转过身来,看见身边站着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考究的衣着,高挑的身段,雪肤黑眸,脸上画着精致的淡妆,手上拿着一个精巧的白皮包,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
不会是和我说话吧,我看看周围,没有别人,那女人笑了笑说:“就是和你说话呢。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我觉得她的笑容似曾相识,像在哪见过,心里就有了一份熟稔的感觉,就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
“哦,沙吉,”那女人柔声地说,“经常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呢?”
“你是说青榴吧,可能已经回去了。”提到青榴,我有点闷闷不乐。
“回去了,”那女人听了有点失落。她凝神想了想,最后像是下了决心似的说,“能告诉我她家住在哪儿吗?”
我把她带到青榴家住的那条街的街口,告诉她朱红腰门的那家就是,就回家了。
一路上我都在想,那个漂亮女人是谁?她怎么知道我跟青榴经常在一起?她找青榴干吗?
一回到家,我就把这事对云婆婆说了。
云婆婆听了,愣了半天才说:“终于还是找来了。”
“什么?她是谁?”我听得莫名其妙。
“小孩子少管闲事,快吃饭。”云婆婆把饭菜端上了桌。
第二天一到学校,就想快点见到青榴——昨天遇到的那个女人带给我的悬念已经把心里的不快冲淡了。可直到快上课的时候青榴才来,已经没有时间说什么了。
看得出,青榴根本没有心思上课,她两眼发直地望着黑板呆坐了一阵,然后拿出草稿本,在上面写了一句话,推到我面前。
我一看,上面写着:“我要走了。”
我一惊,回道:“去哪儿?”
“省城。”
“跟那个漂亮女人?”突然灵光一闪,我瞎猜道。
青榴扭头看了我一眼,她很奇怪我怎么会知道。
而她回的话更是让我彻底懵了:“她是我亲妈。”